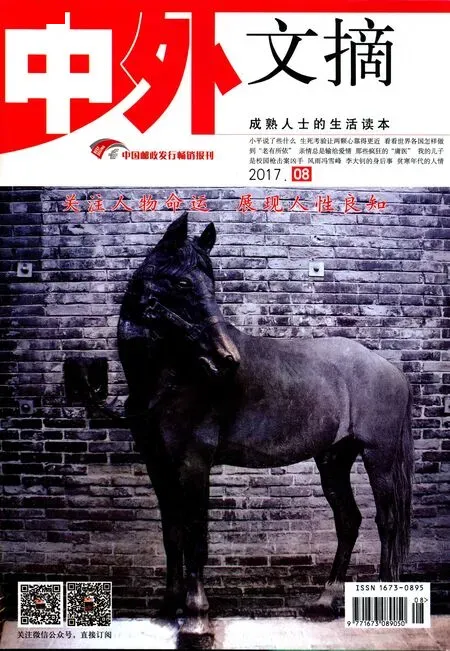社交媒體扼殺著什么
□ 張立潔
社交媒體扼殺著什么
□ 張立潔
很多人睜開眼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別的,而是玩手機,超過五成的父母玩手機的時間超過陪孩子的時間,北京人民使用手機日均7小時以上,全國最長……
數字時代“社交網絡在扼殺社交”這樣的言論并不陌生。如今這些“永遠運行、永遠在線”的技術,威脅到了一些人類生存的基本特征。那些讓人們時刻聯系在一起的技術,反而讓大家難以建立真正的人際關系。
除了時間,被扼殺的還有什么?你有沒有發現,很多人已經完全無法忍受獨自一人。馬路上、超市的隊伍里,哪怕給他十秒鐘,他也要拿出手機做點兒什么。也許接下來就是失去專注或者自我反省的能力,你的注意力只會投向外界。面對自我和發現自我是人格發育的基礎,獨處是自我對話的前提,但遺憾的是,人們獨我自處的能力正在消失。
人們如何與技術互動,繼而影響人際關系?在以社交網絡為代表的網絡媒體極其迅猛的更迭下,人們的注意力被裹挾著迅速跳轉。我們人類獨有的移情能力(即感受他人感受的能力)也從身體力行、感同身受,變成了“點贊之交”“口水情緣”。
試問自己,你還能記起槍殺俄羅斯大使的那名土耳其警察嗎?如動作大片一樣的場景不過發生在不久之前。槍擊之后,他沒有立刻開始大規模殺戮,而是對著鏡頭高喊“不要忘記敘利亞,不要忘記阿勒頗,我們在經歷痛苦,你們也不能好活”,為的是讓自己制造的混亂能夠在網絡上瘋傳,他做到了,可是我們忘記的速度更快,這何嘗不是另一種諷刺?
不論是明星丑聞、戰爭暴行還是慈善義舉、好人好事,無一例外都只能是“各領風騷幾小時”,我們生活的當下一切均以分鐘計算。這都是迅速發達起來的網絡信息一手促成的結果,這其中社交網絡越來越成為“議程設置”的推手。
無獨有偶,敘利亞的小姑娘BanaAlabed和家人一起被困在敘利亞首都阿勒頗,9月24日,Bana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發了第一條消息“我需要和平”。從此,她開始“直播”戰爭,由此成為網紅,得到了土耳其總統和夫人的嘉獎。然而,戰爭真的能夠停止嗎?
扭頭不看現實真是太容易了,而我們又能否邁出虛擬世界,把現實的生活建設成它應有的樣子呢?社交媒體賦予個體以信息傳播、組織動員的力量,作為“弱者的武器”有助于抗爭者爭取輿論關注等外部資源,但是在“發出聲音”和“做出改變”之間還有諸多環節缺失,導致事情并不總是能向著好的方向發展,有時不過如拍岸的潮水,湮滅消失而已。
舉一個“正面”的例子,或者說前后環節順利銜接并最終成功的例子,只是這個例子多少讓人有些唏噓感慨,那就是剛剛結束的美國大選。
包括Facebook的總裁扎克伯格在內的知識精英派其實都是希拉里的支持者,但卻不能不眼看著自己的媒體平臺親手把特朗普送上總統寶座。據社交媒體數據分析機構所述,自去年6月以來,特朗普在Facebook和Twitter平臺上發言超過6000次,在所有社交平臺上的“交互”近8500萬次,遠高于希拉里的3100萬次……在去年3月到今年3月的12個月期間,特朗普一共在社交媒體發布了44457個帖子,而美國人用于閱讀、回復和傳播這些帖子的時間總計達1284年。特朗普的例子似乎又在證明著社交媒體的無所不能。
問題在于,面對一項永遠能運行在你身上的技術,我們要如何才能在這樣的情形下過著更有意義的生活?毫無疑問,我們還沒學會駕馭它,反而被裹挾其中,幾近失控。
(摘自《三月風》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