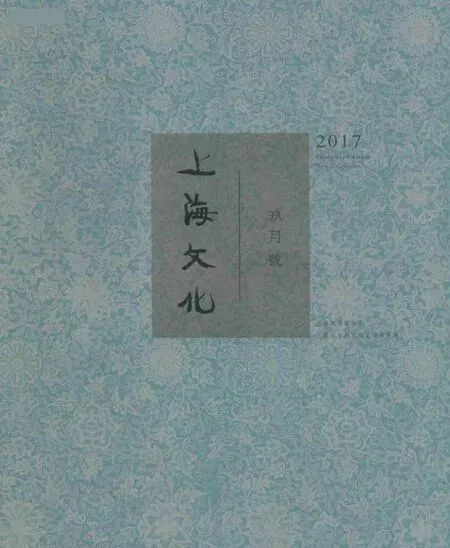“大師兄”王富仁
黃子平
“大師兄”王富仁
黃子平
因為是浩劫之后第一位“中國現代文學博士”,所以呀,廣義地說,您是我們所有這些1980年代入這個行當的人的“大師兄”了。當面給他戴“紙糊高冠”,王富仁兄卻不為所動,笑咪咪地吸煙,靜靜地瞅著這幫廣義的“小師弟”有一搭沒一搭鬼扯。忽然扯到他覺得有意思的話題了,好吧,一開口,一支接一支不抽完半包煙他停不下來。
有一種“正經八百”的學術研討會,規定每人發言二十分鐘,還剩三分鐘打鈴一次,還剩一分鐘打鈴兩次。可想而知參加這種會富仁兄有多受罪,不許吸煙不說,剛開了個頭,叮叮,打鈴兩次!有一回在港大開魯迅研討會,講評的香港教授拿到富仁兄的論文,主旨深刻視野宏闊觀點明晰邏輯嚴密,挑不出毛病,不知怎么講評,只好從細節入手,說引魯迅沒注明出處。聽會的學生們都笑說,魯迅的全集都在王老師肚子里了,隨手拈來注什么出處嘛。
1980年代初,我在《文學評論》上讀到富仁兄博士論文的緒論,大為震撼。就好像在“正統魯學”的鐵屋子里,有個傻子搬了塊磚頭,咣咣地砸了個透亮的窗戶。我們一伙“廣義的師弟”都覺得,這篇論文宣示了幾十年巋然不動的“正統魯學”的終結。當然“鏡子說”仍不脫反映論的思維窠臼,然而從“政治革命”轉到“思想革命”,這就非同小可。他把《吶喊》、《彷徨》二十幾篇小說,重構成一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系統,從立意到藝術,解析得那叫一個通透!——無懈可擊。
后來“魯學”又成為顯學了,言說魯迅的文章我就不太愛讀。批魯反魯也好,捍魯衛魯也好,大都寫得沉悶而無聊。富仁兄的長文也讓人吃不消,但讀到那些回憶他少時讀魯的文字,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這是貼著生命的有溫度的回憶。富仁兄說,在那謊言充斥的年代,唯有魯迅的書是對我說真話的書,唯有魯迅是跟我說真話的人。但少時讀魯也有意想不到的嚴重后果。富仁兄說,明明昨天你還是三好學生、學生干部、優秀少先隊員,忽然你就看周圍什么都不順眼了,周圍看你也什么都不順眼了。用古人的話說,忽然你就有點“不可”一世,如是一世也就“不可”你。中了“摩羅詩力”的蠱,會活得很辛苦。憑著這一代人少時讀魯的經驗教訓,我對老錢錢理群去給中學生講魯迅,就頗有點腹誹——絕對誤人子弟!高中畢業班的老師給學生們的忠告是對的:你的目標是考入北大去聽錢老師講魯迅,而不是聽了錢老師講魯迅去考北大。你這時候聽得開心,然后別說考大學了,做人都很艱難。于是爆滿的錢氏中學生魯迅講座,忽然冷冷清清,學生們真乖:這是好的。要知道,魯迅的書有毒,說真話會害人。這一點魯迅自己也說過很多次了,唯有“以說謊和遺忘為前導”,你方能依稀看見那條灰白的路從暗夜蜿蜒而來。
富仁兄對魯迅作品的解讀,那種細致綿密的條分縷析,我總是嘆為觀止。譬如他解說《故鄉》的“悠長”,悠長的憂郁,以及憂郁之美。富仁兄說,直到結尾,這種憂郁的情緒仍然沒有全部抒發罄盡。故鄉的前途仍然是一個未知數,一個需要人自己去爭取的未來。它把對故鄉的關心永久地留在了人們的心中,把對故鄉現實的痛苦感受永久地留在了人們的心中。“人們沒有在結尾時找到自己心靈的安慰,它繼續在人們的心靈感受中延長著、延長著,它給人的感覺是悠長而又悠長的,是一種沒有盡頭的憂郁情緒,一種沒有端點的歷史的期望”。在“中國文化的守夜人”魯迅心里,這無盡的鄉愁一如悲涼之霧,籠罩四荒。
然而,對富仁兄那些大框架、大論述,譬如大氣磅礴的“新國學”論綱,我就有點望而生畏。在這一點上,倒是老錢錢理群對他有“同情的理解”,說,富仁兄給自己規定的任務,是將國學(民族學術)內部,長期被視為勢不兩立的各個派別,例如:古代文化(“舊文化”)與現當代文化(“新文化”),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學院文化與社會文化、革命文化,聯系為一個更大的統一體,建立自我和自我對立面共享的價值與意義,構造一個有機融合、相互溝通互助的“學術共同體”,并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同存共棲”的精神歸宿。——好吧,這兩位大師兄都有這種愛用大詞、大概念的雄心/毛病,對我這已經習慣于碎片化思維的人來說,只能敬而遠之。我總覺得,“國學”無論新舊,一旦姓了“國”,就難免有壟斷,有霸權,有科層等級的區分和壓榨,所謂“共同體”無非是一種烏托邦空想而已。可是轉頭一想,你又會為這兩位兄長的拳拳之心、死不改悔的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感動不已,并開始反省自己的犬儒和遲暮疲懶的心態。
五年前我到老家的嘉應學院訪問,講點“當代文學中的勞動與尊嚴”之類的專題。富仁兄說,路很近啦,還不順便到汕頭大學來講一次。嘉應學院跟汕大有密切的戰略合作,派車送,這就第二次到了汕大。記得上一次是來開一個很大的學術研討會,叫“全球化視野中的現代文學研究”什么的,題目唬人,參加人數也嚇人,主持者富仁兄忙得腳不沾地,根本說不上話。這回從從容容,講完了課吃潮州菜,傍晚到水庫大壩散步乘涼。那時他的身體狀態已經不太好了,卻還很自豪地宣布:我戒了——戒酒不戒煙!那年香港的嶺南大學有一個會,討論老錢的新書巨著,想請富仁兄作為“同時代人”去參加發言。我說起香港的校園全面禁煙,而香港海關免稅煙是十九支(也就是說,一盒煙你得在關外吸完一支才能過關,否則整盒收稅)。富仁兄大驚失色,一臉堅毅地說:這樣子啊,那我就不去了。我本想以香港的苛政為契機令他戒煙,沒想到反效果是失去了在嶺南大學與他再聚的機會。
第二天是個陽光燦爛的日子,富仁兄叫車帶我去澄海塔山參觀一個博物館。偌大的館(分布在幾個小山頭),孤零零只有我們兩人繞山而行。“碑廊銘史”,“石筆書史”,經了“焚書坑儒”的年代,創辦者想用堅硬的介質來抵抗歷史虛無主義,他們沒想到“焚坑事業”及其手段,其實一直在進化之中。參觀這樣的博物館,令人心情如同那些石塊一般沉重。下山的時候烈日當空,富仁兄沙啞著嗓音說,只怕這樣的博物館,也辦不了多久了……
那就是我和富仁兄最后的一次相聚。我心憂傷,如此悠長。
編輯/木 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