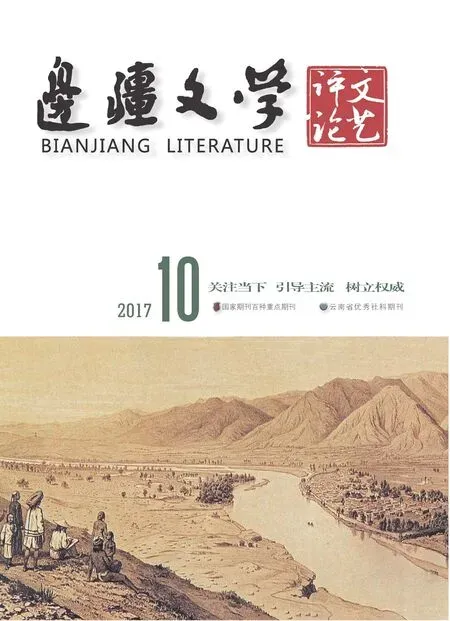《太陽照常升起》和《刀鋒》對迷惘青年的不同闡釋
曾子芙
經典重讀
《太陽照常升起》和《刀鋒》對迷惘青年的不同闡釋
曾子芙
海明威1927年出版的小說《太陽照常升起》,毛姆1944年出版的小說《刀鋒》,兩部作品的主角都是美國退伍軍人,他們經受了戰爭帶來的肉體和精神創傷,試圖在迷惘中尋找人生方向,用各種方式尋求精神慰藉,代表了一戰后信仰崩塌、陷入迷惘且難以重建精神支柱的美國青年。
海明威在《太陽照常升起》中從在戰爭中性功能遭到損傷的退伍軍人巴恩斯的視角,講述了一戰結束后,他和同伴在歐洲度過的幾周,描繪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對現狀失望、對未來悲觀、對人生困惑的美國“迷惘的一代”青年。毛姆在《刀鋒》中從作家自己的第一人稱視角,講述了他身邊的退伍軍人拉里的戰后生活,拉里的戰友在戰場上為了救他而犧牲,戰爭結束后,拉里回到了正在積極建設“繁榮而偉大的時代”的故鄉美國,卻始終與周圍環境、周圍人格格不入,失去了人生方向,他以各種方式來重新追尋人生的意義,故事一直延續到了二戰前。
兩部小說都表現出了戰后美國青年的迷惘心態,我們把小說里的男主人公單獨拎出來,從作品中塑造的主角的迷惘心態的疏離感、漂泊感和失落感三個層面來看,他們展現了戰后青年迷惘心態的不同側面。我們會發現,兩位作家在闡釋戰后青年迷惘心態上,不僅在時空跨度、敘述視角、寫作技巧和語言風格等方面不一樣,而且著眼點不同,海明威更專注時代情緒的深刻挖掘,毛姆更傾向于表現時代多方面的大變遷。海明威所闡釋出的迷惘心態是沉痛而精準的,毛姆所闡釋出的迷惘心態是有出口有希望的。
一、疏離感:封閉的心靈
迷惘心理的表現之一是疏離感,它的含義可以從不同維度進行解釋。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美國社會學家卡普蘭在其《疏離感與身份認同》中說:“當一個獨立的個體察覺到他與他的社會地位、身份認同、人際、生活方式以及他的工作之間缺少了有意義的聯系時,疏離感就會發生。”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疏離感作為一種內在的心理成分,主要指個體內心感受和身體體驗到的一種遠離、疏遠和冷漠。從人與社會的關系來看,當一個人過于沉浸在濃烈的個人情緒時,自然就會對周圍事物產生不同程度的疏遠,成為一個冷漠的旁觀者。
《太陽照常升起》和《刀鋒》都重點表現了主人公疏離的心理狀況,它們用不同的文本形式和敘述角度,表現了主角在社會環境、人際、自我認同三個方面所呈現出的疏離感。兩部作品在解釋導致美國青年這一狀況的原因上也各有側重。
1、社會環境疏離感
在兩部小說中,兩位主人公的物質需求都不高,都沒有來自金錢的煩惱,《太陽照常升起》中巴恩斯有工作帶來的固定收入,他對物質生活的質量要求不高,也懶得改變自己目前的生活狀況,他基本上對自己的物質生活是滿足的。他的焦慮、困惑都是精神世界的,為了緩和愛情生活的不如意帶來的壓抑,他賭博、喝酒、釣魚、發呆、看斗牛……他依然在尋找生命激情,因為自己的生理缺陷,他的愛人做什么他都可以寬恕。“他始終感覺到他的戰后生活如同做惡夢一般,夢境反復出現,雖然已經熬過,但現在又必須從頭熬起。”他在繁忙的社交生活中感到異常為難,竭力排斥那些他不喜歡的人。
戰爭改變了巴恩斯,也改變了現實,他覺得戰爭“仿佛是一個天大的玩笑”。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社會政治腐敗、社會犯罪增加、貧富分化、宗教矛盾、環境破壞等諸多問題,參加過戰爭的巴恩斯在戰爭中獲得觀察國際形勢的能力,他喜愛冒險、旅行,同時也厭惡節約、謹小慎微等過去清教徒所倡導的“平民美德”。戰爭讓他變得難以承擔責任,并讓他覺得現在的生活難以忍受。他遠離自己的故鄉,在“既骯臟又奢侈,厭煩、空虛、沉悶、丑陋”的巴黎過著沉淪的生活,他對現實感到失望,選擇回避。他始終都和一個狹小的圈子里的人交往,沒有一點擴大自己社交圈的欲望。在小說中我們看到的是在戰爭的蹂躪下,經歷過戰爭的年輕人心靈上的瘡痍,他們對現實不滿,又看不到未來。
《刀鋒》中的拉里始終同社會主流意識格格不入,他在美國時是迷惘的,他來到巴黎后,開始接觸宗教、文學、藝術、東方文化……試圖盡量廣闊地尋找自己生存的可能性,去發掘新的精神依托。拉里與社會的疏離是他主動選擇的,戰爭結束后他回到家鄉,他的親朋好友為他設計了所謂的“有前途”的人生道路,而他卻對這些毫無興趣,一心只想“晃膀子”。以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看來,“有前途”的人生道路就是要像伊莎貝爾說的那樣:“美國正在一日千里地前進,要有責任參加國家的發展事業,要有勇氣去擔當目前面臨每一個美國人的重任”,要勇于建設社會,直面現實,而不是采取避世的態度。拉里選擇了與主流社會相悖的“晃膀子”人生。對于“晃膀子”,毛姆在敘述時,一直沒有讓拉里明說出這到底是什么,毛姆一直在設置懸念,不斷勾起讀者的閱讀興趣。
巴恩斯被動地承受著戰爭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得不選擇與愛人、社會進行疏遠,他被海明威塑造成戰后“迷惘一代”文學的代表人物。拉里的社會環境疏離感,是因為他內心的形而上追求,帶有幾絲積極和傳奇的意味,拉里被毛姆塑造成一個理想主義式的人物。
2、人際關系疏離感
在《太陽照常升起》中,海明威用簡潔的語言來描述巴恩斯瑣碎的日常生活細節,走過哪里、怎樣走過、看到了什么、吃了什么……海明威對這些日常行為和環境的敘述是直接而準確的,將日常生活瑣事用樸實的語言表達出來,巴恩斯獨自一人時,對美好生活是有追求的。但在巴恩斯與其他人的日常交流對話中,他卻常常表現出一種拒絕交流的態度,巴恩斯的語言表達充斥著大量的消極和抗拒,無論任何人問起他的事情,他幾乎都消極且敷衍地應對:“你想不想到南美洲去?杰克。”“不想去。”“為什么?”“不知道。”……這樣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對話,在小說中比比皆是。
在小說中,海明威對巴恩斯日常瑣事及周圍環境進行豐富的描寫,同巴恩斯在人際交流上的空洞虛無形成一種強烈反差,表明巴恩斯雖有豐富的生活經歷與內心世界,但他內心拒絕和別人分享,沒有和其他人交流的興趣,他的心理狀態是封閉的。由于在戰場上失去了性能力,又恥于向別人訴說,他陷入心理極度壓抑的狀態,即便每天都在聚會與社交,但在繁忙熱鬧中,卻異常孤獨。而在親密關系中,由于性能力受損,巴恩斯只有不斷抑制對布萊特的愛,一方面看著她和各色男性周旋,一方面與其維持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曖昧關系,于是在愛情中得不到寬慰,和愛人相互疏離。
《刀鋒》里的拉里也常常參與各種社交活動,友善地同他人交流。但他始終和周圍的人有隔閡,小說中多次強調他在戰后和戰前相比,就像換了一個人似的,戰爭對他有很大影響,但他從不與周圍的人訴說他在戰場上的經歷,他的未婚妻伊莎貝爾多次讓他告訴自己他在戰場上經歷了什么,“他卻總是那樣笑笑,說沒什么可說的。”在小說前半段,他在戰場上的經歷,成為了他身邊許多人疑惑的“懸念”。
毛姆在講述拉里同別人交流的這部分,就不單單用對話來表達,他更多地是用小說中其他人對拉里的評價,來表達出拉里從戰場回來后變得不太同人交流,變得行為古怪。比如他的未婚妻伊莎貝爾總是提到他和參加戰爭前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拉里把自己的內心隱藏了起來,遠離了過去的社交圈子,他可以一個人安靜地在圖書館看一整天書,他的疏離感表現在他的與眾不同,異類的脫離了正常人的生活軌道。對拉里來說,愛情和婚姻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他可以輕易放棄同伊莎貝爾的婚約,也可以隨意就娶了落魄的索菲。
巴恩斯的人際關系疏離感是一種我行我素式的冷漠,帶著重重的生硬感,由于戰爭剝奪了他的性能力,他被動地選擇同人群遠離,環繞在他周圍的是無意義。拉里的人際疏離感來源于一種精神困惑,表現為拉里與社會主流背道而馳的追求,他對世界充滿困惑,卻依舊對人生有期待,只不過他是走在與社會主流大眾背道而馳的追尋之路上。
3、自我認同疏離感
在《太陽照常升起》里,海明威筆下的巴恩斯對布萊特愛的本能和他們之間無法解決的現實問題,讓他對自我產生厭惡。在日復一日的壓抑下,巴恩斯不斷地自我麻痹,在心里筑起一道道屏障,試圖遺忘,用酒精麻痹自己,置身于喧囂的環境里,茫然地走在大街上,嘗試獲得短暫的大腦空白。他的生活是得過且過,每一天都在痛苦、無聊與空虛中度過。戰爭給巴恩斯帶來的決定性影響,在于剝奪了他作為一名男性的身份肯定,他不能接受這樣的現實,于是選擇自我疏離。
《刀鋒》中多次提到拉里和戰爭前就像是換了一個人似的,他疏離的是沒有經歷過戰爭時的自我。他自動忽略了周圍人的所作所為,也不關心當下的政治經濟形勢,后來索性遠離了西方社會。他不在意對他“晃膀子”無關的人的看法,他不和周圍的人進行過多爭辯,即便他的未婚妻伊莎貝爾以退婚來威脅他,逼迫他停止“晃膀子”時,他也平靜地接受分手。戰爭的創傷記憶對他來說,是跨越了一切的,是長久而深入的,拉里意識到死亡的色彩和滋味。經歷了戰爭的拉里對生活對“自我”感到懷疑,他疏離了戰爭前的那個他自己,他在戰后的美國環境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開始急切地尋找新的信仰和新的“自我”。戰爭中突如其來的震動,讓他對原本的自己和社會給他安排的社會角色產生疏離感,拉里的自我意識開始蘇醒,開始關心“自我”和尋找新的“自我”。
巴恩斯和拉里都對自己的社會身份產生了懷疑,不同的是,巴恩斯是對他男性身份的一種逃離,他選擇回避現實。拉里是對過去自我的一種否定,他選擇拋棄親人給他設計的社會身份,走上一條艱難的追尋新的“自我”的道路。
《太陽照常升起》里的巴恩斯的疏離感,來自于他在一戰中留下的生理創傷,因不能和自己愛的人相愛,難以結婚成家,不能生兒育女,而否定自己,逃避現實,是被動的。《刀鋒》里的拉里的疏離感,是他自我意識覺醒后的主動行為,他所有的行為,包括學語言、看書、去大學聽課、去打工、去修真……都來源于他意識的主動性,他有自己的判斷和打算。
海明威和毛姆都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造成年輕人對社會、他人和自己產生疏離感的重要原因,戰爭給他們帶來了肉體和精神上的創傷,大戰改變了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引發了各種社會問題,青年人無法在短時間內適應,沒法融入社會,只有逃避,表現出對社會、他人和自己的疏離感。
二、漂泊感:逃離家園
漂泊感也是構成迷惘心理的重要部分。《太陽照常升起》和《刀鋒》里的人物都有一種“逃離美國”的情緒,都遠離了自己的家鄉,在遠離故土的地方尋找新的人生方向。小說中主要的故事都發生在歐洲,并輾轉了歐洲的好幾個城市,作品充滿異國情調,并帶有一種居無定所的漂泊感。
在《太陽照常升起》里,巴恩斯和一群年輕人來到歐洲,時而沉醉在狂歡和玩樂中,時而留戀于大自然的美麗風景里,時而陷入長久的困頓,巴恩斯對未來何去何從的迷惘心理表現為一種漂泊感,迷惘心理因心靈上的無家可歸而更加深刻。巴恩斯的內心是矛盾的,他處于一種搖擺不定的漂泊狀態。他和自己的土地失去了聯系,卻不能在新的土地上獲得領悟,戰后的歐洲環境光怪陸離,不論是在巴黎的紙醉金迷,還是深入比利牛斯山放松垂釣,還是在西班牙與巴斯克人一起狂歡舞蹈,他都始終置身其外,他用一種旁觀者的態度看著他的同伴,他醉醺醺地看著其他人狂歡,看著布萊特換了一個又一個男伴。 巴恩斯來到歐洲,他在漂泊中找尋著自己的方向,卻始終找不到出口,掙扎在漂泊者的泥淖中出不來。他的這種自我流放的行為一開始就是帶有對原本傳統的割裂之情的,可現實給他帶來的影響依舊是負面的,他帶著對故土、對歐洲的雙重失望陷入迷惘。
《刀鋒》中拉里的人生探索執著而漫長,他想要一生有所作為,但是又不知道做什么,只有慢慢地往未知方向去尋找,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不急躁,對人隨和,慈悲為懷,丟掉一個我字,不近女色。”他不僅在歐洲各國漂泊游歷求學,還走到了更遠的印度,踏上一條心靈的自我修復之路,對生命價值進行了多方面的參悟,還在印度學會了神秘的催眠術,最終回到美國繼續追求精神的完美。他逃離故鄉來到印度,通過閱讀、冥想、修真、練瑜伽等一系列他認為能夠找到人生真諦的行為。
拉里從美國漂泊到倫敦,再從倫敦漂泊到巴黎,再從歐洲漂泊到遙遠的東方,最后再從東方回到美國。從這樣一條清晰的由西方到東方,再從東方繞回西方的精神探索之路可以看出:毛姆敏銳地觀察到了歐洲大陸經歷了戰爭后人們信仰的崩塌、精神的幻滅,新的信仰應該從何而來?毛姆試圖解決這樣的問題,最后根據他的經歷,他把拉里追尋精神之路的落腳到了他自己也并不是非常了解的印度神秘的吠陀經哲學上。這是毛姆在創作上的一種敘事策略,把他自己也不太了解的印度神秘哲學當作拉里追尋人生真諦的終點,可以吸引讀者的閱讀興趣,又體現出他對西方精神信仰缺失的憂慮,對東方文化的向往和期望。
從某種程度上看,兩部小說在表達青年在漂泊中試圖沖出迷惘心理的過程,都是帶有一定自傳性質的小說。海明威呈現的漂泊感是一種沉重的、難以掩蓋的傷痛。而毛姆呈現的是舊價值觀的破滅,在漂泊中對新事物進行探索,毛姆將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了精神漂泊中執著探索的拉里身上。
三、失落感:生命價值失落
迷惘心理常常表現為難以消除的失落感,“迷惘的一代”也是“失落的一代”。簡單來說,失落感是因為失去了自己原本擁有的,現實也沒有達到自己的期望而造成的一種心理落差而導致的各種消極情緒,比如:沮喪、苦惱、心虛、彷徨。由多種消極情緒交織起來的情緒體驗就是失落感。
對于巴恩斯和拉里來說,他們始終在思考著生存與死亡,因為他們感覺不到自由,他們行動的動因最主要的還是來自于心靈的“迷惘”。《太陽照常升起》中的每個人都面對著痛苦、疼痛、失望和死亡,他們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靠酗酒、狩獵、看斗牛麻醉自己,逃避現實。 在小說的前半段巴恩斯說到自己的人生價值已經固定,不會再改變了。到后面又由布萊特一語道出,“你其實并沒有什么價值觀,你早已心如死灰,這就是事實。”
《太陽照常升起》里除了主人公巴恩斯之外,還寫了很多和他一樣經歷了戰爭,在戰后郁郁而不知所向的人,環繞在各色男性之間的布萊特,苦苦追求布萊特的科恩,樂于享受的比爾,他們面對不同的人生問題和不同的迷惘困惑,他們是戰后一代人的象征。一戰后,太多的年輕人意識到,他們可以獲得基礎的溫飽,不用為一日三餐而奔波,但他們失落了人生價值追求,一戰帶走了生命,帶走了愛情,這樣郁郁無求的迷惘是一種無盡的、深入的失落感。
在《刀鋒》后段,呈現出拉里已經形成了和當時美國主流社會人群完全不同的生活態度。是物質至上?還是追求精神的豐富?毛姆并沒有在小說里直接回答,他一方面展現了一戰后到二戰前這段時間里歐美的社會現實——經濟危機、上流社會的幻滅和巴黎藝術圈的變化等——一方面又兼顧著小說的可讀性,除了講述了男主人公拉里之外,也講述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追求生活富足的伊莎貝爾,縱情于酒精和毒品的索菲,享受著上流社會虛偽的尊重的艾略特,亦步亦趨地走著長輩安排的道路的格雷,一心要同藝術為伍的蘇菲……他們追求的是不同的人生道路,形形色色人物的結局都和他們的初衷背道而馳。
從兩部作品對人物失落感的敘述看,海明威剖析了心情憤慨的迷惘的一代方向失落、遭受失敗和共同的創傷,《太陽照常升起》里的人物帶有某種虛無主義色彩,海明威是絕望的,他表現的精神失落感帶來的破壞力是毀滅性的,這樣的絕望類似于艾略特在《荒原》里呈現的,是可以一直反復斟酌的無盡空虛。而毛姆試圖在《刀鋒》里探討戰后青年在失落感中重新尋找人生價值,在尋找過程中的各種可能性,他塑造的拉里帶有理想主義色彩。
《太陽照常升起》是一部講述精神世界被破滅了又要重構,卻沒有重構起來狀態的小說。《刀鋒》是一部講述人物的一種理想化心靈修復的小說。兩部作品給人帶來的是不一樣的閱讀感受,這樣的區別帶有時代烙印,但最終都落到了對戰爭的深切控訴上。
《太陽照常升起》于1927年出版,此時正處于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小說集中展示了迷惘一代當時的窘境,精準地切中了一代人的要害,它具有顯著的反傳統性和革命性。而海明威簡明扼要、樸實無華的“冰山體”創作是具有現代性的,小說一經問世,就獲得了評論家的大量討論,在文學和文化領域觸發了革命性的轟動。這部小說成為展現“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品,海明威也成為了“迷惘的一代文學”先驅,成為該文學潮流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家,這部小說對美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
《刀鋒》于1944年出版,由于小說沒有太多先鋒性的涉及,在內容和敘事上都保留著的英國一貫的現實主義筆法,這部作品在當時的評論家眼中是一部平常小說,但這部小說又在讀者中產生了廣泛而持續的影響,《刀鋒》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價值,與它在讀者中的極高的聲譽間,存在巨大差異。毛姆用精巧的筆法,準確、簡潔、悅耳的語言,引人入勝的情節,在不斷地推動情節的過程中設置懸念,力求小說的可讀性最大化,主角拉里的追尋是一種帶有傳奇性的積極探索,對讀者有極大的閱讀吸引力,給正在二戰泥淖中掙扎的人們帶來一絲新的希望,也給今天的青年許多啟發。
[1] 莫頓 A.卡普蘭.疏離感與身份認同.[M].紐約:自由出版社,1976.第118頁.
[2] [3] [4] [6] 歐內斯特·海明威.太陽照常升起.方華文.譯.[M].江蘇: 譯林出版社,2012.第207頁,第7頁,第42頁.
[5] [7] 威廉·薩摩賽特·毛姆. 周煦良.譯. 刀鋒[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第71頁,第28頁,第49頁.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楊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