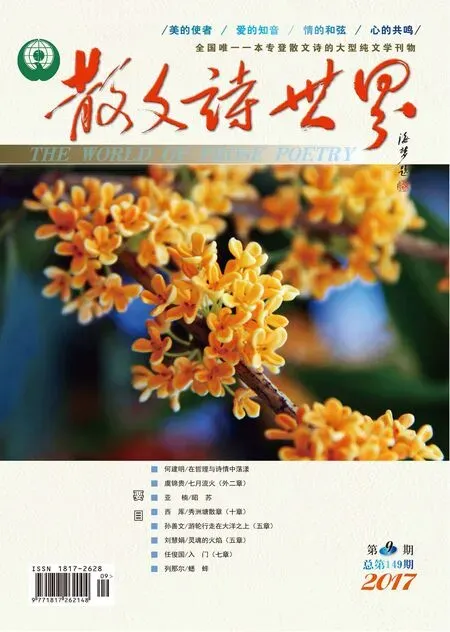樓板寨六記(外一章)
山西 李詠梅
樓板寨六記(外一章)
山西 李詠梅
一
這里,是樓板寨。
東漢末年以降叫云中縣、卻胡堡、明清樓。
嘉靖年間叫蘆班寨。
這么多年了,公元210年的村莊,也已經長成了公元2016年的村莊。
匆匆閃過的核桃樹、高粱、玉米、谷子,都像我那些夙興夜寐的長輩:在風雨中無聲地開花,無聲地結果,以足夠多的沉默喂養后人。匆匆閃過的煙酒店、副食店、肉鋪、旅館、澡堂,都是比我年長的久居人間的煙火。
以供銷社墻上的斑點為證,以糧油店門上的塵垢為證,以飯莊瓦楞間的細縫為證:
這些生活的火焰之源,早已被生活用舊了。
二
王家營的兩汪泉水依然可以從玄武巖的裂隙中,福祉一樣源源不斷地涌出。
古人不見,“秀云山泉”,有秀勇之品格清醇,有秀勇之心地甘甜。
古人不見,這個早已在云中山脈主峰群腹地扎下慧根的人,
眼中自有晉善之流水,
胸中自有晉美之丘壑。
三
過神泉,車子在王家營村口的活動空地前停下。
他將車門鎖好,下車,走向士兵一樣的大葉楊林。他站在林中插腰四顧的樣子,在我看來,恍若身在沙場。
一個前幾日還在家,學著將生活之美揮毫成草書的人,此刻兼任著草木的王。
他姓趙。
喜酒,喜書,喜山水。
至今我仍不知他名誰。
四
深紅色爬山虎、臭金蓮、雞冠冠花、五種顏色的菊花,在村口同時消磨著王家營的仲秋。
他一弓身進了花團錦簇的水磨坊。
他叫生,也叫森。
如果樹木可以開口說話,一定是他在山中唱民歌的樣子。
每一次他牽頭的山中行,都像一首仿古的《長歌行》。
每一次,他暗暗動用遠古的歌喉,試圖回答孟德兄“人生幾何”的哲學疑問時,都會有弟子一樣虛心的草木,向生而立,向他袒露出一腔綠色的真理。
此地民風古樸,大山若愚。
而眾草是慧的,眾樹是慧的。
一個懂得如何在生活中活的人,也是慧的。
五
在樓板寨,在滴水崖下,我親眼目睹了流水的決絕。
水滴縱身躍下,猶如星光,帶來了高處的秘密。
我愛這瀑布,愛用目光在這明亮的布上繡花。
而我生來就有一顆懸崖邊也不勒馬的野心。
學會御馬這門技藝,太難。
我傾盡一生,也無法勒住時間的韁繩,無法把一瞬活成永恒。
六
在彭家塔,只見六人,兩狗,七牛。
民舍有古意,如入《豳風?七月》,“如入桃源”。
水磨坊連通的溝渠里,清水抱琴而來。
在分流處,我閉目聆聽——
這首濕潤的小令,代表了整個樓板寨的心跳,轉達了十月的村莊對陌生來訪者的默默禱告。
落 日
下班了,我和落日一起,結伴回家。
古往今來,暮色蒼茫的群山背后,那顆碩大的、燦爛的、明艷的落日,曾讓多少疲憊迷茫惶惑的人心有所慰。
它的親人遍布星空。那些大的、小的,遠的、近的,明的、暗的,不是它的兄弟,就是它的姐妹。
我有時候會把落日認成親人。
我凝視它,用手機拍它,用詞描述它。閉上眼睛后,我還會用心畫它。
我凝視它,直到我意識到落日是近的,而我才是天涯……我才發現,我像每一個流離失所的游子,正專注做著一件認祖歸宗的事情。
我凝視它,此刻,夕陽中的每一縷光線都是我的閨蜜。
我目不轉睛地看著落日在宇宙中一點點淪陷,仿佛目睹一場誰也無法拯救的愛情。
落日從來不會回心轉意。它看不見自己的身后,有如影隨形的月亮,有月亮一樣彎彎的眼睛。從車窗里望出去,我看見沿滹沱河兩岸的曠野上還積著一層薄薄的雪,落日的余暉給它們鍍上金子,而積雪終將消逝成光陰。
溝溝壑壑中,一些風景始終隱隱滅滅。那些看不見的事物,永遠值得我繼續為之激動。
落日遠,落日殤。
我閉目祈禱:夜降臨兮歸我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