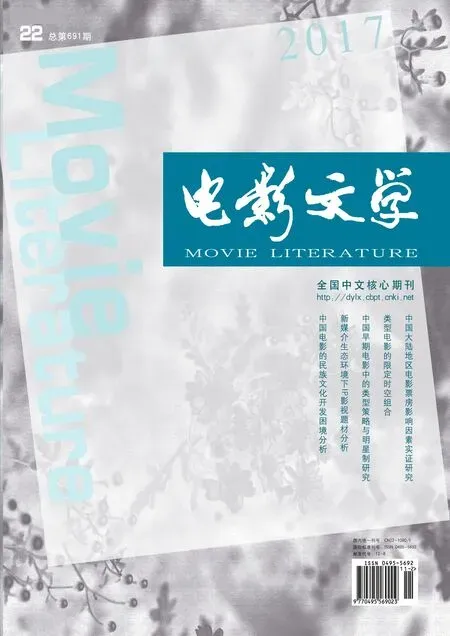類型電影的限定時空組合
李燕吉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4)
法國戲劇理論家布洛瓦認為:“要用一地、一天內完成的一個故事,從開頭直到末尾維持著舞臺的充實。”即要求每部劇限于單一的故事情節,事件發生在一個地點并于一天內完成。這就是戲劇理論遵循的“三一律”原則。“三一律”對時間、地點和情節的限制,可以使故事更加緊湊、明晰,戲劇沖突高度集中激烈,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誕生于20世紀初的電影藝術起源于戲劇,但經由聲光電轉換的現代技術手段比戲劇更加貼近現實生活。自誕生之日起,就擺脫了戲劇三堵墻的束縛,故事的時間跨度更長,空間范圍更廣。場景空間的開放性和場景轉換的靈活性成為多數電影創作者約定俗成的創作理念,亦是電影區別于戲劇的顯著標志。雖然電影敘事在空間的轉換頻次和時間跨度上大大優于戲劇,但承載時空的容量畢竟是有限的。電影不同于長篇小說,能夠在創作上天馬行空,擺脫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講述主人公傳奇的一生,表現人物復雜的內心世界,有著近乎無限的敘事空間和敘事時間。特別是類型電影,要在有限的兩小時時間內向觀眾講一個完整的故事,闡述一個鮮明的主題。為了增強故事的戲劇性,還必須有開始、沖突、轉折、高潮和結尾。最后還要讓觀眾看懂,認同故事的主題和結構。這就要求必須對影片的空間和時間進行適當的限定、壓縮,讓故事在一個有限的時空中發生、發展,從而達到或接近“三一律”所營造的戲劇原則,以此來吸引觀眾,贏得票房。正如安德烈·戈德羅所說:“電影是互媒介的。一方面,電影從文學或戲劇中獲取成分,另一方面,電影經受這些媒體的一些影響。電影在其早期尤其是互媒介的,將來可能更是如此。”類型電影和戲劇、小說等姊妹藝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而其自身的特色,即來源于時空的限定組合。類型電影的時空限定比戲劇長,比小說短。
托馬斯·沙茨認為:“類型影片就像敘事作品一樣,必須從時間、空間來加以研究:發生了某件事,它是在有限的視覺行動舞臺范圍內發生的。類型沖突的時間過渡強化,以及感知或體現那一沖突主人公的存在,要求我們的分析去考慮事件的連續性和發生那些事件的環境。要通過類型的關系結構來對待空間和時間的想法,這個結構就應該看作是所謂空間關系和時間關系的組合來加以研究。”沙茨首先提出了研究時空組合的必要性,并且闡明了限定時空的相互組合方式是決定類型的一個重要判斷標準,不同的限定時空組合方式決定了類型電影的類型化特征。在限定類型空間中所出現的典型環境和特殊文化社會群體就是一種類型的代表性符號。例如,限定時間是在匪徒坐火車到達小鎮前找到幫手,準備決戰;限定空間是荒漠、小鎮、風沙、鐵路站點;出場人物是牛仔、警長、妓女、匪徒,那么觀眾看到荒漠、小鎮和騎馬持槍的牛仔、警長、匪徒后就會立刻明白——這部電影的類型是美國西部片。如果限定時間是趕在朝廷殺手到來前逃出邊關,限定空間是塞外邊城、黑店客棧,出場人物是仗劍俠客、朝廷殺手、黑道幫會、西域商隊,觀眾就會馬上得出結論——這是中國武俠片。但是,沙茨研究的對象是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好萊塢電影,他僅僅提出了一個時空組合的觀念,并沒有就時空組合的具體方式提出更具體的研究方案。電影學者孫建業在沙茨研究的基礎上,對好萊塢類型片時間、空間和人物的關系進一步細化,進行了組合研究,將其分為限定時間下的封閉空間敘事和非限定時間下的封閉空間敘事。“當空間被封閉,時間也被限定時,故事的戲劇性張力集中在人物與空間的互動上。而時間則相當于二者之間的催化劑,不僅強化了空間自身的封閉性,更加劇了人物與空間的戲劇沖突。即時間決定了人物或者事件的發展,規定了敘事的整體脈絡。因此,在限定時間下的封閉空間敘事中,人物與空間的沖突通過時間來得以淋漓盡致地呈現,更加凸顯了時間的價值。另外,當空間被封閉,而時間卻相對開放時,故事的戲劇性張力則集中在空間與時間的二元對立上。即以空間的不變對抗時間的變,而人物則成為促進二者關系互動的關鍵因素。”本文根據沙茨對時空限定的觀點和孫建業先生對時空限定的細分理念,重新對時空限定進行了排列組合。把時間分成限定時間和非限定時間,把空間分為限定(封閉)空間和非限定(開放)空間。 類型片即是限定時空相互組合的藝術。通過限定時空可以決定影片的類型,通過限定時空的范圍、程度、長短,則可以改變故事的架構和走向,影響主人公的情感抉擇和故事結局。不同限定時空的相互組合,通過放大、強化時空限定、組合后的某一個方面,來達到強化、凸顯類型片的某一種類型特征的效果,成為滿足觀眾內心深處情感需求和審美期待的最佳催化劑。
“限定時間+限定空間”組合, 可以營造緊張感和懸念。這種組合方式是對時間和空間的雙重限定,也是類型電影中最接近戲劇“三一律”一時、一地、一事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簡化了繁雜的情節,強化了戲劇沖突。時間限定可以營造緊張感和懸念,空間的限定可以制造戲劇沖突,主人公則在時間、空間二維限定所產生的雙重壓力下被迫采取行動,激發出自我潛能,影響事件的發展方向和最終結局。好萊塢電影大師希區柯克主張電影應該制造懸念,讓觀眾緊張、焦慮,從而持續保持對影片的關注力。在類型電影中,時間限定(Deadline)就是制造懸念的一種常用手段。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南軍把北軍俘虜關在條件簡陋的空地上,在四周畫上白線,并筑起圍墻,哨所。北軍俘虜只要越過白線,南軍哨兵就開槍將其擊斃。于是這條線就被稱為“Deadline”(死線)。“Deadline”后來被美國人廣泛用于時間的終結點,意指不能逾越的限定時間。類型電影的限定時間就是制造一個人為的時間終結點,主要人物一旦越過這個時間結點,就會有生命危險或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損失。這種設置的好處是對時間刪繁就簡,避免冗長拖沓,易于制造緊張感和危機感。讓觀眾覺得主人公根本不可能在限定時間到來之前做好準備,救出人質或戰勝敵人,進而下意識地進行角色替換,與主人公產生同樣緊張、焦慮的情緒。此外,根據“三一律”理論,戲劇沖突在限定的空間中才可能發生。 限定空間易于制造敵我雙方的矛盾沖突,而這種沖突由于地理空間的封閉性和環境空間的局促性讓人無從逃遁,并且在時間限定的壓力下不可避免、不可調和地最終爆發。這種模式在好萊塢動作片、西部片、戰爭片、懸疑片中都很常見。例如,好萊塢西部片《正午》就是小鎮警長搶在匪徒正午12點乘火車到達小鎮之前的一天時間內準備戰斗的故事。對時間、空間的雙重限定讓這部情節簡單的西部片一直成為美國電影史上的經典。 在國產類型電影中,諜戰片和戰爭片的時空雙重限定屬性最為明顯。
近年拍攝的很多國產諜戰片在時間、空間上都具有雙重限定性。必須在某一個時間結點之前完成任務,否則就會失敗,失敗的代價則非常高昂,可能對革命造成巨大損失。時間的緊迫性促使人物行動產生嬗變,能激發出前所未有的潛能來應對挑戰。諜戰片的空間大都設置在敵人內部一個相對封閉的特定環境中,例如幽森的古堡、陰暗的刑訊室、牢房、奢華的夜總會。空間的封閉有利于集中觀眾的注意力,制造激烈的戲劇沖突,更好地刻畫人物性格。當限定時間越來越近時,主人公與空間的矛盾空前激化,終于在時間的壓力下做出了抉擇,改變了故事的方向和結局。而這種抉擇通常都要付出重大代價,甚至犧牲自我。例如,《紫蝴蝶》《色·戒》,這兩部諜戰片的時間限定圍繞著倒計時的對敵暗殺行動展開,空間則限定在上海租界內。《紫蝴蝶》設置了一個三重暗殺的局中局。按照日本特務的計劃,在最后到來的暗殺行動中,暗殺與被暗殺雙方都被除掉,但意料之外的小人物最后闖入夜總會,導致大家同歸于盡。《色·戒》中主人公王佳芝在時間的壓力下,愛情戰勝了理智,在珠寶店內出賣了同志,導致了暗殺行動失敗。漢奸在上海租界內戒嚴抓人,自己和同志悉數落網,最后被執行槍決。這兩部諜戰片的空間限定在上海租界內,各方勢力悉數登場,矛盾錯綜復雜。同時也只有在上海租界內,利用租界的特殊環境,暗殺行動才有實施的可能性。特定環境為故事情節的開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和可能。隨著暗殺行動逐漸準備就緒,觀眾在時間的限定下感到巨大的壓力,暗殺能成功嗎?這種懸念始終攫取觀眾的心。隨著暗殺行動即將付諸實施,這種壓力無形中越來越強,觀眾也越來越緊張,而這正是影片的魅力所在。
這種以暗殺為時間結點,特定空間為典型環境的時空限定類型片還可以有多重變種。例如,時空限定如果加上中國功夫和俠義精神,就演變成了武俠諜戰片。我們再來看一部武俠諜戰片《十月圍城》。該片把故事限定在孫中山來香港與同盟會全國各地代表開會的一天時間內,在英屬殖民地香港島的主要街道上,展開清朝刺客與同盟會保鏢之間暗殺與保護的殊死搏斗。該片從頭至尾貫穿了一個懸念——革命黨人喬裝打扮成孫先生的計劃能騙過刺客嗎?孫先生來香港能平安脫險嗎?一天的時間不斷過去,街道空間逐漸縮小,敵我雙方的沖突愈發激烈,影片的暴力色彩愈發濃厚。隨著革命黨人為了拖住刺客不斷慘烈犧牲,觀眾緊張、焦慮的心情也隨之增長。片中的革命黨人不斷看表,時間在緊張焦慮的觀影心態下產生畸變,讓觀眾覺得一天的時間過得極其漫長。當革命黨人犧牲殆盡,孫先生的座駕在狹窄街道上無處躲藏時,空間被壓縮到最小,決戰時刻也最終到來。喬裝打扮的革命黨人為保護孫先生犧牲了自己,與敵人同歸于盡!影片結尾,孫中山平安離開香港。觀眾的情緒終于得到了釋放,懸念揭曉,時空限定解除。
相比之下,《風聲》《誰是臥底之王牌》的時間限定在敵人圍剿我方同志前送出情報的送信行動展開。空間限定則更加封閉、逼仄,變成了幽森的古堡和恐怖的刑訊密室。目的就是讓觀眾置身于懸疑驚悚的氣氛中,產生緊張感和壓迫感,強化敵我雙方的精神和肉體較量,從而使影片富于懸念。在狹小的刑訊密室和陰暗的牢房,敵我雙方斗智斗勇,人性的崇高善良、堅強勇敢、陰暗丑陋、自私貪婪暴露無遺。影片的戲劇性也在這一短兵相接的過程中得到了空前的強化,讓觀眾的心靈為之震撼!主人公最后在時間限定之前,終于果斷采取了行動,以自我犧牲為代價打破了空間限定,用自己的尸體把情報傳遞出去。這種諜戰片的時空限定類似法國作家讓·保羅·薩特于1946年創作的存在主義經典話劇《死無葬身之地》。影片講述的是二戰時期法國地下抵抗組織的一群游擊隊員被納粹德軍和維希政府的法奸抓獲,在幾個小時的刑訊折磨后被集體槍決。是什么讓觀眾對該劇百看不厭、印象深刻呢?答案就是對時間、空間的嚴格限定。幾個小時之后就要被槍斃,刑訊室和牢房的狹小封閉空間里,在遭受酷刑折磨的特殊環境下,展示人性的各種可能。把戲劇“三一律”一時、一地、一事的創作優勢幾乎發揮到了極致! 而這幾部諜戰片在時空限定方面和《死無葬身之地》高度相似,充分借鑒了戲劇的經典理論。
戰爭片與諜戰片類似,與生俱來地具有時間、空間的限定性。時間是在某一個限定時間結點前達到戰略目的,消滅或者阻擊敵人;空間是交戰雙方的戰場。戰場不是普通的生活空間,而是一個反人性的特殊環境,可以放大人性的冷酷、勇敢、殘忍、丑陋。人在這種限定空間中的表現也與日常生活空間有很大不同。吳宇森的《赤壁》時間限定是刮東風的時間段,空間限定是長江兩岸水師戰場。東風一到,孫劉聯軍火燒曹操戰船,取得戰爭的勝利。為了增強時間的緊迫性,影片還設置了小喬只身渡江用美色拖住曹操,通過表演茶藝為周瑜贏得時間的橋段。趁此時機,諸葛亮借來東風,周瑜果斷發動火攻,率領水師殺過長江,贏得赤壁之戰的勝利。馮小剛的《集結號》是一部現代戰爭片,故事圍繞解放戰爭時期一個連的隊伍掩護大部隊撤退展開。時間結點是吹號,聽不到號聲,就要戰斗到最后。時間結點沒有到來,敵人越打越多,陣地即將失守!空間限定愈發逼仄,于是戲劇沖突爆發,高潮到來,主人公做出了死守陣地、全連犧牲的抉擇。影片懸念是:集結號到底吹了沒有?戰士們對此意見不一,戰后的尋訪對此也莫衷一是。這種懸念是在限定時間下產生的,在戰場空間下強化的,在戰后很長時間內主人公積極尋找,并且渴望證實的。影片最后,在廢棄的煤礦里找到全連戰士的尸骨,英雄被莊嚴安葬。葬禮上,集結號終于吹響,暗示著遲到的時間結點最終到來。懸念揭開,觀眾感動,情感釋放。以上兩部戰爭片中都各自存在一個懸念符號——“東風”和“集結號”。而時間限定就是“東風”到來,“集結號”吹響。“東風”會來嗎?“集結號”會吹響嗎?圍繞著這種疑問,戲劇沖突得到不斷強化,人物與不斷壓縮的空間矛盾激化,影片戲劇化達到高潮。由此可見,戰爭片的時空限定有著強化懸念、加強戲劇沖突的驚人效果。
相比之下,《辛亥革命》《太行山上》《百團大戰》等革命歷史題材戰爭片沒有遵循類型電影的模式進行編劇,無視一時、一地、一事的“三一律”創作原則,不注重時空限定,大都采用了宏大敘事策略編劇。一部兩個小時的影片中多時、多地、多事,時空轉換頻繁,時間跨度太長,空間跨度太大,多個事件敘事繁雜,多場戰役來回切換,導致主題不夠鮮明,觀眾注意力分散,剛剛被情節吸引,劇情馬上跳躍,無法產生必要的懸念。這種戰爭片無視類型電影創作規律,故事性不強,主題分散,更加接近紀錄片的敘事風格。為了宣傳的需要,把一個歷史事件或一段革命時期硬性包裝成類型片模式,時空組合、敘事模式對觀眾缺乏吸引力,導致票房慘淡。
“非限定時間+限定空間”組合在大多數武俠片和懷舊愛情片中較為常見。武俠片的矛盾沖突較其他類型片更為激烈。人物需要近距離生死搏斗,充分對抗,這就決定了人物需要處在相對狹小、固定的空間環境中。這樣也有利于展示確定的人物關系,增強影片的情節力度。大部分武俠片的時間雖然是非限定的,沒有出現時間結點,但是為了配合影片的暴力性和緊張感,通常都不會很長,著重講述一段固定時間內發生的故事。 托馬斯·沙茨在《好萊塢類型電影》一書中提出了類型的“圖像志”概念,即“把藝術品中的形象、主題、題材等加以鑒定、描述、分類、解釋的學科”。他認為“圖像志包含了一個流行故事的不斷重復而產生的敘事和視覺編碼過程。其反映了一套價值系統,而這個價值系統定義了它的特定文化社區,并延伸到構成它的實物、事件和角色類型之上。每種類型內涵的價值和信仰系統——它的意識形態和世界觀——決定了其角色的演員挑選、問題(戲劇性沖突)和這些問題的解決辦法”。沙茨在“圖像志”的理論基礎上,將好萊塢類型電影中的角色和場景所構成的空間關系稱為“沖突的社區”。“沖突的社區”即類型片的“限定空間”,故事情節發生、展開的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 例如,《龍門飛甲》的限定空間是嘉峪關的龍門客棧。圍繞著典型環境——小小的沙漠客棧,典型人物——忠良俠客、西廠密探、韃靼商隊、客棧伙計、戍邊官軍、綠林豪杰等各路人馬互相提防、互相試探,展開了激烈沖突和殊死搏斗。正是由于客棧的特殊典型環境,才會聚了各路人馬;正是由于其空間狹小局促,才加劇了人物之間的沖突、對抗,推進了情節的加速發展。《龍門飛甲》在時間上展示的是發生在龍門客棧幾天之內的故事,有利于情節緊湊,也加劇了故事的緊張感。 另一部武俠片《墨攻》的限定空間是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小國梁國的都城,圍繞著梁城展開了趙國軍隊攻城與梁城軍民守城的對抗。趙國大將巷淹中是征伐者,墨者革離是保護者,梁王為首的君臣是搖擺其中的兩面派。圍繞著小小梁城,各方勢力你爭我奪,激烈的攻防戰讓觀眾目不轉睛。戰爭間隙的權力斗爭是第二條敘事線索,同樣緊緊圍繞梁城攻防展開,人性的陰暗卑鄙、自私齷齪比戰爭更加驚心動魄。《墨攻》在時間上沒有限定的結點,但是同樣比較緊湊,是趙國攻城期間幾個月內的故事。《天地英雄》圍繞保護佛骨舍利,大唐校尉與馬賊展開的殊死搏斗。故事的空間由兩隊人馬在西域絲綢之路上相互追逐著展開,大漠孤煙、黃沙漫天的絲綢之路是故事發展的主要空間環境。隨著情節發展,空間不斷擠壓,最后校尉李被迫選擇一座邊塞孤城作為與馬賊決戰的地點。在限定空間下保護佛骨舍利的大唐護衛們死傷殆盡,高潮也隨之到來。而《葉問1》《葉問2》 和《霍元甲》的善惡最終對決則都是在狹小的比武擂臺上完成的。《霍元甲》的最終比武對決在上海武館內。《葉問1》的故事限定空間在佛山,主人公與占領佛山的日本侵略者比武。到了《葉問2》,主人公來到香港,與英國拳王比武。葉問一生中的兩個主要故事,按照限定空間和非限定時間的模式,拍攝成了兩部武俠片,都是票房大熱。如果合二為一,打破空間的限定性,必然會導致主題不夠鮮明,影響影片的類型化特征。這兩部人物傳記片時間都拉得較長,通過講述主人公一生中幾個精彩的事件,彰顯其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
懷舊愛情片是以空間的不變對抗時間的變化,構成了空間與時間的二元對抗,用主人公的行為凸顯出愛情堅貞、命運無常,讓人感受到一種哪怕時光流逝,縱然遠隔千里,愛情依舊永恒的偉大力量。張藝謀的《我的父親母親》講述了插隊下鄉的知識青年和鄉村女孩之間的愛情故事。故事的空間環境限定在一個小山村,來村里小學教書的知青父親被當成右派抓走了。父親為了看母親,逃回來繼續教書,又被村干部抓走,而母親依然在小山村等著父親,其間的時間跨度有幾年。結尾用黑白膠片拍攝父親去世,學生送葬,時間跨度更是達到了幾十年,而空間仍然是小山村。影片最后一個場景,時間又回溯到年輕時的母親給父親送飯,奔跑在春天里的山村小路上!營造出歲月流逝、愛情永恒的藝術氣息。 如果說《我的父親母親》是張藝謀對知青愛情的禮贊,那么他的另一部懷舊愛情片《歸來》與其結構相似,但是更加具有批判性和悲劇色彩。《歸來》的空間設置是家和車站。妻子與丈夫在車站會面,目睹逃回家的丈夫被再次抓走,撕心裂肺,痛苦不堪。丈夫經歷了反右斗爭、“文革”下放,經過20年勞改后終于歸來,妻子卻不堪承受組織壓力和社會歧視精神失常,每個月5號定期從家去火車站等丈夫回家。張藝謀用車站空間不斷對抗時間,有意拉長時間的結構設置,從中年到老年,每個月5號夫妻二人都到車站等待,執著地不與時間妥協,終身捍衛著失去的愛情。如此有力度的情節,表現出中國知識分子愛情的堅貞、執著,也讓《歸來》成為中國懷舊愛情片的經典里程碑。
有意思的是,很多懷舊愛情片的空間環境喜歡定位于民國時代的上海,以帶有海派風格文化印記的男女主角講故事。《茉莉花開》《長恨歌》《理發師》等都是如此。侯詠導演的《茉莉花開》改編自蘇童小說《婦女生活》。故事空間始終依托上海,展示了茉、莉、花三代上海女性的愛情故事。“茉”“莉”兩代母女依附于男性,遭到無情拋棄,自尊自強的“花”不斷抗爭,終獲幸福。在這里,上海見證了三代女性的愛情經歷以及失敗與成功。時空對抗的結構設置讓觀眾見證了時代的變遷和女性的覺醒。 另一部以上海為限定空間的懷舊愛情片是關錦鵬導演的《長恨歌》,根據上海著名女作家王安憶同名小說改編。女主角王琦瑤一生中有四個戀人——國民黨高官、文青攝影師、民族資本家的兒子和上海小流氓。每個人都行色匆匆來了又走,分別出現在她生命中的一段時間里,帶給她痛苦、甜蜜的回憶,只有她始終生活在上海,感受著時光飛逝、青春不在、歲月變遷、愛情枯萎。為什么民國上海、異國情調、海派文化、摩登時尚成為中國懷舊愛情片的主要限定空間環境呢?本文認為,上海成為懷舊愛情片的限定空間有以下原因:首先,上海自1843年開埠通商自由貿易,各國列強攜帶金融資本和西方文明紛至沓來。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成為中國最文明開化的城市、亞洲的金融中心、遠東最大的貿易港口,資本主義市場空前繁榮。成熟的市場吸引了大量金融買辦,成就了大批富裕的城市中產階層,為中產階級的愛情造就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其次,上海是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租界最集中的城市,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內是大量外國貿易公司駐華總部所在地。華洋雜處,文化、服飾、飲食、娛樂等摩登時尚、文明開化引領中國風氣之先,形成了極富異國情調的海派文化,為浪漫愛情滋生造就了合適的文化土壤。再次,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在1949年后被香港取代,愛情片所呈現出的中產階級情感在新中國成立后夭折,美好的愛情生活成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心中思念的對象。民國上海作為逝去不遠的歷史風景,與新中國上海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風尚等各個方面有巨大差異。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吸收了現代西方文明的愛情也容易引起觀眾的好奇心,產生觀影沖動。最后,民國上海造就了一大批文學家、藝術家、作家和電影導演,李叔同、張愛玲、王安憶、蘇童等文學家,夏衍、蔡楚生、費穆等知名導演都曾生活在上海,他們對上海有豐富的生活體驗和情感回憶,上海也自然成為他們創作的對象。他們的作品處處透露出時尚浪漫的“小資產階級情調”。服裝是長袍馬褂、西裝革履、旗袍卷發、歐式長裙;飲食是上海本幫菜、法式西餐;建筑是巴洛克大樓,哥特式別墅;交通是有軌電車、人力黃包車;娛樂是看電影、跳交誼舞;社交是喝咖啡、打麻將;男主角是留學歐洲、日本,接受西方現代文明教育的洋派青年;女主角是本地民族資產階級的大家閨秀和名門淑女。這樣的愛情故事更接近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更符合人性追求美好物質生活的夢想,或者說更加羅曼蒂克,比階級斗爭和階級革命考驗下萌生的“無產階級革命友誼的升華”顯然要更有觀賞性和故事性。
注釋:
① [法]布洛瓦:《詩的藝術》,任典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32頁。
② [加]安德烈·戈德羅:《從文學到影片:敘事體系》,劉云舟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16頁。
③ [美]托馬斯·沙茨:《舊好萊塢/新好萊塢:儀式、藝術與工業》,周傳基、周歡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頁。
④張會軍、黃英俠編:《電影理論:敘事分析與本體研究》,中國電影出版社,2014年版。
⑤[美]托馬斯·沙茨:《好萊塢類型電影》,馮欣譯,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版,第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