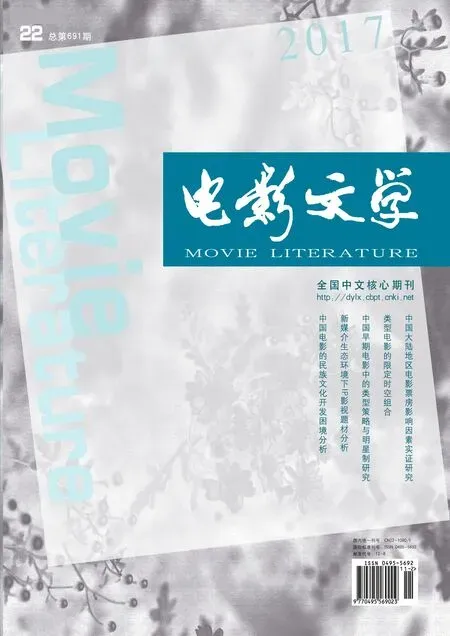中國(guó)電影的民族文化開(kāi)發(fā)困境分析
李朝陽(yáng) 周 園
(中國(guó)勞動(dòng)關(guān)系學(xué)院,北京 100048)
梅特·希約特曾把電影的文化因素分為三個(gè)層次:第一層次是晦澀的難以溝通的電影文化因素;第二層次是可以轉(zhuǎn)換的電影文化因素;第三層次是國(guó)際化的電影文化因素。這三個(gè)層次中決定跨文化傳播效果的關(guān)鍵在于第二層次,即在國(guó)際化與本土化的雙重視域中進(jìn)行“整合”。梅特·希約特主要是從空間維度,即共時(shí)性的層面提出了這一層次劃分。實(shí)際上,對(duì)于所有的地方文化而言,這種整合還或多或少地包括時(shí)間維度,即歷時(shí)性的層面。對(duì)于中國(guó)這樣有著悠久歷史的國(guó)家而言,如何提煉自身的歷史文化資源,同時(shí)又使那些資源能夠符合當(dāng)下的審美習(xí)慣和社會(huì)接受心理,從空間、時(shí)間兩個(gè)維度出發(fā),整合電影民族文化資源,增強(qiáng)自身的文化軟實(shí)力,從長(zhǎng)遠(yuǎn)來(lái)看,將是對(duì)中國(guó)電影最大的利益保護(hù)。
一、民族與世界
回顧中國(guó)電影史,第五代導(dǎo)演曾經(jīng)使中國(guó)電影真正進(jìn)入了國(guó)際視野,雖然后來(lái)又經(jīng)過(guò)第六代導(dǎo)演的努力,但中國(guó)電影在國(guó)際電影舞臺(tái)上似乎顯得后續(xù)乏力,也沒(méi)有誕生新的有影響力的國(guó)際導(dǎo)演,其中一個(gè)原因就在于跨文化傳播的天然障礙。
《銀皮書(shū):2011年中國(guó)電影國(guó)際傳播研究年度報(bào)告》指出:引起外國(guó)觀眾關(guān)注度最高的文化符號(hào)是中國(guó)功夫,占54.5%。“從電影類(lèi)型上看,外國(guó)觀眾較為青睞動(dòng)作、功夫類(lèi)中國(guó)電影,顯示出外國(guó)觀眾對(duì)我國(guó)功夫文化的喜愛(ài)。”自從李安的《臥虎藏龍》(2000年)榮獲包括奧斯卡最佳外語(yǔ)片在內(nèi)的四項(xiàng)大獎(jiǎng)之后,中國(guó)電影人就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如何打入國(guó)際市場(chǎng)上,如張藝謀的《英雄》(2002年)、陳凱歌的《無(wú)極》(2005年)、馮小剛的《夜宴》(2006年)等,但經(jīng)過(guò)十年中國(guó)古裝大片輪番亮相之后,這些電影紛紛折戟,“中國(guó)式大片”創(chuàng)造力的匱乏逐漸顯現(xiàn)。顯然,原因并不在于國(guó)外沒(méi)有市場(chǎng),而在于國(guó)內(nèi)導(dǎo)演不善于此類(lèi)電影題材的開(kāi)發(fā)和駕馭,不善于以科學(xué)的市場(chǎng)營(yíng)銷(xiāo)的方法研究受眾,不善于將民族文化的內(nèi)涵植入電影之中。
此外,中國(guó)電影在跨文化傳播過(guò)程中的短板,還體現(xiàn)為不善于以電影特有的方式表達(dá)思想。2013 年初英國(guó)《衛(wèi)報(bào)》網(wǎng)站一篇文章再次提到字幕翻譯的問(wèn)題:“《泰囧》的幽默,中國(guó)色彩太濃,無(wú)法獲得更廣泛的影響力。”在跨文化傳播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跨文化適應(yīng),從心理學(xué)層面而言,它是指外國(guó)人在新的文化環(huán)境中的心理反應(yīng)和社會(huì)整合,側(cè)重個(gè)體價(jià)值觀和態(tài)度的變化以及行為變化的研究,因?yàn)椤拔业恼Z(yǔ)言的邊界就是我的世界的邊界,語(yǔ)言的不同導(dǎo)致了世界的不同”(維特根斯坦語(yǔ))。
一般來(lái)說(shuō),文化的構(gòu)成包括:一個(gè)民族的歷史、傳統(tǒng)、宗教思想、價(jià)值觀念、社會(huì)組織形式、風(fēng)俗習(xí)慣、政治制度、社會(huì)發(fā)展階段(工業(yè)化程度、科技水平等)。電影語(yǔ)言本質(zhì)上而言是造型語(yǔ)言,電影中的文化傳播,就是通過(guò)具有比語(yǔ)言文字更大的通約性的視覺(jué)語(yǔ)言、行為語(yǔ)言、音樂(lè)語(yǔ)言去傳達(dá)思想和價(jià)值觀念,并以此透過(guò)電影的表面影像系統(tǒng),呈現(xiàn)出電影內(nèi)在的深層意義結(jié)構(gòu)。上述舉例中的中國(guó)武俠電影的共同弊端,就在于浮于表面,未能充分表現(xiàn)出電影這種藝術(shù)形式應(yīng)該包含的內(nèi)在的思想文化價(jià)值和哲思意趣,因而流于視聽(tīng)奇觀,而無(wú)法帶來(lái)對(duì)民族文化的更高層次的體味和欣賞。“影像表達(dá),并不僅僅如字面意思所呈現(xiàn)的那樣,是指電影鏡頭傳達(dá)的信息和意義。從文化的本質(zhì)內(nèi)蘊(yùn)來(lái)看,它對(duì)應(yīng)了文化的技術(shù)系統(tǒng)(影像系統(tǒng)) 和價(jià)值系統(tǒng)(表達(dá)系統(tǒng)) 兩大部類(lèi),前者是電影所有視聽(tīng)語(yǔ)言和表現(xiàn)手法的總和,構(gòu)成電影文化的‘淺層結(jié)構(gòu)’;后者則是影像表達(dá)過(guò)程中所呈現(xiàn)的價(jià)值取向、審美情趣、思維方式等,屬于電影文化的‘深層結(jié)構(gòu)’。前者是顯性的,后者是隱性的,前者是由可以把握的諸如構(gòu)圖、色彩、鏡頭運(yùn)動(dòng)、剪輯等組成,后者則是指潛藏在各種視聽(tīng)語(yǔ)言背后的知識(shí)、價(jià)值觀、意向、態(tài)度等。”
因此,對(duì)中國(guó)電影而言,在跨文化傳播以及實(shí)現(xiàn)民族文化接軌國(guó)際市場(chǎng)的過(guò)程,從開(kāi)發(fā)策略上而言,以民族的文化為內(nèi)容,以國(guó)際化的呈現(xiàn)為形式,應(yīng)該是中國(guó)電影的一個(gè)基本定位。這不僅包括對(duì)民族文化、歷史、風(fēng)俗習(xí)慣、價(jià)值觀念進(jìn)行針對(duì)國(guó)際市場(chǎng)的有目的性的梳理和提煉,也包括在電影語(yǔ)言的運(yùn)用上以及包裝和營(yíng)銷(xiāo)上采取國(guó)際的通用方法去執(zhí)行。李安的《臥虎藏龍》就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和美國(guó)西部類(lèi)型片的創(chuàng)作基調(diào)進(jìn)行完美融合的典范,不僅得到東方觀眾的認(rèn)同,也得到西方觀眾的喜愛(ài),既表達(dá)了東方的思維模式和故事內(nèi)容,又采取了西方的表現(xiàn)形式和視覺(jué)圖譜。
二、歷史與當(dāng)下
在中國(guó)電影的對(duì)內(nèi)傳播方面,中國(guó)電影的民族文化對(duì)于觀眾而言的“共通感”也經(jīng)常遭到阻隔與撕裂,這直接體現(xiàn)為電影語(yǔ)言的所指功能被能指取代,文化符號(hào)的深層意義結(jié)構(gòu)被抹平,電影流于敘事和影像的表面,顯得空洞、沒(méi)有深度。從大的方面而言,有三個(gè)原因:政治文化的干預(yù)、外來(lái)文化的影響、大眾文化的擠壓。
(一)政治文化的干預(yù)
近一百年來(lái),中國(guó)民族文化一直在各種風(fēng)起云涌的政治運(yùn)動(dòng)中被東拋西擲,一直處于被某種占優(yōu)勢(shì)地位的政治文化所鉗制的狀態(tài),而失去了一種文化自然而然地發(fā)展和傳承的機(jī)會(huì)。以儒家文化為例,遭遇了五四運(yùn)動(dòng)、“文革”這兩次大的打壓和某種閹割式的改造,從而削弱了這種文化在傳承上的實(shí)際影響力。換言之,一種文化即使在它的表面符號(hào)上,如建筑、器具、服飾、書(shū)籍、儀式等方面得到了相對(duì)完整的傳承,但這種文化真正的意義傳承依然可能出現(xiàn)斷層,這種斷層不一定體現(xiàn)在外部世界,而是體現(xiàn)在人對(duì)這種文化的認(rèn)知、情感、觀念、價(jià)值判斷以及潛移默化養(yǎng)成的日常行為習(xí)慣和生活風(fēng)貌中。從這種意義上而言,儒家文化在中國(guó)歷史上,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宗教的角色,以一種無(wú)神論的姿態(tài),提供了行為自律和內(nèi)心安寧的可能,具有一定的抽象超越性和終極關(guān)懷的特點(diǎn),因此具有某種宗教性,所以才能夠在全世界上獨(dú)樹(shù)一幟地成為東方文化的代表。然而,由于在傳承的過(guò)程中,儒家文化被人為地割裂,從而造成中國(guó)人對(duì)于這種文化發(fā)自?xún)?nèi)心的陌生感,這種“無(wú)根”的文化漂泊憂(yōu)傷,并非在短期內(nèi)能夠得以療愈。如同寧瀛的北京三部曲電影《找樂(lè)》《民警故事》和《夏日暖洋洋》一樣,而賈樟柯的《世界》也是一部有關(guān)中國(guó)當(dāng)下文化焦慮的寓言,回應(yīng)了文化符號(hào)根基喪失所帶來(lái)的精神痛苦。故事里的年輕人都住在公園里,一起工作、吃飯、游蕩、爭(zhēng)吵。他們都來(lái)自外地,在2003年的北京這個(gè)不屬于他們的世界里幻想、相愛(ài)、猜忌、和解。城市壓倒一切的噪音,讓一些人興奮,讓另一些人沉默。這座公園布滿(mǎn)了仿建世界名勝的微縮景觀,從金字塔到曼哈頓只需10秒。在人造的假景中,生活漸漸向他們展現(xiàn)真實(shí):一日長(zhǎng)于一年,世界就是角落。
“存在”一詞在文化意義上的“無(wú)根”,即是哲學(xué)意義上的“虛無(wú)”,如果連接民族情感的文化符號(hào)只具有表面上的能指意義,而不具備內(nèi)在含義的延伸功能,那么這種文化在歷史傳承中的再生能力就必然顯得極為有限。而且,這種“無(wú)根”的社會(huì)心理狀態(tài)體現(xiàn)在電影的審美效果上,則是觀眾對(duì)于電影藝術(shù)語(yǔ)言解讀的困難、陌生乃至漠然。一種來(lái)自觀眾的對(duì)于民族文化集體的陌生感一旦蔓延開(kāi)去,則會(huì)以一種釜底抽薪的姿態(tài)迫使電影藝術(shù)做出違背民族文化表達(dá)初衷的表達(dá)形式,因?yàn)橥晟贫窒到y(tǒng)的民族文化符號(hào),是“民族的此在”構(gòu)成的標(biāo)志,也是一個(gè)民族審美判斷力的基礎(chǔ),如果由于現(xiàn)實(shí)生活圖景被破壞,從而導(dǎo)致觀眾無(wú)法解讀具有民族文化美學(xué)蘊(yùn)含和藝術(shù)價(jià)值的電影,那么民族電影必然遭到扭曲,電影的產(chǎn)業(yè)化進(jìn)程也必將受挫。
因此,中國(guó)電影對(duì)于民族文化符號(hào)的呈現(xiàn),亟待從外部表達(dá)和內(nèi)部表現(xiàn)兩個(gè)層面入手,挖掘當(dāng)下社會(huì)心理中具有人文意義的焦慮,以及帶有明顯物質(zhì)特征的現(xiàn)代化過(guò)程中的壓力,并力圖創(chuàng)新,發(fā)現(xiàn)新的表達(dá)式樣和手法,做到精英的文化電影與大眾電影的平衡,在共同的文化基礎(chǔ)之上生成具有“通約性”的美感,從而激發(fā)大眾的審美快感,實(shí)現(xiàn)電影對(duì)民族文化符號(hào)的審美轉(zhuǎn)換。
(二)外來(lái)文化的影響
2002年,中國(guó)政府在“十六大”上首次提出發(fā)展文化產(chǎn)業(yè)后,一個(gè)關(guān)于以美國(guó)電影為主的外來(lái)文化的“狼來(lái)了”的比喻就經(jīng)常見(jiàn)諸媒體。顯然,這個(gè)比喻的背后是對(duì)中國(guó)文化自身作為羊的存在的確認(rèn),表達(dá)了中國(guó)電影的不自信和恐慌,甚至曾有一些學(xué)者把美國(guó)電影進(jìn)入中國(guó)院線(xiàn)稱(chēng)為“文化入侵”。雖然“入侵”只是一種比喻,而非實(shí)際狀況,因?yàn)橹袊?guó)觀眾喜愛(ài)并樂(lè)于接受美國(guó)電影、美劇、韓劇等外來(lái)文化,所以不能用“入侵”而只能用“影響”一詞加以描述。但是,這種帶有“敵我”性質(zhì)的文化區(qū)分確實(shí)表達(dá)了當(dāng)時(shí)國(guó)內(nèi)電影界的焦慮。
這種對(duì)于外來(lái)文化影響的心理畏懼感,在近一個(gè)多世紀(jì)以來(lái)一直存在于中國(guó)現(xiàn)代化的進(jìn)程中。由于先前的整體知識(shí)系統(tǒng)都必須遭到更新和揚(yáng)棄,并且這種揚(yáng)棄是在帶著“不得不”的屈辱感的過(guò)程中進(jìn)行的,所以對(duì)于外來(lái)文化的畏懼,盡管可能會(huì)被羨慕、渴望、膜拜等情感遮蔽,但也會(huì)成為中國(guó)人集體無(wú)意識(shí)的某種殘留。正如吉登斯所說(shuō):“焦慮實(shí)質(zhì)上就是恐懼,它通過(guò)無(wú)意識(shí)所形成的情感緊張而喪失其對(duì)象,這種緊張表現(xiàn)的是'內(nèi)在的危險(xiǎn)'而不是內(nèi)化的威脅。”
時(shí)隔15年之后,在今天再次反觀外來(lái)文化對(duì)中國(guó)的影響,依然有過(guò)之而無(wú)不及,且不說(shuō)日常生活中中國(guó)人所依賴(lài)的必需用品有多少來(lái)自美國(guó)、日本、德國(guó)、韓國(guó),但就美國(guó)電影每年在中國(guó)電影票房前十名中所占的比例,以及中國(guó)當(dāng)前幾乎所有有影響力的綜藝節(jié)目的創(chuàng)意全部來(lái)自國(guó)外就可見(jiàn)一斑。如果說(shuō),由于自身原因而導(dǎo)致了民族文化傳承的斷裂,那么,外來(lái)文化無(wú)孔不入的滲透和影響,則是填補(bǔ)了那些斷裂空間的物質(zhì)。這種狀況完美地遵循著物理學(xué)的擴(kuò)散原理,處于真空狀態(tài)下的容器一旦開(kāi)了一條縫,就會(huì)瞬間被周?chē)臍怏w所填滿(mǎn),從市場(chǎng)營(yíng)銷(xiāo)學(xué)的角度來(lái)看,這就是“有需求即被滿(mǎn)足”的生產(chǎn)和銷(xiāo)售原理。
實(shí)際上,從具有建設(shè)性的角度來(lái)看,美國(guó)好萊塢電影的傳播當(dāng)然可以促進(jìn)中國(guó)電影的發(fā)展,關(guān)鍵在于中國(guó)電影是否能夠有效地對(duì)其加以學(xué)習(xí)和利用。美國(guó)的格杜德?tīng)柕热嗽杨?lèi)型電影定義為“是由于不同的題材或技巧而形成的影片范疇、種類(lèi)或形式”。在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當(dāng)許多歐洲電影導(dǎo)演以輕蔑的眼光看待這種類(lèi)型片時(shí),“新德國(guó)電影運(yùn)動(dòng)”的主要導(dǎo)演法斯賓德卻把大眾化的、通俗的情節(jié)劇和他為了造成觀眾思考和分析而使用的新的敘事手段結(jié)合在一起,換言之,即商業(yè)性與藝術(shù)性的結(jié)合、娛樂(lè)性與思想性的結(jié)合。法斯賓德自稱(chēng)是“為德國(guó)觀眾拍攝德國(guó)電影的德國(guó)人”,并認(rèn)為“情節(jié)劇電影是恰當(dāng)?shù)碾娪靶问剑欢绹?guó)人拍情節(jié)劇影片的方式,只要求作用于觀眾的情感,別無(wú)所為,我則想在喚起觀眾感情的同時(shí),為他們提供思考與分析其感受的可能”。法賓斯德借鑒和吸收、研究并創(chuàng)新的做法理應(yīng)成為中國(guó)電影人在面臨新的電影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格局時(shí)學(xué)習(xí)的榜樣。
(三)大眾文化的擠壓
全世界都不得不面臨的一個(gè)困境就是:大眾文化審美趣味的泛濫導(dǎo)致全球電影的思想文化內(nèi)涵逐漸衰落,并在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革新的背景下,日益為商業(yè)利益所驅(qū)使而迎合耳目視聽(tīng)的感官娛樂(lè)。這一點(diǎn),不論從近年來(lái)奧斯卡電影節(jié)獲獎(jiǎng)影片的藝術(shù)質(zhì)量來(lái)看,還是從國(guó)內(nèi)“豆瓣”打同樣分?jǐn)?shù)的電影質(zhì)量來(lái)看,從整體而言,都難以企及10年前、20年前經(jīng)典電影的藝術(shù)水準(zhǔn)。誠(chéng)然,從大的方面分析,這種蔓延全球的理性思維滑坡、知識(shí)層級(jí)被抹平、娛樂(lè)至上的現(xiàn)狀,與文字時(shí)代式微、圖像影像時(shí)代到來(lái)以及信息的爆炸和傳播媒介的技術(shù)革新有著必然關(guān)聯(lián),然而,這只是意味著,在這種時(shí)代背景之下,或迫于市場(chǎng)的壓力,或迫于制片方的要求,或出于省時(shí)省力的考慮,堅(jiān)守藝術(shù)與商業(yè)的平衡顯得更加艱難,但絕不意味著無(wú)法再制作出精品。
表1中各項(xiàng)指標(biāo)能定性、半定量地評(píng)估冰磧湖潰決風(fēng)險(xiǎn)。近年,定量估算冰磧湖潰決風(fēng)險(xiǎn)研究也取得較大進(jìn)展。有學(xué)者將母冰川危險(xiǎn)冰體的體積與湖水體積比值(R)的倒數(shù)定義為冰湖潰決危險(xiǎn)性指數(shù)(Idi),即Idi=1/R,R值越大其發(fā)生潰決的概率越小,并計(jì)算出西藏若干個(gè)冰湖的潰決危險(xiǎn)性指數(shù)變化于0.054~0.73之間。
由宮崎駿執(zhí)導(dǎo)、編劇,吉卜力工作室制作的動(dòng)畫(huà)電影《千與千尋》(2001年),榮獲2003年奧斯卡金像獎(jiǎng)最佳長(zhǎng)篇?jiǎng)赢?huà)獎(jiǎng),同時(shí)也是歷史上第一部至今也是唯一一部以電影身份獲得歐洲三大電影節(jié)之一德國(guó)柏林電影節(jié)金熊獎(jiǎng)的動(dòng)畫(huà)作品。這部電影在日本最終取得了304億日元的票房和約2350萬(wàn)人次的觀看,并超越了《泰坦尼克號(hào)》262億日元的票房,成為日本歷代電影票房排行榜的第一名。《千與千尋》講述了少女千尋意外來(lái)到神靈的世界后發(fā)生的故事。整部電影充滿(mǎn)了日本傳統(tǒng)的文化符號(hào),不僅體現(xiàn)在極具沖擊力的外部影像造型語(yǔ)言中,也體現(xiàn)在人物的內(nèi)部心理、觀念和價(jià)值取向中,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獨(dú)具日本特色的民族電影,但同時(shí),電影又巧妙地借用了西方民間神話(huà)中的“巫婆”形象,和西方現(xiàn)代工業(yè)的機(jī)器,以此作為承載國(guó)際化思想的工具,其文化寓言能夠?yàn)槿澜绲娜撕翢o(wú)障礙地加以解讀。
同樣,作為國(guó)際電影大師的李安也深諳電影的國(guó)際化制作手法。根據(jù)揚(yáng)·馬特爾的小說(shuō)改編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2012年)是一部3D電影,該片在2013年第85屆奧斯卡頒獎(jiǎng)禮上獲得包括最佳導(dǎo)演在內(nèi)的四項(xiàng)大獎(jiǎng)。除了巧妙地選擇了人與神、人與自然、東方與西方這種國(guó)際題材之外,李安在這部電影中成功地做了一次具有劃時(shí)代意義的嘗試:用高科技數(shù)字技術(shù)去呈現(xiàn)如同哲學(xué)一般深邃的藝術(shù)世界。之前,大多數(shù)學(xué)者認(rèn)為,技術(shù)的革新只會(huì)日漸擠壓人文藝術(shù)的生存空間,因?yàn)榧夹g(shù)是以邏輯、分析、判斷、歸納等理性思維方式而運(yùn)作的,因此,當(dāng)這種高清晰度的、主客二分的工具理性介入藝術(shù)創(chuàng)作之中時(shí),必然會(huì)損害藝術(shù)精神所要求的超越性、超驗(yàn)性、模糊性。但是,在這部電影中,李安以實(shí)證的手法給出了相反的答案:技術(shù)完全有可能表達(dá)深層藝術(shù)結(jié)構(gòu)中所蘊(yùn)藏的難以用語(yǔ)言表達(dá)的哲思和趣味。
不論是呈現(xiàn)民族文化的《千與千尋》,還是采用國(guó)際化題材和用高科技呈現(xiàn)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都是在大眾文化在全球文化場(chǎng)中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語(yǔ)境下取得的巨大成功,不僅獲得了國(guó)際聲譽(yù),也贏得了難以企及的票房收入。它們非常雄辯地證明:沒(méi)有絕對(duì)不可能的環(huán)境,而只有不知道如何適應(yīng)環(huán)境和利用環(huán)境的電影人。對(duì)于跨文化傳播中遇到的各種問(wèn)題,正如李安所說(shuō):“這個(gè)問(wèn)題只有適應(yīng),沒(méi)有解決之道。”
總之,在全球化和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電影制作者的國(guó)籍、某一地方文化題材的使用,已經(jīng)不再是決定一部電影的文化身份的根本要素,而這種文化內(nèi)在的文化邏輯才是一部電影文化身份的根本標(biāo)志。在當(dāng)前地方文化資源可以不分國(guó)界地為他者文化無(wú)償開(kāi)發(fā)的背景下,打造具有中國(guó)民族文化特點(diǎn)的電影精品,是中國(guó)電影的核心競(jìng)爭(zhēng)力所在。中國(guó)電影在文化內(nèi)容上的精心選擇和提煉,在文化傳播形式上的國(guó)際化努力和嘗試,在電影語(yǔ)言的使用技巧上向成功案例的學(xué)習(xí)和借鑒,越發(fā)顯得迫切而又至關(guān)重要。中國(guó)電影人需要深刻體察中國(guó)當(dāng)下的社會(huì)心理、審美趣味、文化根基或文化“無(wú)根”的心態(tài)結(jié)構(gòu),同時(shí)對(duì)民族文化有機(jī)地進(jìn)行編碼,此外,以一種國(guó)際化的形式加以呈現(xiàn),以更好地尋求未來(lái)的發(fā)展之路。
注釋?zhuān)?/p>
① [美]梅特·希約特:《丹麥電影與國(guó)際化戰(zhàn)略》,《后理論:重建電影研究》,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714 頁(yè)。
② 中國(guó)文化國(guó)際傳播研究課題組,編著:《銀皮書(shū):2011年中國(guó)電影國(guó)際傳播研究年度報(bào)告》,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2 年版,第183-184 頁(yè)。
④ 《英報(bào)分析〈泰囧〉在美票房為何變囧?》,新華網(wǎng),http: //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2/15/c_ 124346890.htm。
⑤ 單波:《跨文化傳播的問(wèn)題與可能性》,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10 年版,第145 頁(yè)。
⑥ 陳曉偉:《中國(guó)電影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維度、現(xiàn)狀及方法》,《鄭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4年第6期。
⑦ [英]安東尼·吉登斯:《現(xiàn)代性自我認(rèn)同》,趙旭東等譯,三聯(lián)書(shū)店,1998年版,第 49頁(yè)。
⑧ 邵牧君:《西方電影史概論》,中國(guó)電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頁(yè)。
⑨⑩ 汪流:《電影編劇學(xué)》,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頁(yè),第201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