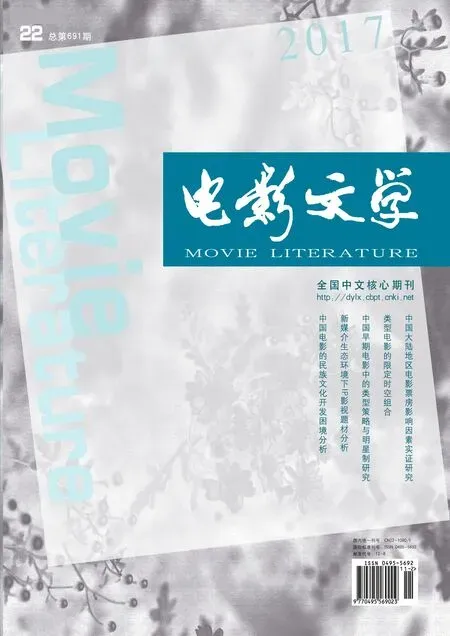詹姆斯·艾弗里對文學作品的經典改編
蒙麗芳
(桂林旅游學院外國語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6)
1986年的一部改編自E.M.福斯特經典小說的影片《看得見風景的房間》,讓1928年出生的美國導演詹姆斯·艾弗里聲名鵲起,在好萊塢嶄露頭角。而之后其所執導的《莫瑞斯》《霍華德莊園》《伯爵夫人》《長日留痕》等改編自英國文學名著的影片,不僅讓詹姆斯·艾弗里成為好萊塢“文學電影”的金字招牌,而且更是以優雅、懷舊、憂郁的藝術風格受到全世界影迷的追捧。詹姆斯·艾弗里在其改編影片中,一方面借鑒了英國經典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情節、場景等元素,讓影片呈現出濃郁的英倫風情;另一方面又將更多商業性、娛樂性和現代元素融于影片中,滿足著現代觀眾快節奏的觀影習慣,讓觀眾在有限的光影時空內感受著文學作品獨特的情感和思想內涵。基于此,本文從詹姆斯·艾弗里電影故事主題、人物情節、敘事節奏三個方面對其電影進行分析,為更好地探究其文學改編電影的藝術特征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故事主題由繁入簡
從1986年《看得見風景的房間》開始,詹姆斯·艾弗里就逐漸以反傳統的方式對文學名著進行改編,其中最為明顯的是他充分認識到好萊塢電影商業價值和觀眾的認知能力,于是他在其文學改編電影中普遍采用故事主題單一化的大眾化策略,保證故事內容的可理解性或欣賞性,讓故事主題與觀眾內心緊密聯系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弱化了文學作品哲理化的主題模式,讓故事性和思想性更容易被現代觀眾接受。
以《看得見風景的房間》為例,原著小說主題較為復雜抽象,作者福斯特通過中產階級小姐露西、巴特利特、喬治、塞爾西間的愛恨糾葛,一方面宣揚愛情的美好,另一方面極力批判英國僵化平庸、封建保守的社會制度對人性的束縛,凸顯作者對自由、解放及女性主義的態度。而電影《看得見風景的房間》則單純以露西和喬治的愛情為單一主題,沒有花費較大篇幅對英國中產階級社會的糜爛生活進行批判,而是重點突出愛情的美好和力量。影片中忽略了露西對感情的彷徨,而是從一開始就讓其對愛情充滿強烈的渴望,從不懷疑自己的感情,甚至讓露西敢于拋棄小說中的世俗規范。影片這種對原著主題思想的簡單化處理,讓故事具備了明顯的現代性,讓觀眾非常輕松容易地接受了故事內容,在完整而又簡單的故事中形成對人性及其他深刻思想的挖掘和思考。同樣在《霍華德莊園》中,導演也對原著故事主題進行了充分的簡化處理。小說不僅圍繞男女主人公的婚戀,而且還圍繞英國和人類的文明與命運,通過主人公們的褊狹和隔閡表現作者對英國工業社會實利主義的質疑和反思,同時表達對傳統英國農業社會的希冀和向往。對于現代觀眾來說,這種主題過于抽象復雜,如直接移植入影片中則讓影片晦澀難懂。因此,電影《霍華德莊園》中,導演主動地對原著哲理性及議論性內容進行了精簡, 通過主人公海倫對愛情、自由的追求及最終實現夢想的故事將原著主題淡化,同時將原著中海倫和巴斯特階級不對等的愛情竭力塑造為完全平等的愛情關系,讓男女主人公都獲得了更為美好的品質和追求,甚至還故意淡化了女主人公海倫充當第三者的這一不光彩行徑,讓愛情這個永恒不變的主題感染著觀眾,同時宣揚著導演詹姆斯·艾弗里對于人性、道德的個人見解。總之,詹姆斯·艾弗里在其改編電影中出于對電影時空限制和欣賞性及商業價值的考慮,在對原著進行改編時采用了主題簡化的方式,放棄了部分思想負載較深的哲理性內容,強調了電影和小說與觀眾的共通精神。通過簡單的故事主題引發觀眾對故事更深層次內涵的挖掘思考,這樣既保證了影片的商業價值和票房,同時也避免了“重表現、輕思想”的局限性,實現了思想性、藝術性和商業性的完美統一。
二、人物情節適度增減
文學作品擁有較大的時空范圍讓作者進行充分的敘述和思想傳輸,而電影相對小說來說,無論是時間上還是空間上都相對有限,無法將原著內容和思想完整地進行展示,因而必須進行適當的改編,以保證電影的戲劇性和觀眾的可理解性。詹姆斯·艾弗里在其文學改編電影中經常對故事主題進行簡化,因此其必然要對原著小說中的人物、情節進行必要的改編,或增或減或變,只有這樣才能與故事主題形成一致。雖然人物和情節的改編,讓故事較為淡薄,但是卻讓矛盾更為突出,人物形象更為生活化,有助于提升觀眾對影片的觀影興趣和接受程度。以1993年榮獲奧斯卡八項提名的影片《長日留痕》為例,導演詹姆斯·艾弗里對著名小說家石黑一雄同名小說中的人物、情節進行了適度的改編,既淡化了原著濃郁的政治內涵,又凸顯了主人公間的矛盾沖突,讓觀眾在充分領略了英倫文化的同時,也被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所吸引。如原著中,斯蒂文斯作為主要敘述者,通過他的回憶錄讓讀者認識到莊園主人、肯頓小姐、達林頓勛爵、男女管家等形形色色的人物,而影片則是將肯頓小姐作為主要敘述者,將與她和斯蒂文斯感情無關的人物予以刪除,不僅讓觀眾逐漸認識到斯蒂文斯老年階段對年輕時期驕傲、自負的反思和悔意,而且也讓觀眾透過肯頓小姐本人的視角發現其獨立、熱情、浪漫的性格,進而認識理解她與斯蒂文斯之間的反差,形成對兩者矛盾的完整認知,也讓所有主要人物更加飽滿形象。除了對人物形象進行刪減外,影片還根據矛盾發展需求增加了個別人物,例如肯頓的未婚夫本恩。原著中并沒有本恩這個人物的具體描述,而在影片中為凸顯斯蒂文斯人性的弱點,創造性地將本恩設計為敢于反抗、敢于堅持自我的英式男性形象。他對愛情堅定果敢,對未來充滿希望,最終憑借激情贏得了心愛的肯頓小姐。而相比之下斯蒂文斯則總是克制隱忍,選擇逃避,最終讓肯頓小姐厭倦了他的冷漠,嫁給了本恩。在人物設定上,詹姆斯·艾弗里根據美國人的性格特質和矛盾發展需要對原著人物進行了適當刪減和增加,讓電影既保留了原著濃郁的英倫氣息,同時也讓這些人物更為生活化,符合現代審美需求。而在情節方面,導演詹姆斯·艾弗里也是根據矛盾發展需求對很多原著作品進行了適度的增減。以《看得見風景的房間》為例,首先,在影片中導演為適應影片的拍攝需要,刪去了部分不重要的故事內容或對部分情節進行簡化處理。如原著中旅客們在公寓中長談闊論的情節與電影主題的關系較小,被予以刪除。其次,導演還在影片中故意增加了原著沒有的內容,如影片的后半部中,當巴特利特到露西家游玩時,在火車上被車窗外的沙子迷住了眼睛的情節在原著中并沒有。之后巴特利特在火車站內巧遇喬治的情節在原著中并沒有詳細描述,而影片卻對其予以擴充和深化。詹姆斯·艾弗里讓喬治在這一后添加的情景中騎著自行車和巴特利特所乘坐的馬車賽跑,通過這個充滿英式幽默的鏡頭為影片增添了一定的喜劇色彩,同時也含蓄抽象地暗示了兩者間的鴻溝和隔閡。影片最后,喬治與露西返回佛羅倫薩貝托里尼小旅館的情節在原著中只有只言片語,而影片中卻為其增加了額外的內容。導演增加了老少兩位女游客,仿佛當年的巴特利特與露西一樣在旅館內小聲爭論,喬治和露西看到該場景相視一笑,如同看到當年一般。影片通過這些細節的增加或減少,讓影片呈現出更多的戲劇沖突,讓觀眾在觀影過程中情緒一直處于飽滿的狀態中,形成對故事內容和矛盾更為直觀和深層次的理解。同樣在《霍華德莊園》《伯爵夫人》《莫瑞斯》等影片中,導演詹姆斯·艾弗里沒有全盤照搬原著故事中的人物設置和情節設置,而是根據電影戲劇矛盾需求和時空限制,對人物、情節進行了增加刪減,甚至還故意對人物性格和故事發展方向進行了個性化改編,為觀眾展示了一幅幅與原著不同的畫面,讓觀眾產生一種似曾相識而又別有一番風味的觀影感受。
三、敘事節奏對比變化
文學作品敘事節奏一般體現在故事情節的輕重緩急及人物命運的不斷變化上,或者通過不同章節、內容的對比與聯系等關系上,而詹姆斯·艾弗里影視作品的敘事節奏主要通過音樂、鏡頭的起伏、對比、變化及其他各種藝術表現手法或技術來進行表現,不僅讓影片內容和節奏更為鮮明、感性,而且也讓敘事節奏呈現一種動態變化的風格。例如,1991年改編影片《霍華德莊園》就將導演詹姆斯·艾弗里的敘事節奏和風格彰顯得淋漓盡致。作為文學改編三部曲的第三部,《霍華德莊園》敘事節奏體現在整體節奏與局部節奏兩個方面。整體節奏就是影片整體情節、內容的推進發展等,而局部節奏就是對劇中人物的言行、視聽語言等元素的變化運用來形成特殊的敘事節奏。在整體節奏上,影片呈現出松弛有度的節奏,其140多分鐘的故事發展中,影片多數情節的推進較為迅速,人物的動作、語言較為簡潔干練,而鏡頭也切換頻繁,整體上比較集中緊湊。在局部方面,影片通過人物、音樂、鏡頭的對比讓故事呈現不同的敘事節奏。在影片中,導演詹姆斯·艾弗里對人物的運動、行為、語言等內容進行了具體化的對比式呈現,通過可視性形象給觀眾制造極具視覺沖擊的印象,讓故事敘事節奏產生動靜結合的效果。如威爾考克斯夫人的緩慢與身邊其他人物的快速變化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人物對比讓故事在動靜變化的節奏中產生了更多的象征意義,威爾考克斯夫人象征著英國舊時代階級特性,而其他人則代表新時代階級特點。另外,影片還采用鏡頭的對比讓故事呈現出不同的敘事節奏。如影片伊始,導演詹姆斯·艾弗里就連續采用三個明顯固定的長鏡頭描繪霍華德莊園的黃昏,讓觀眾充分體會到英國莊園的寧靜氣氛,接著就采用大量快速轉換鏡頭的相互映襯,烘托威爾考克斯夫人恬靜的氣質。電影第一個畫面鏡頭瞄準了深藍色的裙擺,然后鏡頭慢慢上搖,將威爾考克斯優雅美麗的背影展示給觀眾,之后鏡頭又快速切換至其手中的小花、步伐、面容、家人、仆人等,這種固定長鏡頭和短鏡頭的對比切換讓故事呈現出與眾不同、時快時慢的敘事節奏,讓觀眾在變化的節奏中形成對人物身份、性格的直觀認識。除了通過人物和鏡頭對比讓影片節奏發生動態變化外,詹姆斯·艾弗里還將音樂對比運用到敘事節奏的變化中,并承擔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如電影中,導演將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作為主要背景音樂,當海倫在音樂會上時,背景音樂是緩慢從容的音樂;而當心不在焉的海倫與不顧一切的巴斯特在雨中狂奔時,命運交響曲伴隨著兩個人凌亂的腳步強烈地撞擊著觀眾的心靈。音樂節奏的變化暗示著兩個人內心情緒的變化,這種變化不但讓影片產生了更為急促和緊張的氣氛,而且也為原本輕松舒緩的整體敘事節奏增加了更多的戲劇性,滿足了觀眾的感官需求。同樣在《看得見風景的房間》中,導演詹姆斯·艾弗里也是采用了音樂的對比讓影片敘事節奏產生動靜變化。采用貝多芬樂曲來代表主人公露西對愛的渴望和激情,也讓故事敘事非常緊湊;采用舒曼鋼琴曲則代表了露西內心的猶豫和隱忍,將英國上層社會大家閨秀封建的一面展示給觀眾,也讓故事情節的發展趨于緩慢。
四、結 語
詹姆斯·艾弗里在影視創作過程中,通過對文學原著作品個性化的改編,讓文學本身的藝術價值實現最大范圍和最直觀的傳播,同時也讓觀眾在光影的世界中獲得更多的審美愉悅感。從這點上來說,詹姆斯·艾弗里實現了對文學作品的二次創作,實現了文學與影視藝術完美的契合,而詹姆斯·艾弗里改編電影的成功也值得我國文學改編電影創作者認真研究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