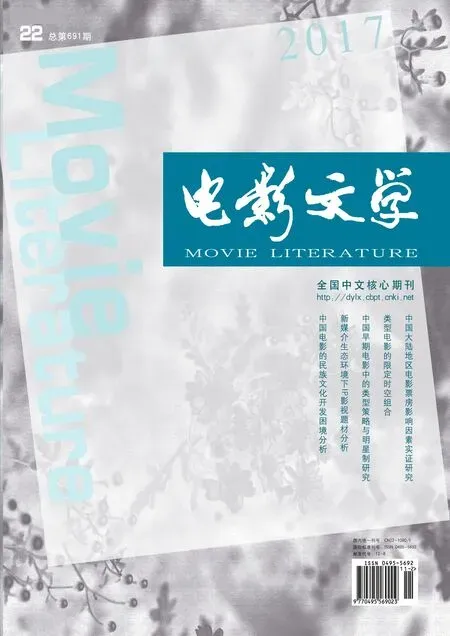由《喊·山》看中國鄉土電影審美旨趣
汪 霖
(江西財經大學藝術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楊子導演根據山西女作家葛水平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的《喊·山》(2015)可以視作是國產電影中近年來難得的、較為純粹、典型的,同時又表現出一定藝術水準的鄉土電影。它可以成為我們管窺中國鄉土電影審美的一個切入點。
一、鄉景民俗的展現
鄉景民俗是鄉土空間最直觀的物質和精神特征,是觀眾在視覺上進入這一銀幕空間的最重要標示。同時,鄉景民俗也是人物活動的環境,它們直接關系著人物的思維和行為,在鄉土電影中顯然是必不可少的。如張藝謀在《秋菊打官司》(1992)中設置的秋菊家紅艷艷的辣子,在《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中加入的原著沒有的“點燈”習俗,讓紅燈籠點亮這個沒有生機的府邸等,都屬于一種對鄉景民俗的展現。而就審美旨趣來說,關鍵就在于在對其進行展現時,電影主創會采取一種怎樣的藝術思維。在上述兩部電影中,紅辣椒和紅燈籠除了在視覺上給觀眾造成了一種激情、欲望的暗示外,也關系著女主人公的鄉土生存處境:秋菊家的經濟來源便是種辣椒,她的丈夫正是因為想蓋一座辣子樓而與村長發生了沖突,導致了秋菊走上打官司之路;而頌蓮則在嫁入陳府以后,期待著下人能送來意味被老爺“臨幸”的大紅燈籠,幾個姨太太和丫鬟之間的宿命便在紅燈籠之間糾纏著。以暗喻、對比等展現鄉景民俗,已經成為當下中國導演的一種審美共識。
在《喊·山》中,觀眾可以看到電影一開始以俯拍鏡頭展現的一片寂靜、祥和的山野風景。平心而論,這段風光是極為美好的。但這段景觀畫面傳遞出來的是雙重信息:第一,它表明故事發生在一個位于群峰競秀、五彩斑斕的太行山當中的偏遠的村落,重重疊疊的大山埋下了這里極為閉塞的伏筆。正是因為這里的閉塞,法制對村民來說是遙遠的。因此紅霞才會在被拐賣又被強制遷移到此處以后無法通過報警脫離困境。也正是因為這種封閉性,韓沖在埋設炸藥誤炸死臘宏之后,村民們所選擇的方案不是報警,而是讓韓沖賠付給紅霞兩萬塊錢,并照顧她們母女的生活。第二,這一段唯美的外景是和與其緊密相連的一段內景鏡頭互相對照的。在內景中,臘宏進門、關門(女兒和兒子在外面),帶著一臉猥瑣的表情強行將紅霞拉上炕,不能說話的紅霞用身體語言來盡力地表示自己的拒絕,然而她的力量太弱小了,完全不能阻止臘宏對她的施暴。外部風光越是光明、美好和祥和,越是襯托出不為人知的房間內發生的事情是何等黑暗和不堪,觀眾也完全可以想象得到,電影中的紅霞實際上是幸運的,依然有無數個紅霞歇斯底里的吶喊和掙扎被九曲山巒所掩蓋。
二、抒情性鏡頭的運用
所有的電影鏡頭實際上都是主觀性和客觀性相結合的產物。客觀性指的是攝影機天然有著記錄真實的人物、事物和景象的能力,而一些客觀事物也并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而主觀性在于,攝影機終究是由人操作的。電影主創選擇從怎樣的角度來觀察事物,讓鏡頭在某樣被拍攝物前保持多長的時間,以及拍攝時的燈光、道具等的加入,包括后期的剪輯和技術加工等,都是為電影畫面增加主觀性的方式。不同的主創在不同的政治傾向、文化素養等因素的影響之下,鏡頭所呈現出來的風格和電影的整體表現手法自然也是不同的。在鄉土電影中,這種主觀性和客觀性結合的范例也比比皆是。從客觀性來看,例如在陳凱歌的《黃土地》(1984)中,西北的風貌以及翠巧等人物的原型都是有跡可循的。而從主觀性來看,如霍建起的《那山 那人 那狗》(1999)中,觀眾跟隨著郵遞員的腳步看到的是青翠的群山、清澈的溪流和石板路等,農村景象是清新、潔凈而唯美的,這些實際上都是導演藝術選擇之后的結果。而主客觀皆有的則有如張藝謀在《紅高粱》(1987)中的“顛轎”一段,從陜北民歌中不難發現,這種習俗并不是張藝謀的杜撰,只是在電影中,張藝謀將它直接與男女主人公的野合聯系起來,因此將其表現得更富有亮麗的激情。絕大多數情況下,即使是張藝謀在《一個都不能少》(1999)、《我的父親母親》(1999)中采用的那種接近紀錄片式的拍攝手法,電影鏡頭依然是主客觀共同參與完成的,鏡頭語言的紀實和抒情之間并沒有涇渭分明的界限。
三、中性化的轉述視角
在討論中性化轉述視角之前,有必要對其他中國鄉土電影的敘述視角進行一下簡要的概括。一般來說,由于時代和個人藝術視野的限制,前代(包括當代)中國電影人在觀照鄉土時,往往不是“向上轉”便是“向下轉”。
在《喊·山》中,導演嚴格地遵守了原著的故事情節,既沒有考慮到商業利益而扭曲、夸大情節,以創造出某種戲劇效果,也沒有以一種高度理想化的濾鏡自動屏蔽鄉土中的陰暗面。在電影中村民們普遍是善良的,如韓沖的父親便是一個厚道的長者,他主動催促韓沖對紅霞做出賠償,在紅霞被警察戴上手銬帶走時,韓沖父對一直哭個不停的紅霞女兒小書說的是:“警察帶媽媽去治啞病,跟爺爺走吧。”但正如盛寧曾經指出的那樣,長久以來,沒有一種宗教能夠在中國成為主導性宗教,對中國社會造成全面的影響,這就使得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填補這一空間的是一種民間的、草根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塑造著中國人的文化身份。“但民間意識形態基本上是一種以生存為目的的意識形態,它的最突出的一個特征就是它的權宜性——為了達到生存的目的可以采取各種變通的手法,也正因為如此,它最缺乏的是一種長遠的、終極的關懷。”在電影中,村民們對紅霞表現出來的善意都是有限的,都是建立在不影響自己生存的基礎之上的,一旦他們認定紅霞是個禍害,就會千方百計地趕走她。
中國鄉土電影中的審美旨趣不是抽象的,它是由創作者根據自己對人與自然的觀察,然后以心靈“外化”而出的一種審美傾向。在新的時代,中國鄉土電影的審美得到了重新建構,而這些可以從楊子的電影《喊·山》中一窺端倪。《喊·山》在表層上,展現了農村的鄉景民俗,在手段上,運用了帶有抒情意義的鏡頭,而在思想內涵的表達上,則采取了一種既不理想化鄉土空間,又不對其進行全然貶低的中立態度,這種中性化的敘述并不影響觀眾在觀影之后獲得深刻的感受,并對電影中指出的鄉村的痼疾進行反思。由于農村社會在中國巨大的體量,它必然不會為國產電影所遺忘,那么如何在文化表述的自由化以及經濟商業化兩個潮流不斷深入的當代,拍攝出既屬于中國又屬于時代,同時還屬于導演本人的高質量鄉土電影,《喊·山》可以說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值得借鑒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