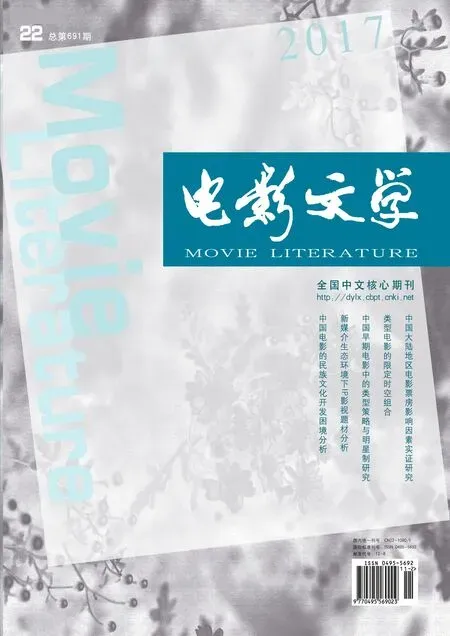從《驢得水》看民國時期女性意識的崛起
栗曉樞
(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15)
“講個笑話,你可別哭”:一個小山村,一群懷揣著教育夢想的人,一頭名為“呂得水老師”的牲口,幾個看似毫無關系的因素在這部講述民國故事的影片《驢得水》中相互穿插,相互利用,相互傷害著,雖然被冠以喜劇的稱號,卻讓人看到心痛,悲不自勝。
一、“烏托邦”的破滅
“山村支教”是一件非常偉大的事情,但最需要的是金錢的扶持。為了能拿到更多的經費維持學校的正常運轉,校長向教育廳謊報了教師的數量。在教育廳派特派員來進行考察時,為了應對突發情況,學校臨時找了一名銅匠來充當教師。銅匠從未經歷過這樣的大事,一直推托拒絕,最終,女教師張一曼用自己的魅力“睡服”了銅匠。講到這里,不難看出,大家閨秀、三從四德這些形容中國傳統女性的詞語都不適用于張一曼的身上。這名弱女子之所以來到山村,除為了教育事業奉獻以外更多的是逃離城市中戴著有色眼鏡之人的目光。同行的教師裴魁山向她告白的時候,她只是云淡風輕地說道:“你覺得我是那種可以跟你過一輩子的人嗎?”說著,將手中剝好的蒜皮輕輕揚手一撒,開心地說著“下雪啦”,將世俗眼中的廢棄之物當作浪漫的雪花,一曼內心的純凈絕非一般人能比。從影片的整體情節能夠看出,對于銅匠,一曼的情感也是真實的,“哪怕那不是愛,哪怕只是感動,甚至于只是一種觸動,于是,才有了我與你的一縷青絲,還你此生一段情誼,今生不能結發夫妻,算我欠你的,有來生再還”,但她有著自己的做人原則:不傷害別人,也不受人束縛。正是因為這個原則,當銅匠問她是否有一絲喜歡自己時,為了不破壞別人的家庭,她狠狠地說道:“在我眼里,你就是個牲口。”讓銅匠對自己徹底死心,看到銅匠傷心地將珍藏的自己的頭發扔到地上轉身離去時,她意識到對于銅匠的傷害太大了,但為了銅匠的家庭,她忍住了淚水,確定銅匠遠走后才將地上的頭發撿起,痛心地說道:“對不住啊,銅匠。”為了應付外國友人的檢查,校長再次邀請銅匠回到學校,此時的銅匠早已不是當初那般模樣,大奔頭、墨鏡、貂皮大衣,十足的大腕范兒,可是,他提出了一個無理的要求,只有小學里每個教師都對張一曼進行謾罵,他才會再次充當“呂得水”老師。首當其沖的便是裴魁山,在表白被拒發現張一曼與銅匠的奸情后,懷著“得不到就將其毀滅”的想法大罵張一曼。最終在銅匠的要求下,一曼的頭發被剪掉,所有人都對她惡語相向。
這不禁讓人想起法國作家莫泊桑的《羊脂球》。妓女羊脂球在前行的路上,雖然同行的伙伴總在明里暗里譏諷自己,但她仍舊在大家最需要食物的時候拿出自己的余糧與大伙分享。在遇到侵略者提出非分要求的時候,為了幫助大家,委曲求全,最終馬車上的同伴都得到了安全的保障,唯有羊脂球孤身一人挨凍受餓,在科爾尼代的《馬賽曲》中嗚咽。科爾尼代是一個失語的符號,沒有任何意義,在眾人諷刺羊脂球時,他沒有跟著一起謾罵,在大家為了自己的安危勸說羊脂球妥協時,雖然對這陰謀論看得一清二楚,但他依舊什么也不說,隨那些人聽之任之,他處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去看待整件事情。當看到受苦的“羊脂球”時,他本可以去安慰或者為其提供食物,但他并沒有,只是冷眼旁邊,輕聲淺唱《馬賽曲》。《馬賽曲》是法國國歌,他的創作背景是在法國路易十六時期,社會矛盾日益激化,新興的資產階級同情農民疾苦,受到巴黎雅各賓派的影響,阿爾諾帶領馬賽港的市民設計奪取了要塞,得到了武器,并驅逐了公爵他們舉行集會通過決議組織義勇軍進軍巴黎去搭救同情改革的議員,馬賽市民積極參軍,高唱著《馬賽曲》向前進發,以此揭開了法國大革命的序幕。這首歌曲同時也成為鼓舞斗志的贊歌。但這樣的歌曲在此時此景中響起,不禁讓人發出無奈的苦笑,諷刺的效果達到了極致。小說中,雪慢慢變小,侵略者紛紛逃跑,唯留羊脂球輕聲嗚咽,聲音不大,卻震撼人心!其實,這個世界上,真正的小人并不可怕,他在明處,最可怕的是那些披著人皮道貌岸然的偽君子,他們躲在暗處。“只要用意是好的,做任何事情都不會觸怒天主”,正是因為老修女的宗教學說,才使得羊脂球為了大家的利益犧牲了自己。然而,最令人想不到的是,被自己當初幫助過的那些人正是最后將其推向火坑的人!
影片《驢得水》中的張一曼又何嘗不是現代版的羊脂球?在銅匠拒絕幫助學校的時候,她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可是她并沒有這樣做,按照校長的話來說就是“做大事不拘小節”,將大家從困境中解救了出來可是當本性已變再次回歸的銅匠要求將一曼的頭發全部剪掉時,拿起剪刀的竟然是那個滿口道義的校長!如果說一曼是自作自受的,那么,是誰導致了她今天的窘況呢?是滿口仁義的校長還是虛偽自私的裴魁山,還是屈服現實的教師周鐵男,抑或是內心扭曲的銅匠?“唯有完人才有資格向罪人扔石頭。但是,完人是沒有的。”
二、“三民”的反叛
影片的故事發生在民國1942年,地點是“三民小學”,影片中升起的是“青天白日滿天紅”旗。非常自然地,學校的命名讓人馳思遐想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所指的是“民主、民權、民生”,強調的是人民擁有自己最基本的權利,諸如生命權、人身自由權等。張一曼就是一個徹底貫徹“民權”主義的女性,她主張自己的身體自己做主,不為迎合他人,只為自己開心,這樣的理念與前幾年風靡的“支配自己的身體是每個人的權利”理論不謀而合。封閉了幾千年的中國傳統社會,對于女子的要求一直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在100多年前的小山村,一個女教師具有如此超前的思想是不會被人所尊重,甚至被人不齒,正是這樣的原因,張一曼才遠離喧囂的城鎮,來到這個荒蕪的小山村教書育人,過著自己理想中的生活。然而,生活總是殘酷的,在水流湍急的波濤中,若你不隨波逐流,偏要一意孤行做個另類時,最后的結果就是被浪潮所打倒。“當你沒有辦法改變現實的時候,就要學著適應生活。”周鐵男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最開始最堅持原則、最堅持正義的就是他,當張一曼被銅匠百般侮辱時,唯有他沖出去將一曼拉在自己身后說:“你們誰敢動她一下!”但是,當特派員保鏢的槍聲一響,徹底把這唯一的英雄嚇壞了,變成了主動給特派員找驢肉、看到特派員侍衛欲強奸一曼而躲避一邊的沒有底線的“慫包”。張一曼并沒有周鐵男這樣的靈活變通,她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原則,認為對的就不會改變,最終之所以選擇一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是對人性的絕望,對現實的無奈,對那個曾經對自己滿口情話甚至聲稱要娶自己的人竟然能說自己是“公共廁所”人的決絕。
同樣生活在那個年代的,還有一位杰出的女性代表,她就是阮玲玉。為了愛情,她可以如同飛蛾撲火般奮不顧身,不管是和張達明還是唐季珊,抑或是蔡楚生,最終卻被她所深愛的這些人深深傷害,被外界的輿論描繪成“破壞家庭的狐貍精”。雖說是“人言可畏”,但比這更可怕的是人心!這世間有兩樣東西無法讓人直視,其一是太陽,其二就是人心!她與三個男人提到了結婚:最初是與張達明商議結婚,卻遭到了張家的反對;在狀告事件發生后,與唐季珊發生沖突中提到了結婚,卻換得了一記耳光;在人生絕望時,遇到了蔡楚生,希望可以遠走他鄉共度一生時,得到的卻是委婉的拒絕。在世人的眼中,所謂“完整女人”必須同時兼顧女兒、妻子和母親三者身份為一體,缺一不可;在沒有婚姻時,與任何男子的親密接觸都會被冠以“淫婦”的名號。雖然阮玲玉也有著獨立的女性意識,自己工作養活自己,不依靠男人,自主選擇,遵從自己的內心,但終究與當時的社會格格不入,不被接受,最后吞藥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三、嬉笑的諷刺
在男權思想統治的社會氛圍中,男性處于統治者的地位,女性處于被統治的地位,當有女性稍有進取的想法時,便會觸怒到長期處于統治階層的男性,認為權利被侵犯了,進而進行百般的打擊,使其打消進取的念頭。然而,如果從來沒有嘗試,又怎會知道不能成功呢?沒有張一曼、阮玲玉這些女性的犧牲,怎會有現如今的男女平等呢?
所謂女性意識,指的是女性對自身作為人,尤其是女人的價值的體驗和醒悟。影片中張一曼沒有錯,錯的是她生活的時代,她的思想太超前,她不愿意為了迎合大眾的眼光而改變自己,她清楚地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所以她堅強、獨立、有主見。試想,如果張一曼是男性,那么,還會因為在城市里和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而被別人指指點點嗎?
“過去的如果就這么過去了,以后只會越來越糟。”最終,真相在陽光下暴露,一場鬧劇得以結束,“三民小學”看似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校長、周鐵男、裴魁山就像以前一樣手搭著手“聚聚氣”,卻發現一曼不在。蹦的一聲槍響,大家都向一曼的房間尋去,看到的卻是一曼用新的布料為大家做的新衣服,雖然之前被大家無情地拋棄謾罵,卻仍舊一心牽掛著她所愛的這個大家庭。當認為一切都歸于原點的時候,卻發現,改變的人心已無法再回到從前。看夠了這個世界的丑陋,既然這個世界容不下自己,那就去另一個地方,一個自由的地方。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為我梳妝。這夜的風兒吹,吹得心癢癢,我的情郎。我在他鄉,望著月亮。都怪這夜色,撩人的瘋狂。都怪這吉他,彈得太凄涼。哦,我要唱著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這夜色,撩人的風光。都怪這吉他,彈得太凄涼。哦,我要唱著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麗的衣裳。為你,對鏡貼花黃。這夜色太緊張,時間太漫長,我的情郎,我在他鄉,望著月亮。”一首《我要》將一曼渴望浪漫愛情的情懷表露無遺,也許,在愛情的處理上,她是輕浮的;但是對于愛情的渴望她與他人無差,她的內心更是純潔的。而她更是整部電影中唯一一個真實的存在,也是唯一一個悖離道統,游離于所謂道德的存在,她的犧牲是為了讓更多追愛的女性可以愛之所愛,放下盔甲,丟掉棱角,從容安詳。
四、結 語
婦女的解放問題一直都是民主革命的重要組成內容,孫中山先生一直認為女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要且非常必要的,這可以促進社會文明的進步,促進男女的平等,使女性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權利。但是,在強權的制度下,女性的反抗是無力的,卻不是無用的,一曼用死帶給了影片深刻的反思,女性意識在百年前的山村已經開始萌芽發展,雖然最后以自殺落幕,卻留給了觀者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