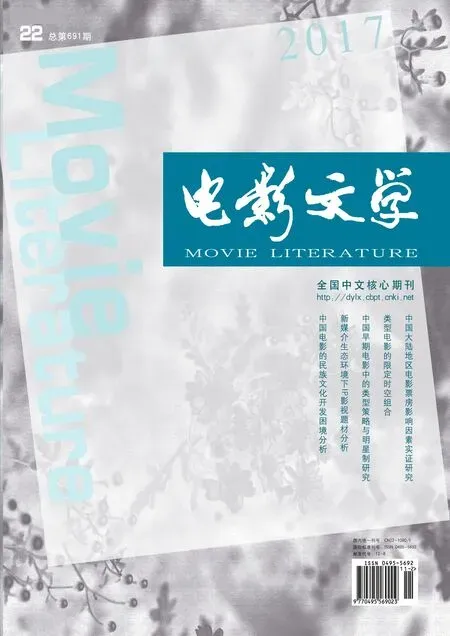《請叫我英雄》對日本社會現實的觀照
周 毅
(包頭醫學院,內蒙古 包頭 014040)
在諸如外星人攻擊地球,特大自然災害乃至鬼片等能夠將觀眾置于世界末日的感官刺激之中,讓觀眾感到或神秘、或恐怖的題材幾乎為電影人開掘殆盡后,隨著游戲、漫畫影視化進程的加快,喪尸電影近年來逐漸成為驚悚電影中的新寵。《生化危機》(Resident
Evil
,2002)、《釜山行》(Train
to
Busan
,2016)等都是喪尸電影中的佳作。而日本也不甘人后。佐藤信介執導的《請叫我英雄》(I
Am
a
Hero
,2016)改編自花澤健吾的同名漫畫。《請叫我英雄》在恐怖特效上亦是可圈可點的,但其審美價值遠遠不止在于視覺特效制作和漫畫影像化之上,與《生化危機》中濃郁的過關游戲感,和《釜山行》的重點是對人性的揭示不同,《請叫我英雄》的特色在于其中對日本社會的觀察和調侃上。一、“逆社會化”生活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社會中的“基本人際狀態”出現了“逆社會化”的特征。所謂“逆社會化”,即人自覺地將自己從社會規范和社會生活中脫離而出。社會化是促使人融入社會的趨向,個體會與周圍的人群形成固定的社會關系。而逆社會化則是反其道而行之,人有著擺脫這種社會關系的傾向,逃避原來社會對自己的定位。“逆社會化”的影響是廣泛的,中青年及少年都有為數不少的“逆社會化”人群。最為極端的表現便是日本陡然上升的自殺率、離婚率以及大量抑郁癥患者的出現。逆社會化“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如人際關系淡薄,人變得更為無助;社會競爭加劇,失敗者增多;個人選擇的增多也增加了對選擇失敗的擔心,加大了不安全感;許多人無所事事,精神迷茫……這些問題許多與西方發達社會一樣,屬于‘現代社會病’”。
在《請叫我英雄》中,男主人公鈴木英雄原本便是一個有逆社會化傾向的青年。“英雄”的名字對他來說更像是一種諷刺。他是一個過氣的漫畫家,目前的工作是給別的漫畫家做漫畫助理,只能做些毫無創造力的畫陰影線等工作,并且這一項工作已經持續了十幾年之久。而在15年前,英雄曾經拿過新人大獎,和他同時出道的人已經成為風生水起的漫畫家,并在編輯那里當面羞辱英雄,對方掀起衣袖露出的勞力士深深地刺激到了英雄。一方面是現實生活的窘迫,而另一方面是漫畫職業帶來的浪漫主義思維,英雄常常幻想出另一個自己,如幻想同事們一起以一種熱血沸騰的姿態高喊“漫畫至高無上”,而實際上卻被同事教訓“工作時不要自言自語”;又如,在喪尸橫行時,他幻想自己開槍瞄準喪尸,而其實他的手上空空如也,只好用假裝打出租車來掩飾自己的尷尬。在整個漫畫工作室中,英雄也是最沉默,與其他人來往最少的一個,當其他人討論新聞時,英雄永遠只是旁邊沉默的那一個。
在將自己與同事隔離起來的同時,他還有意無意地減少了自己與女友黑川徹子的交流。如當徹子在床上看電視,看到一個節目在說男人應該腳踏實地,不要給女朋友添麻煩時,徹子故意調大了音量,希望能對英雄有所觸動,讓他放棄不切實際的夢想。而英雄只是埋頭吃泡面,露出尷尬的表情。到了深夜,英雄還在努力地畫漫畫,這個時候徹子已經睡著了。兩個人之間幾乎沒有正面交流,因為英雄知道自己的現狀是徹子不滿意的,既然他無法改變現狀,他就只能選擇逃避。
這種逃避的結果就是他的幻想癥越來越嚴重,因為相比起這個殘酷的世界,英雄更愿意生活在一個自己想象出來的理想社會中。在面臨和喪尸們的最終對決之前,已經躲進鐵柜子的英雄聽到外面同伴被撕咬的聲音,考慮要不要出去的時候,他幾乎已經陷入精神分裂的狀態中,而當他結束幻想鼓起勇氣沖出鐵柜時,喪尸早已不見蹤影。
而電影還提供了一個作為襯托英雄成長的角色,那便是女主人公藪。藪的本名小田貢到了電影的最后才透露。她原本是一名護士,因為自己丟下無法醫治的喪尸而獨自逃亡,陷入了深深的自責當中。于是她給自己取名藪,藪在日本俗語里指庸醫,用以自嘲。與英雄的“名不副實”不一樣,她的名字是另一種名不副實。可以看到,藪是一個勇于面對挑戰,在災變之下的臨時社會中積極掌握人生的人,也正是她幫英雄成為真正的英雄。
二、生存壓力與社會癥結
長期以來,日本社會具有階級壁壘鮮明、分工明確的特征。社會成員生活于其中就必須擁有高度的紀律性和下級對上級的絕對服從性。無論從事何等行業,人們都被各種規范、條款約束,動作必須整齊劃一,最終使得社會這臺大機器運轉得有條不紊。當日本人在自豪于日本社會整體運行的井然有序,日本人工作的各司其職和嚴謹刻板時,他們又深知自己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承受著巨大的生存壓力。人原本的自我意識是被高度壓制的,人不得不對他人彬彬有禮,對主流觀念循規蹈矩。在這種壓抑下,一旦出現了發泄的出口,日本人就很容易走向野蠻兇殘、絲毫不加克制的另一個極端。喪尸電影便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背景,人們在這一環境中失去理智,暴露出本心,而他們所承受的各種生存壓力與這背后的社會癥結也被展露無疑。
首先是人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異化。在《請叫我英雄》中,關于喪尸的設定有一點與《釜山行》等電影不一樣,那就是喪尸還保留了一部分生前的記憶,他們會不停地重復自己被咬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或是自己抱有最深執念的事。如跳高運動員就不停地跳高,每次都落在水泥地板上而絲毫不覺劇痛;上班族就一直保持著提著公文包,拉著地鐵吊環的姿勢;而用購物來麻痹自己的家庭主婦就一次又一次地向商店的門撞去。英雄近距離接觸的人里,一個是出租車司機,在發病時不停地重復說自己30年零事故、零超速,一邊將油門踩到底。另一個則是平時忍受夠了漫畫家潛規則另一個女同事小美的同事大叔狠狠地用棒球棒砸爛了漫畫家的頭,斥責他是一個臭蟲。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或是被機械化,或是積攢了太多的怨氣。
其次是整個社會經濟階層的嚴重分化。在電影中有兩個人表現出了極端的仇富和仇貧情結。一個便是同事大叔,他曾憤怒地抱怨已經結婚生子但還潛規則小美的漫畫家:“他還有錢,還有事業,為什么我什么都沒有,這不公平。”當喪尸事件爆發后,同事大叔竟然幸災樂禍,因為他認為受害的將是那些有錢人,而他們這些窮人將因為不出門而逃過一劫,以后就是窮人的時代了;反過來,與英雄和比呂美共乘一部出租車的西裝男子(從電話內容推斷他很有可能是市政府官員)則極度鄙視窮人,在即將變異時,西裝大叔還不忘咒罵窮人,埋怨政府還不允許開槍,因為在他看來,不交稅的窮人都是可以殺掉的。
這種經濟上的分化也導致了在社會陷入混亂之后人們對于財富的重新分配并不像日本人平時標榜的那樣理智和克己。當英雄進入到臨時住宅區后,大叔阿部來給他分發生活用品,英雄發現阿部手上有勞力士時,阿部便拿出來一筐子的勞力士手表讓英雄隨便拿。顯然這些都是從死人胳膊上拿下來的。想起自己曾經受過屈辱的英雄索性掛了整整一條手臂的勞力士。勞力士手表成為一個伏筆,它原本是英雄“非英雄”的一面,手表折射了英雄作為普通人的貪婪,但在后來的戰斗中,舍己救人的英雄手臂被咬,恰恰就是這一排手表救了他,后來為了開槍方便,英雄索性將這些沉重的手表全部取下,鎮定而沉著地向潮水般涌來的喪尸開槍。手表陰差陽錯地拯救了英雄,以及英雄最后對它們的舍棄,正是英雄一步步從“非英雄”蛻變為“英雄”的寫照。
三、集體主義下的個人主義
就傳統而言,日本民族是有著強烈甚至極端群體意識的。在這種群體意識中,集體的利益被置于高于個人利益的位置,個人的意愿必須服從于群體的意志,絕大部分日本人堅信,個體在必要的時候為集體而犧牲是值得肯定的,是光榮的。這種思想是與日本“神儒一體”的文化背景有關的。神道教中的神秘學說作用于日本大家族的維系,而中國儒家學說中的克己奉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觀念也為日本人所選擇性吸收。而在明治維新以后,這種群體意識開始受到由西方傳來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沖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美國的全方位干預,日本人更是感受到了凝重的集體主義傳統給人們帶來了痛苦和壓抑,于是開始有意識地追求對個人價值的實現,最為明顯的表現就是明治時代和1947年兩次新民法和家族法的修訂。
這種社會思潮的轉變也體現在了電影藝術中。隨著電影產業的全球化,日本電影也向西方電影審美看齊,好萊塢電影中層出不窮的個人英雄主義在商業電影中的意義也為日本電影人所認識。在《請叫我英雄》中,英雄的形象就有著個人英雄主義的意味。只是相對于“美式英雄”而言,英雄是一個較為典型的、缺乏魅力的日式小人物式英雄,如果沒有這一次喪尸爆發,他的機智和勇敢很可能一輩子都無法顯現。與美國西部電影、黑幫電影、戰爭電影中主人公不斷使用暴力不同,英雄不到最后一刻都沒有選擇暴力,包括之前無數次命懸一線,他都不敢向人類同胞開槍;他也無法從容地面對所有危機和困難,甚至屢次需要靠女子如比呂美和藪來救他性命,而英雄除自保以外,他最終斗志被激發,所維護的也只是這兩名女性,而不像美式個人英雄主義中,主人公的壯舉往往與維護正義、保衛人民和國家等有關。
在電影中,英雄本身是一個較為傳統的日本青年,他本身并沒有脫離家庭和集體的意愿。即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漫畫事業中,他也沒有忘記自己努力的一部分原因是和徹子順利建立一個家庭。只是變故橫生,徹子和同事們都先后死去,英雄不得不和少女比呂美相依為命,而比呂美又受到了輕度感染。在這樣的情況下,英雄被情勢逼成了一個孤膽英雄,他一個人帶著已經“貓化”了的比呂美逃命,掩飾比呂美的感染。而當伊浦要建立一個集團化的生存方式,要將自己的地位導向權威化時,一向軟弱的英雄選擇了反抗,他拒絕交出自己的槍。這是符合觀眾的心理預期,能夠引起觀眾的共鳴的。
而有必要指出的是,盡管都是著眼于對個人身份的回歸,但是英雄在電影中表現出來的個人主義與逆社會化是有著區別的。在逆社會化中,正如安東尼·吉登斯所指出的,人因遭遇了“現代性”而對自我認同出現了困惑,甚至失去了一種本體安全,因此會在任何一方感到有一點不適的時候就主動斷絕社會關系,而不顧外在的、傳統的道德標準框架。而與集體主義相對立的個人主義卻是人獲得自我認同的過程,英雄在張揚自我能力的時候確定了自己也可以獲得“英雄”身份,他主動地去營救藪和比呂美,而不將和兩位女性的關系視作自己焦慮和磨難的來源,這時候自我和他人之間是有穩定的、強有力的關系紐帶相連接的。
《請叫我英雄》不僅以頗為幽默風趣的方式給觀眾奉獻了一次喪尸圍城的視覺盛宴,還以主人公英雄為中心展現了當代日本社會文化,包括日本人的民族性格與他們在當下的心理素質、價值取向等。在并不了解日本的觀眾的審美習慣得到充分照顧的敘事套路之下,熟諳日本社會現實的觀眾的觀影心理與情感訴求也得到了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