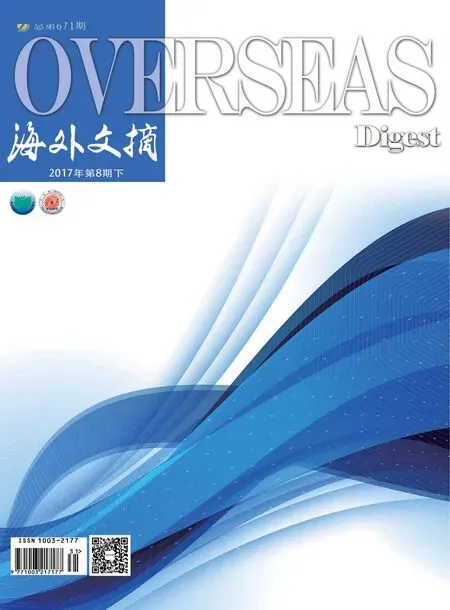戴上眼鏡后,他們失明了
——品讀迪倫馬特作品《拋錨》
劉帥
(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北京 100081)
當特拉普斯與斯托特貝克拋錨在了一個世外之境,他的平庸人生里突然出現了一個更加聰明狡猾、更加具有強人能力的自己,他開始被這個殺人的“童話”所迷住,然而卻永遠地“拋錨”在那個荒誕的鄉村夜晚。在幾個垂死的老年人眼中,這個被工業文明沖擊的世界,這個被鋼筋水泥攪拌的世界,發生了扭曲和變形。戴著老花鏡的老法官、金絲邊夾鼻眼鏡的老律師、還有扭曲著五官舉著單片眼鏡審視世界的老檢察官,以及劊子手彼雷特,四個在工業文明時代生活過、流浪過的人,仿佛是一本厚厚的日歷冊,記錄了這個背棄了宗教、道德、信仰的時代,默認了關于它一切荒誕怪異的“現代規則”。鏡片外的世界和視網膜上的成像,發生了扭曲和變形,就像“拋錨”的特拉普斯一樣,人們開始懷疑所見所聞的真實性,懷疑平日里篤信的教條是否正確,懷疑人生和上帝的意義。“偶然地,我們還可以從一個酩酊醉漢的單片眼睛的反光中捕捉到這個現象。”這個現象便是,人類不再相信上帝,不再震動于交響樂里反復強調的命運,人性被螺絲釘固定在了鋼鐵架構里,愛與純真被當成謊言,而殺戮和欺騙卻是人間俯拾皆是的小把戲,一場“審判游戲”殺死了一個平庸的小商人特拉普斯,同時也向那些麻痹于錢權地位而忘記愛與陣痛的靈魂刺上了深深的一刀。
1 “鏡片里的扭曲世界”
當帶著老花眼鏡的老法官,翻著眼球從鏡框上端觀察特拉普斯的那一刻,一個小心翼翼還有些詭異狡詐的形象便出現在了這個“倒霉的”特拉普斯面前。隨著時間的推移,晚宴的時間越來越近,戴著金絲邊夾鼻眼鏡的庫特和夾著單片眼鏡的措恩也開始出現在了這間別墅之中,此時此刻窗外的風景還是一片的田園牧歌,特拉普斯眼中的世界還是一如既往的和諧而庸俗,無聊而冗長。然而,當這場“審判”游戲,在他毫無防備中開始的那一瞬間,塔普拉斯已經被這群奇怪的老人,帶進了他們“鏡片里扭曲的世界。”
游戲里,特拉普斯的辯護人庫特,是一位退休的老律師。晚宴里,他的黑色禮服里套著的是臃腫油膩的睡衣,金絲邊夾鼻眼鏡里是一雙和諧的爆眼睛,他不時地提醒著特拉普斯要謹慎要慎言,不要被狡猾的檢察官抓住了把柄,其實只是他律師生涯里為錢權高位者出賣法律正義的習慣用語,對他而言邪就是正,有罪也是無罪,世界上不存在所謂的正義和無辜,有的只是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帶給人的高壓和踩在頭頂上的那些人發出的指令,對于一個律師而言,法律都可以篡改,那世間還有什么不可以顛倒黑白?“審判”過程中,他不停地擦拭著自己的夾鼻眼鏡,一次又一次地取下再戴上,似乎他也不敢確定自己眼前的世界是否是真實的,特拉普斯的所言是否可信?他是否真的無罪?辯護人無法相信自己的當事人,當事人視辯護人的忠告為兒戲,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與懷疑,也是導致特拉普斯最終被游戲所殺的原因之一。
檢察官措恩,是這三位老人中年齡最大的一位,他為了夾住單片眼睛而不停地扭曲著五官,臉上的傷疤是風雨蹉跎的標志,鷹鉤鼻則象征著犀利而深邃的人格,這個老檢察官是一個犀利而又狡詐的人物,然而令人滑稽的是一個應當行事謹慎而又心細如絲的人,卻穿著全盤扣錯紐扣的背心,穿著兩只不同顏色的襪子,邋遢混亂的生活痕跡不得不令人懷疑他是否真的是一個稱職的檢察官。如同辯護人庫特,審判中他也時常將單片眼鏡戴上取下,但不同的是他總是緊湊在當事人的面前,詭異而又可怖地扭曲著五官,來觀察別人的細枝末節,他篤信特拉普斯是有罪的,并且在審判中一以貫之。不容忽略的是,檢察官的職責是找到罪犯,然而當他瞪圓了眼睛,用單片眼睛觀察嫌疑人的時候,他卻勢必會瞇上另一只眼睛,一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檢察官,一個應當依據事實說話的人物,卻成為了一個社會黑暗數據的“考據者”,于是根據他的經驗,凡言自己無罪的人一定有罪,特拉普斯死罪無疑。
別墅的主人老法官的出場便是戴著老花鏡,法官依據法律進行最終審判,審判過程保持中立,這位老法官在這場審判游戲中,的確并沒有發出尖銳的聲音,然而卻是這場審判游戲的啟動者和終結者,他肆無忌憚的笑聲,隨心所欲的態度,令人可怖的是從他身上,我們看到那社會的天平似乎永遠無法停止擺動,永遠無法平衡。威壓全庭的法官是一個小矮子,他在這場審判里已經失去了理智和冷靜,全然沉浸在這場激烈的游戲當中,法官成了辯護人和檢察官辯論大賽的旁觀者,將這場荒誕的游戲和最后出乎意料的悲慘結局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正是在說:
“在這個障礙密布的世界里,在我們行進的道路上,在塵土飛揚的道路邊緣,和皮鞋廣告、汽車廣告、冰淇淋廣告緊緊挨在一起的還有許多不幸事故死亡者的墓碑,啟示我們想起一些可能發生的意外狀況,讓我們從若干人的面容上看見一些人類本性,一場微不足道的災難,會觸及人類的普遍真理:公道、正義,甚至是人的品德。”
眼鏡是知識、文化、科技的標志,是有地位道德的人的象征,然而我們卻從三位老人的視野里看到了一個異化的世界:信仰的喪失、人性的扭曲、生命的荒蕪、道德的遺忘……工業社會已將人關于上帝、關于善和愛的愿景,攪碎在了金錢的攪拌機里,成為了被遺忘的碎渣。
2 “含蓄的反諷”
審判里的第四位老人彼雷特,在整個過程中,盡情地吃喝,發言甚少,看上去是四位奇怪的老人里,最沒有棱角鋒芒的一位,連在他的胸上的西服口袋里,插上的那株白色的石竹花,也是仁慈的母性的象征。令特普拉色瞠目結舌的是,這位形象圓潤和善的老人,卻是一位“技藝高超”的劊子手,甚至因為技術精湛而遠近聞名,一位將匕首扎進人心臟、子彈射進頭顱,如同做外科手術一般冷靜而又精準的劊子手,無論他再怎么用訥言的表象和純潔的山竹來粉飾自己,都無法遮住他內心冷酷無情的黑洞。
別墅外的世界仿佛是一片田園牧歌般的世外桃源,勤勞的農民、過往的車輛,鳥語花香的自然美景勾勒出了一副和諧安然的景態,然而隨著夜幕的降臨,別墅的窗戶玻璃上開始扭曲地呈現著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婆娑的樹姿、搖晃的燈光、變形的人像……人性背后的丑陋終于在和美的湖水表面浮現出來,并且這一水紋愈發地激蕩,這場“審判”的游戲也愈發地令人感到可怖。
審判中,醞釀著戰爭殘酷的1914年的美酒,麻醉著心存不善者的神經,宴會的喧囂與詼諧,暗藏著殺人的利器。“戰爭起源于人心”,曾經的一戰為了土地人口而爭奪,當下的工業社會,金錢權利、非分的幻想,依舊挑逗著心里住著“侵略者”的人的味蕾,勾引著他們張開血盆大口互相吞噬咀嚼。
當特拉普斯相信自己是古加克斯的真正的施害人,相信自己擁有將死敵置于絕地的“非凡”能力時,他開始感到心慌和一絲變態的驕傲,他喜氣洋洋地說:“說的完全正確,庫特。完全正確。”卻沒有發現自己已經跌入一場圍獵,“我感覺自己開始有了理解力,并開始對自己有所理解,好似我自己新認識了一個人,這個人恰巧就是我自己。”特拉普斯看到的這個人,是他渴望自己能夠成為的強人,能夠踢開一切絆腳石的大力士,同時也是四位老人異象世界里認可的人物。《陽光普照著我們》的歌聲飄在彌漫著黑色陰云的土地上,“走正道者得好報”、“一顆善良的心是最好的安慰”的普世真理卻出現在潛意識里并不相信法律正義審判的法官家中,“富于童話色彩”的街道,卻永遠沒有第二個清晨來迎接特拉普斯幸福美滿的童話結局,他已然死在懷疑和否定之中。
然而這部作品最大的反諷,便是一個無中生有的案件,用一場游戲卻判死了一個庸庸碌碌的紡織商,一個從不相信自己經營能力、生活能力的人,卻最終相信了自己擁有殺人的絕頂智慧,并深陷其中無法自拔,其實就算特拉普斯能夠將人性本惡的一面展現出來,也需要希特勒般的勇氣去直面現實。
3 結語
迪倫馬特的《拋錨》,將人從現實生活中了抽離出來,如同緣溪而行的武陵人誤入桃花源,特拉普斯也從現代工業社會中抽離,成為這一鄉村別墅永久的不速之客。他的斯托特貝克、他的人生就從這樣一個怪誕的夜晚從此“拋錨”,成為工業齒輪上的一滴潤滑油。這場“審判”游戲,看似荒謬,卻從鏡片反射出的光澤里,看到了關于信仰、命運、正義的反思,感慨于善與愛的淪落,也看到了人性的丑惡也具有致人于死地的強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