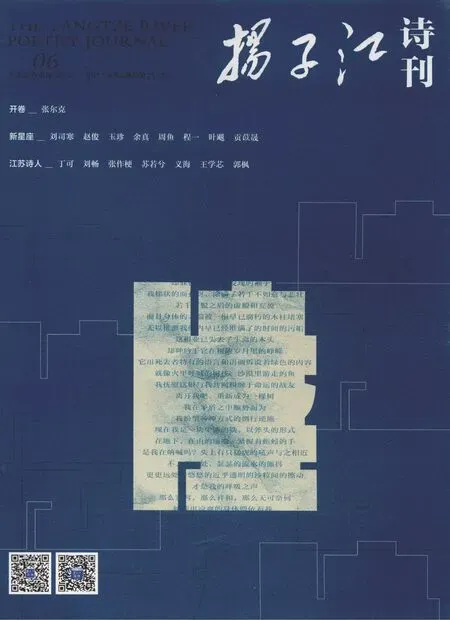與家人和土地說話(組詩)
羅振亞
與家人和土地說話(組詩)
羅振亞
朋友遠行
不用再緊張地排隊驗票
也不用再費力攀爬候機大廳
這次你將乘一縷青煙
做一場一去不返的旅行
早說好的眼淚免了
有瓶常喝的老窖足以盡興
可你還沒親近爐火
窗外就傳來一片燙傷的蟬鳴
聽說天國里沒有冬天
看不見擁堵、霧霾和戰爭
蘭花開遍湖邊路旁
你鼻炎和關節的疼痛會越來越輕
唯有像植物離開土地
此后故鄉只是夢中的一道樹影
如果你實在想兄弟們了
就在雷雨天盡情地吆喝幾聲
和老爸聊天
爸起來吃點飯吧
話音未落發現
他遺像里的嘴角向上翹了翹
冬天我在耐心學習孤獨
被流放他鄉的這幾年
您就是它和疾病輪班陪著
誰說陰陽分屬兩界
您走之后的夢里
咱倆常有一搭沒一搭地閑聊
那年夏天日頭真毒
東北土路也開滿刺眼的白花
您遞給我半個消暑的西瓜
至今我口里還有香甜的味道
有一回我在村邊摔得天旋地轉
您愣是鐵著心不肯攙扶
還說是爺們永遠不該跪著
我站起后至今再沒有彎過腰
爸明代的解學士不想說話
如今的書和遍地莊稼一樣泛黃
放心吧咱家門前那幾株嫩竹
父親臨終前說出三個字
沖著六月和煦的風
父親吃力地說出三個字
——李向陽
我知道那不是呼喚英雄
英雄一生無緣和他照面
也不像在叨念朋友
進城后他僅與孤獨對弈
李向陽是生我養我的村莊
十幾年父親躲閃著
這夢魂牽繞過的三個字
生怕兒孫染上土氣與寒酸的不祥
和母親小聲嘀咕時
才放它們露出頭來吸吸氧
只要一說出村莊的名字
村邊的林子就開始泛綠
玉米穗在院子里自覺站成行
盡情撒歡兒的雞鴨鵝三軍
讀不懂菜園花兒前的蝶舞蜂忙
我和孩子若要探問
“演員”們在父母的微笑中
馬上識趣地退場
也許這三個字沉埋得太久
幾千個日子的施肥澆水
已在心里長起三株穿天楊
枝干轉向哪里
哪里就是思念的方向
父親您過慮了
其實我也想乘這三個字回家鄉
不論外面下雨還是飄雪
柳絮紛飛抑或秋露為霜
向陽總似空中那只美麗的雁
每一次翅膀的翻動
都牽引著無數縷注視的目光
您說過鄉愁的種子也會遺傳
種不種在腳下的土里
都將隨自己的足跡生長
三九天乘著高鐵回家看望母親
窗外鵝毛大雪
一萬個美女的舞姿
仍無法讓急馳的高鐵分神
回家的方向是最快的方向
三九天我乘著高鐵回家看望母親
前方亮起那盞不滅的風燈
也照不清天邊慚愧的云
直到父親臥床
從沒想過母親也需要照顧
父親能讓幾十畝莊稼在手上生長
男人病了也是男人
當有一天父親瘦成墻上那幀照片
母親突然又矮了幾分
燒菜洗衣購物日子紛亂
夜晚忍受著一百多米的孤獨
漫長的黑里不時傳來鬼魅的呻吟
兒女從遠方聚到身邊陪伴
她恨不得把天下美味都擺在桌上
夢中也疏淡了額頭越來越深的皺紋
可沒兩天她便把他們勸回家
說媳婦不敢單住孩子需要看護
自己這把老骨頭還硬朗得很
于是每晚端坐電視機前看天氣預報
成了我堅持最久的一個習慣
地圖上一些密密麻麻的小點兒
開始有了呼吸的表情和體溫
看完后再打個電話提醒她加減衣服
才能靜心在燈下讀書著文
五年她以瘦弱的肩膀
扛起了一千八百多個多變的夜
按時電告兒女身體平安
一個人支撐著全“家”的溫馨
兒女流浪的足有休憩的碼頭
走在冰雪路上
也像懷抱一樣安穩
一個人對一個人牽掛
一個地方對一個地方禱告
思念原本是奔跑在天地間
眼睛酸澀永不老去的靈魂
快到站了母親那雙滯重的小腳
是否已和花白的頭發一起站在路口
焦急地等待把風雪中的我辨認
妻子的頭發
自從認識妻子的頭發
愈覺在云端舞蹈的詩人浮華
明明是帶著體香的一縷青絲
卻被隱喻為黑色的瀑布
甚至比附成茂密的草原
殊不知瀑布會斷流
草原只有一季能舉起溫暖與花
以發傳情不過是唬人的神話
青澀的心事無需養護
風雨中燕子的翅膀更瀟灑
當行囊把雙腿壓得骨質疏松
我肩不起兒子對遠方的眺望
妻子悄然將齊腰的驕傲剪了
說太長易臟不好打理
雖然見識沒和齊耳短發逆向生長
戰斗的早晨緊張的中午疲憊的黃昏
三部曲中她工作像工作家像家
兒子該寫字寫字
我該喝茶喝茶
如今我們住在陽光100
她的手機見山拍山見水拍水
日出的特產常在微信曝光
走在冰雪路上心里也藏著盛夏
不想從不咳嗽的她見肺部陰影
秋天的一次X光誤讀
引發了一場生死“對話”
漫長的黑里她夜夜不眠
白天頭發總是一絲不茍
外出旅游混進秧歌隊伍
粉色的扇子襯著腮邊的紅霞
心里卻惦記我和兒子媳婦相處
誰適合照顧我的傷痛和嘴巴
看了一場撼人的《又見平遙》
只記住一句臺詞
“生都生了,死就死吧”
可我只能告訴她千萬別怕
咱半輩子從來沒想過害人
“彩票不會隨便落到咱頭上噠”
只是怕見“病”“死”“癌”等字眼
它們是一顆顆炸彈
隨時都可能發生爆炸
終于CT打敗X光
陰影原來是散點鈣化
看著她頭上飛雪的瞬間
我說“理個短發,去去晦氣吧”
之后我猛轉身
把背影留給道路
我要看黃河如何決口
山洪怎樣暴發
孩子 我們已沒有資格談論故鄉
月亮是供游子圓缺的
天空由南歸的雁陣丈量
檔案館前的幾只流浪貓
叫出故鄉遙不可及的內傷
日子像瘋狗在身后狂追
不知啥時太陽患了紅斑狼瘡
姑娘穿得少得讓人不敢睜眼
性病廣告貼到幼兒園的門上
小魚兒不斷浮上水面喘氣
岸上人的表情陰晴無常
孩子在都市的車海里學游泳
我們已沒有資格談論故鄉
都說家就是足下的泥土
鄉音將一直朝著家的方向生長
可為什么腳印留在臥室
靈魂卻總迷蹤在路上
抵達一次次成為奢望
遠方越是誰也到不了
越是誘惑得無數人醉臥沙場
從你太爺你爺爺到我和你
蓬萊閣旁的滿院桃花
訥莫爾河畔的兩坰高粱
被置換成哈爾濱天津衛間的高鐵
鋼筋水泥中的一團霧霾
和十七樓一百多米變質的陽光
自從跪別你爺爺碑前的大片青草
和地圖上從未標記的生我的村莊
那條河流的來路就再也看不清了
混亂中的記憶已經改變方向
孩子在之乎者也的平仄里練平衡
我們已沒有資格談論故鄉
高樓旁 一棵蒲公英的靈魂在倔強地飛翔
不知道經歷過幾世的輪回
根才扎入水泥森林中柔軟的縫隙
常借割裂的綠地上開出的天窗
吸幾口鄉野般脆嫩的鮮氣
渴了只能飲自己的淚珠
瘦弱得甚至舉不動怒放的花期
但只要一聽童稚的歡呼叩門
便會剎那間把頭高高揚起
至于目光的無視與踐踏早已習慣
沒有高貴點贊的生命
照樣吐綠開花結子
當然也怕哪一天像稗草一樣
被人連根拔掉在陽光暴曬下
慢慢地枯萎死去
生命剛剛開始就成為結局
或者被稔熟的游子帶回家
就著小蔥一起下肚
喚醒沉睡的記憶
如果成熟穿越了春天
種子們化作舞蹈的白色茸毛
乘著風的“高鐵”飄向未知之域
那絕對不能叫流浪
說不準還會奏出一闋還鄉曲
只要靈魂能夠飛翔
安定與漂泊生和死
在辭海里原本是一個意思
在海景房的窗邊想起村前那條黃土路
炎熱被嚴實地擋在窗外
空調體貼得像失散多年的姐姐再現
陽光本來是垂直說話的
碰到情侶們的花傘卻拐了各種彎
門口剛剛生崽的阿花不吃貓食
沒見鮮肉和小魚兒叫得很凄慘
站在美麗的海景房窗邊
老家村前那條黃土路又在眼前一閃
馱著《論語》和爺爺的黑驢還沒走遠
坐在爸爸馬車上的秋天就跑起一溜煙
每天自行車陪我去鄉中學讀書
兒子慢行的沃爾沃在看彩蝶蹁躚
走過百家姓和“萬年歷”的黃土路
就是老掉牙也還坑是坑來坎是坎
被改寫的海浪在遠方咆哮
相思鳥不知棲在了哪一片柳林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