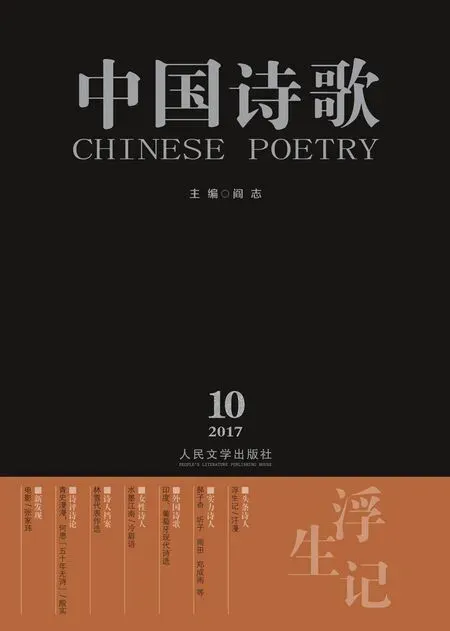羞恥與失敗
□汗 漫
羞恥與失敗
□汗 漫
“一個(gè)作家的源頭,正是他的羞恥。”“生活失敗了,就這樣進(jìn)入詩(shī)歌——無(wú)需天賦的支持。”羅馬尼亞作家齊奧朗的觀點(diǎn),驚心動(dòng)魄。
自少年時(shí)代開(kāi)始,詩(shī)就同行同在,賜予我友情、愛(ài)、思辨力、人格、視野……而我對(duì)詩(shī)、對(duì)漢語(yǔ)的貢獻(xiàn)微乎其微,因?yàn)槲业摹靶邜u與失敗”還不夠卓越?中年以后,羞恥感和失敗感漸漸強(qiáng)烈,或許有助于一個(gè)詩(shī)人形象的完成?
組詩(shī)《浮生記》是我近兩年來(lái)的作品,記出游、訪友、還鄉(xiāng)、獨(dú)步……是中年況味,是下午的自畫(huà)像、黃昏的練習(xí)曲——浮萍流水般的人生,短暫、微弱、不安,需要以寫作加固存在、抵抗流逝。
這些年,我在詩(shī)與散文之間跨界,試圖使散文與詩(shī)歌這兩種文體雙向地滋養(yǎng)與糾正:“詩(shī)歌促進(jìn)了散文對(duì)形而上的渴望”(布羅茨基),而“詩(shī)歌必須寫得像散文一樣好”(龐德)。
在《浮生記》這一組詩(shī)中,散文的日常性、駁雜性、及物性得以進(jìn)入:意象與細(xì)節(jié),書(shū)面語(yǔ)與口語(yǔ),沉思與抒情,正融合為一。而日常生活入詩(shī),對(duì)詩(shī)人是一個(gè)考驗(yàn)——“坐在椅子上,安靜得如同一根導(dǎo)火線。”像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那樣,必須對(duì)自己所引發(fā)的毀滅或絢爛,充滿不安、不凡的預(yù)感。
當(dāng)下,不少詩(shī)人僅僅是寫著“導(dǎo)火線”字樣的濕繩子,坐在論壇上、沙龍里,姿態(tài)別致而又安全,但無(wú)效。有效的寫作,就是辨認(rèn)出那偽裝得如同禮盒一樣的火藥、那修飾得如同眉筆一樣的火柴,去防止或者加速夜色的毀滅——讓焰火在一瞬間絢爛。
有效的寫作,也必須是充滿差異化的、異質(zhì)性的寫作,才有存在價(jià)值。克服時(shí)間的單向性流逝——史蒂文斯說(shuō):“一切詩(shī)歌都是試驗(yàn)詩(shī)歌。”反對(duì)既定的范式,在差異化、異質(zhì)性的寫作中顯現(xiàn)實(shí)驗(yàn)性、先鋒性。當(dāng)下,“實(shí)驗(yàn)詩(shī)”“先鋒詩(shī)”似乎被特指為“某一類型”的寫作,而一旦進(jìn)入“某一類型”,還存在實(shí)驗(yàn)性、先鋒性嗎?實(shí)驗(yàn)、先鋒,從來(lái)都不是個(gè)別人的標(biāo)簽和專利,而應(yīng)是基本的寫作倫理:脫胎換骨,蟬蛻蝶化,從少年寫到中年、老年,越寫越好——像一生不斷嬗變的葉芝,像經(jīng)歷過(guò)藍(lán)色時(shí)期、紅色時(shí)期的畢加索。
與其他文體相比,詩(shī)歌天然具有孤身奔赴的姿態(tài)和氣質(zhì)。扯旗立派、呼朋喚友的“先鋒”“實(shí)驗(yàn)”陣容,是一支可疑的軍隊(duì)。一個(gè)人暗夜獨(dú)行、無(wú)人喝彩,方能在寂靜處感知自我、辨認(rèn)晨星。
“詩(shī)壇上無(wú)法浮現(xiàn)出令人顫抖的圣潔共識(shí)。微妙的、遙遙領(lǐng)悟的默契,率領(lǐng)不了全局。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的此種失律現(xiàn)象,造成了它內(nèi)部的投機(jī)、虛偽、急功近利的藝術(shù)欺騙……越過(guò)了邊界的小型罪惡,積日累月,歷久經(jīng)年……”評(píng)論家徐敬亞曾在一篇文章中表達(dá)了自己的沮喪和焦慮。但我相信,詩(shī)歌擁有糾正、修復(fù)、拒斥、消毒、淘洗等等能力。相信真正的寫作者之間,依然存在隱秘的“令人顫抖的圣潔共識(shí)”、“微妙的遙遙領(lǐng)悟的默契”,那就是:真誠(chéng)與獨(dú)到。
即便我的“羞恥與失敗”還不夠卓越,我起碼可以做到拒絕投機(jī)、虛偽、急功近利,對(duì)母語(yǔ)保持赤子之心,而不要成為制造“小型罪惡”的人。
喜歡北宋黃庭堅(jiān)的一對(duì)好句子:“謝公文章如虎豹,至今斑斑在兒孫。”——戴虎頭帽子、穿豹紋褲子,能假裝成一個(gè)遺傳了前賢血液的英俊后生?我把黃庭堅(jiān)和李白的兩個(gè)句子集在一起:“桃李春風(fēng)一杯酒,與爾同銷萬(wàn)古愁。”以漢語(yǔ)為酒,越代同歡,可銷盡春風(fēng)萬(wàn)古愁——一個(gè)笨拙的人,倘若能夠以筆為盞,干杯,就是幸福的人了。
李白、黃庭堅(jiān)之后,陸游出現(xiàn)了:“記取江湖泊船處,臥聞新雁落寒汀。”歷代寫作者的書(shū)桌,都是停泊于書(shū)房里的船,以寫作一一記取新雁的振翅、鳴叫聲,對(duì)于正在加速降溫的生活,有暖意,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