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
◎王春華
蒲公英
◎王春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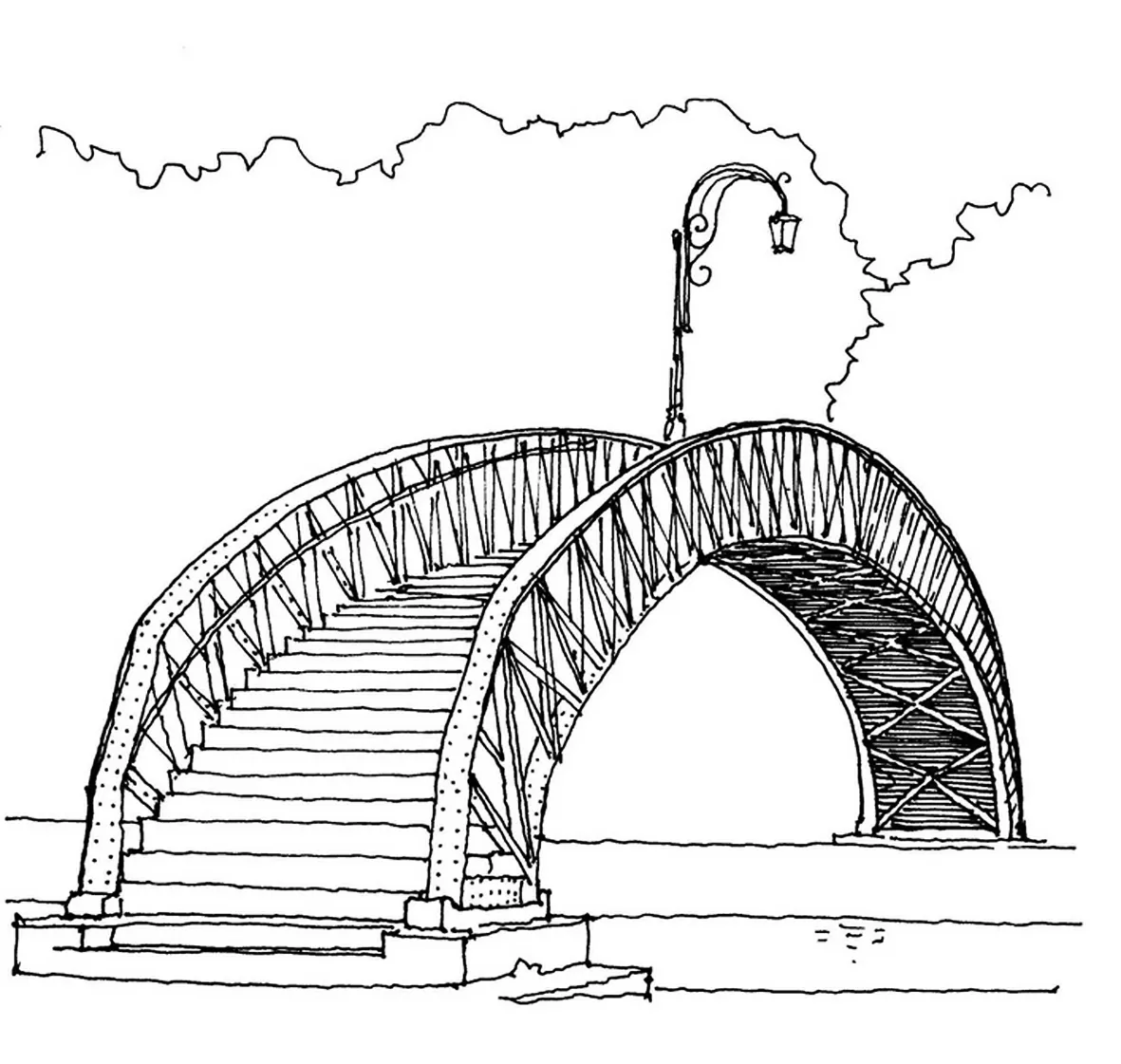
一
簡秋在體檢時查出乳房里長了個腫塊,雖然醫生說是良性的,但她心里仍然有個陰影抹之不去。簡秋敲開了老聞的房門。
“你怎么來啦?”老聞動作遲疑,關上門。
簡秋兩手捂住臉,哭上了。她這是賭,直接找上門來。幸好他在。她不敢先打電話,怕老聞把話說絕,反正電話里看不到臉,容易下狠心。兩個人好好散散多少回了,這又是四五個月沒聯系了,她不主動,他也沒爭取。
“怪不得過年你沒找我,又有新歡了?”
老聞抽了兩張紙巾,塞進簡秋右手的虎口間。“初三那天我去了,我在樓下看見你兒子他爸站在窗口,我以為你們要復婚,沒敢打擾。當時我還去超市買了些吃的,想跟你好好聚聚呢。”
她抓住紙巾,吸去淚水。“過年孩子他爸是來過,孩子大學要畢業了,我們商量給孩子找工作的事。”
“你這是借口。電話里不能商量嗎?”
“……”
是能商量,可見面三分親,時間充分,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效果總歸不一樣。再說孩子非要爸爸回來,原裝的三口之家一起過春節,算不得熱鬧,卻不孤單。當初,發現前夫有外遇,她要死要活離了婚,沒成想過了十年了,新家就再也沒能撮起來。前夫跟外遇結了婚,又離了,新找的女人回家陪父母過年去了,他樂得回舊巢陪兒子。他挽起衣袖,做飯收拾屋子,讓她產生了溫暖的錯覺,當年的恨早就淡了,不然她斷不會允許他進門。只是,分開這么多年,各自尋著各自的情路越岔越遠,誰都沒想法了。
“我跟孩子他爸,根本就沒有復婚的可能。”
“我知道,挑明了吧,我就是你的一個備用胎,這段時間是不是沒人理你了?”老聞盡量用平和的語氣說出這話,拉過屋里唯一的一把椅子坐下,椅子是折疊的,因為沒伸展到位,“咕咚”響了一下。
“別說得這么難聽,你知道,我是愛你的。”仿佛這句話是簡秋帶來的禮物,使她有了底氣,有勇氣抬頭看著老聞。
“可是,我已經答應跟別人處了。”老聞平靜地坐著。
簡秋手捏著皺巴巴的紙巾,又捂上臉,抽泣起來。
老聞只好問:“吃晚飯了嗎?”
“吃了。”簡秋不斷地擦眼睛,聽見老聞站起來,開了燈,拉上了窗簾。天這么快就黑了呀。
“坐一會兒,眼淚干了,就回去吧。”
簡秋剛擦去的淚水又洶涌而出,不再說話,只是肩膀聳動。老聞嘆口氣,坐到了她身邊。“你這是何苦呢。”
兩人再無話,屋里只有簡秋擤鼻涕的聲音。她瞥見老聞兩手在小腹前搓著。五年前,也是這個季節,一天晚上,在小廣場的納涼晚會上,她就站在他旁邊。城市很小,老居民即使沒有明確相識,也聽說過,恍惚有印象,她知道他也是一個人,五十多歲了,卻一點也沒發福,身材像三十多歲,臉也就四十來歲,皮膚繃緊,有模有樣,讓人喜歡。這個年齡的男人,哪個不是肚子高挺,虛腫著悶俗的大臉,能保持這樣實在也令人稱奇,她不免多看了他兩眼,而他也在頻頻看她。即使年過四十,她也仍是漂亮女人,高個子,大眼睛,黑長發,身材豐滿筆直。當主持人邀請觀眾上臺唱歌時,他勇敢地上去唱了一曲,賺了一片喝彩聲,她內心頓生好感。后來,兩人還跳了一支舞。但僅此而已。過了幾天,一個朋友來替老聞說媒了,簡秋沒同意。老聞不死心,有耐心,一到情人節和三八節就隱姓埋名給她送玫瑰花,三年送了六次,仍沒著落的簡秋一朝醒悟,執執拗拗地接受了他。
想到這兒,簡秋說:“當初是你追的我,你不能這么就完了。”
“不是我要完,是你要完。去年,不是你讓我搬出來了嗎?”
簡秋在外地的姐姐來看她,要住在家里,要給她介紹一個有望再婚的人。她從沒跟姐姐說起老聞,他不能在這個家留下任何痕跡,他不在的時候,她把他的衣服和洗漱用具都收拾好了,塞進一個提包里,等他一回來,就叫他拎上走了。姐姐走后,簡秋跟那個人又見過幾次,沒有下文。老聞賭著氣,沒說要回來,她也沒邀請,兩人若即若離地懸著。
想了一下,簡秋說:“過去的事了,你還記著,你也沒明說結束啊。”
“我……”老聞看看簡秋梨花帶雨的樣子,改了口:“別哭啦,躺下睡一會兒吧。”
簡秋不動,只是哭。老聞終于伸出手,將她扳倒,她掙扎著,起來。他再把她扳倒,她再起來。反復好幾次,老聞嘆息一聲,坐著不動了。后來,他打開電視,說看會兒電視吧,她沒朝電視瞟一眼,自己又抽了紙巾,攥在手里。老聞說:“不早了,我送你回家吧。”她的淚水就又沖開了閘門。
不覺到了半夜。簡秋的眼睛腫成紅桃了,老聞說:“不回家,就在這兒睡吧,幸虧明天周六,要不你咋上班?”說著,又伸手將她扳倒了。簡秋把臉捂在床單上,嗚咽著說,單位體檢了,她乳房里有腫塊。
老聞嚇了一跳,俯身問:“良性惡性的?”
憑這一問和那著急的語氣,簡秋明白,老聞根本就放不下她。她心生安慰,一感動,眼底的水泵又把淚水抽上來了。“看你,別哭了,對腫塊不好。大夫說吃什么藥?”老聞在她身邊躺下來,手搭在她后背上。
“不用吃藥,過半年再去查一下,看看長大沒有。”
簡秋覺得老聞的手摸上她的頭發,他最喜歡她的長發了,他在她頭上拍了拍。“沒事兒,良性的,沒事兒。”她突然翻過身,貼進他懷里。
二
關系暖回初期,雙休日一半的時間,簡秋都是膩在老聞這里度過的,一時忘了這里的簡陋與寒酸。后改建的小廚房,只能一個人在里面轉,連個冰箱也沒有。有時她想,老聞如果從未離婚,現在的日子會怎么樣呢?她沒問過他第一次離婚是因為什么,畢竟是久遠的事了,中間還隔著另一場婚姻,跟她現在的生活不沾邊,只知道他是凈身出戶,連工資都是前妻月月去領,一直領到他再婚。他第二次離婚,是買斷工齡下海撈金后,與一個賣運動服的女人結婚,住在女人的房子里,幫忙撫養女人的孩子,因為生意需要,他去外地兌了一個攤床賣窗簾,掙了錢就打到他們共同的儲蓄卡上。有天,他聽說那女人跟別人好上了,他趕回來探個虛實,發現卡上的錢都讓她轉走了。后來,他又賺了點錢,給兒子結婚用了。再后來,總是賠錢,能領可憐的退休金了,收手上岸,生活就成了這種狀態。
不過,在簡秋眼里,老聞有才,歌唱得好,還會寫點文章,他祖父活著時是個中醫,醫術沒傳下來,到老聞這,多少還有些中醫知識。這些,應對一個普通女人也就夠用了。還有,他不吸煙,不喝酒,不打牌,也是簡秋喜歡的。
他們都小心著,沒有像以前那樣再搬到一起住,只是周末的時候,老聞到簡秋的家里過一夜,在那里,云啊雨啊,畢竟方便。周六或周日,簡秋會有一天過來,給老聞送點她自己做的吃食,看看老聞在干什么。
有天,老聞拘在筆記本電腦上查資料。簡秋湊近了一看,詞條是“蒲公英”。她說:“這不就是婆婆丁嘛,你查這個干嗎?”
“我聽人家說,婆婆丁的根挖回來熬水喝,能治你那個腫塊。我查了一下,百度上說《本草綱目》是這樣說的,根能消炎去火,化解癰阻。”老聞拖動頁面讓簡秋自己看。
菊科草本植物。葉子灰綠,鋸齒狀。開黃花。絮球白色。根莖粗壯,褐色。
簡秋一目十行,不想細看。“婆婆丁誰不知道啊。我兒子小時候,我還給他念過兒歌呢:一個小球毛蓬松,又像棉絮又像絨,對它輕輕吹口氣,飛出許多小傘兵。”
老聞說:“我小時候,一到春天,放了學,我媽就把我趕到野地里去挖這玩意兒,回來蘸醬吃,真苦,沒辦法,那時沒大棚,到了春天沒菜吃。看來我得重操舊業了,馬上入秋了,到時我去給你把根都挖回來。咱們看看,能不能把你那個東西化掉。”
“老聞,你對我真好。”簡秋頭靠在老聞的肩膀上。
兩人都盯著電腦屏幕。老聞一手摟著簡秋的腰,一手劃動著鼠標的滑輪,繼續往下拖頁面。他說:“你看,在這兒呢,清熱解毒,消腫散結……”簡秋突然打斷他:“別動,看這句,什么 ‘花語’?婆婆丁也有花語?‘無法停留的愛’?”
一時,都呆住。
蒲公英,無法停留的愛。終歸不像玫瑰、康乃馨、勿忘我什么的,語意令人寬慰。以兩人的常識和童年就獲得的認知,這會兒,一個映像自然地在他們腦海里轉,那是蒲公英青紫色的空心花莖,頂著蓬松的棉白絨球,忽然風來,球絮突地橫向飄移,悠忽翻飛,前路茫茫。
兩人相互覷了一眼,似乎碰到了尷尬的問題,目光又趕忙轉到電腦上。他們生活的小城,靠近中俄邊境,開放前,城里只有兩萬人口的時候,絕大多數人的婚姻都是完整的,個別離婚的人,一定是人們嘴上的怪物。而今,小城燈紅酒綠閃亮,拉出個不起眼兒的人,不是富豪就是土豪,官方統計的常住人口有六萬多,遍地是至少離了一次婚的人。他們當中能再婚的人不多,且婚后也過不了多久,總會因為這樣那樣的矛盾又再次分離。老聞如此,簡秋也在怕著前面的車轍。
到底還是老聞轉得快,食指“咔嗒”一點,關掉頁面。“管它什么花語呢,咱們要的是根。”
轉眼秋涼,老聞送來了蒲公英的根,泥土都抖掉了,仍散發著潮濕親切的微腥氣息,還有一點苦味。
簡秋的微笑著實可用幸福來形容,熬水成了她的頭等大事。她很認真地清洗那些根,放在鋼精鍋里,先大火燒開,再小火慢熬。滿屋子都是苦森森的氣味。老聞打開了窗子,說她一定要多透空氣。他的老毛病又犯了,晚上睡覺,一定逼她泡過腳再上床,說腳是人的根,要好好養護。她嫌麻煩,他不來的時候,能省就省。他來的這一晚,也是他把洗腳盆放在她腳邊,泡完了,再給她擦干。早晨起床,他逼著她一定要將頭伸出窗外,用鼻子而不是張大嘴巴,呼吸十口新鮮空氣,清洗她的肺。
“又來了,你活得累不累啊。窮講究。”
話一出口,簡秋立馬后悔了。“窮”和“講究”本不搭邊兒的,老聞偏偏將二者糾合在一起,她這樣說,他不會敏感吧。
老聞卻說:“這不是講究,是生活的態度。因為窮,才要呵護好自己的生活。那些財大氣粗胡吃海喝的人,是在禍害自己的生活。”又說:“你也不小了,以后凡事想開點,在單位不要跟那些女人計較,腫塊都是因為氣上來的,氣瘀造成的。”
“你說得輕巧,就那個環境,不氣才怪。”
簡秋單位女人多,是非多,見天議論的都是誰的老公是哪個單位的頭兒,誰的老公是千萬老板,誰是小三兒,誰是小四兒。有次,簡秋聽她們議論她,挑挑揀揀這么多年,怎么看上一個窮光蛋,有點才有什么用,能解決什么問題?讓簡秋不郁悶,是不可能的。
“你得自己有個好心態,不說清心寡欲,也別欲壑難填吧。你看那些長壽老人,有幾個是大富大貴的,都是窮鄉僻壤無欲無求的人。”老聞說。
“你老啦,我還年輕呢。”簡秋耍賴。
第一次喝完一杯苦巴巴的水,簡秋和老聞躺在簡秋的床上。老聞摸上她的乳房。“是這邊吧?我要讓我的手指記住腫塊有多大。”“錯啦,是這邊。”簡秋將左乳挺過去。老聞認真地摸著,不疼,卻有點癢。簡秋一直怕癢,以前,老聞想讓她服,只撓她癢就行。說也奇怪,愛得神魂顛倒時,老聞摸她哪兒都不癢,只覺得受用,時間久了,疲沓了,主管情欲的那根神經麻木了,老聞一摸她就癢,她就將他的手推開。這會兒,老聞的手雖是再熟悉不過,卻像回鍋肉,總還是有滋味的。
老聞說:“哦,有黃豆粒那么大呢。我堅持挖,你堅持喝,過段時間看看,小了沒有。”
三
“哎呀,太麻煩了。還費煤氣。”
“我挖的都不嫌煩,你喝的還煩了?”
“苦啊,太難喝了。”
“唉,實在不能替你喝,堅持吧。”
有半個月的時間,老聞隔兩三天,就挖回一些婆婆丁,有時送上門來,有時是簡秋去他那取回來。為了老聞這番好意,簡秋皺著眉、捏著鼻子往下喝。每次她都是像老聞教的那樣,像熬別的中藥那樣,熬三遍,三遍的水再兌一起,裝進一個蓋子密封的大水杯里,在家里喝,也帶到單位去喝,一打飽嗝,滿嘴苦味,叫她直想吐。
期間,簡秋自己摸過那個腫塊,對老聞說:“咋一點也沒見小啊?”
“哪能這么快,你那個寶貝也不是三天兩日長成的。來,我給你揉揉,雙管齊下興許有效。你早跟我結婚,我天天給你揉著,哪會長這東西。”
簡秋轉了話題。“你把那個女人怎么樣啦?”
“什么女人?”
“你懂的。”簡秋也用上了網絡流行語。
“哦,”老聞聲色寡淡,“我跟她說不處了,她挺遺憾的,現在有時還發短信。”
“你能說不處就不處了?真放得下?”
“有什么放不下的,剛認識,不像你,戀了這么多年了。”
簡秋突然咯咯笑。
“你笑什么?”
“有點癢。”
“侍候你不容易,重了吧,疼,輕了吧,你又癢。”
老聞翻過身去,很快睡著了。簡秋披上睡衣,去了趟洗手間,敞著懷兒,她看到了自己的乳房,稍微有點下垂了,但飽滿度還是可以的,看不出那個腫塊,那個潛伏的殺手,難道未來,健康和美麗都要毀在它的伏擊下?苦口良藥,還是繼續喝下去吧,反正喝不死人。
這天,是個周六,簡秋本來要去美容院,老聞卻讓她在家等他。不到中午,他就拎著一袋菜根來了。“我下午去我兒子家,孩子他媽住院了,他去陪護,讓我幫他照看生意。”老聞的兒子在兩百里開外的鄰縣,開著一個小超市。
“要多久?”簡秋問。
“得一個星期吧。這不,我多挖了些,夠你喝一氣的。”
簡秋接過菜根,抓出一大把泡進水里。“那你吃完飯再走吧。”她開始洗菜做飯。
老聞挖了一上午菜根,走了不少城外的土路,真有點累了,洗了手去沙發上坐著看電視,沒幫忙。簡秋將米下到電飯鍋里,一個灶眼兒煮水,一個灶眼炒菜,不到一小時,兩人就坐下吃飯了。快吃完時,老聞嗅嗅鼻子。“什么東西糊了?你灶上有什么?”
簡秋一個激靈跳起來,一步躥到廚房去。是蒲公英的根讓她煮糊了。“你怎么不多添點水?你別看這東西多了,就不珍惜,婆婆丁都快讓我挖沒了。”隨后跟來的老聞,表情有點心疼。
“我是想少添點水,煮濃點喝。這破記性。”
“沒事兒,這邊挖光了,我就辦個護照,到邊境那邊去挖。”老聞又回飯桌邊,繼續吃飯。
簡秋笑,忙著去開窗,把屋里肺里的焦糊氣排出去。當她把客廳的窗子打開,愣了一下,對面稅務局辦公樓二樓的窗口,站著一個男人,正在看三樓她的窗口。男人急轉身,離開了。簡秋覺得這面孔似乎在哪兒見過。
秋光見深,田野的色彩斑斕好看,卻是冷涼得很了。簡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跟著老聞來挖婆婆丁根。上次,她把水熬干了,浪費了老聞的勞動成果,有點不好意思,再說,一直都是老聞在挖,全是為了她,她也該有所表示才好。
小城一年年擴建,曠野越退越遠了。出來一次,沒有以前那么近便了,但簡秋興致不錯,就當郊游好了。他們沒有鐵鍬、鎬頭這些大家伙,每人只帶了把小刀子,看上去真就是郊游的兩個人。老聞說:“別的地方都讓我挖沒了,就這東山崗才來過兩次,就在這兒挖吧。”
簡秋彎下腰,在草叢中尋找著。若不是老聞提起,誰還記得蒲公英這低調不起眼兒的植物呢?到了這時節,蒲公英還開著黃花的已經不多,葉片又是破碎的,灰綠色的,混在雜草里很難發現,簡秋轉悠半天也找不到一棵。老聞找到一棵讓給她來挖,她又吭哧吭哧半天也挖不出來。
“這東西這么難挖呀?”她蹲在那里,兩手握著小刀掘土,刀尖挑上去了,卻沒有一點土起來。
這點她可沒有老聞有經驗,暄土地里的蒲公英是很容易挖的,但是根比較細小,他懷疑藥性不足,所以專找白漿地和堅硬的地帶去挖。挖出的根又粗又長,黃棕色的,看著才像藥材。但這樣一來,這簡單的事情變得艱難了。土地太硬,挖不動,還要掘得很深,半天才能挖出一根,指甲縫里都是泥土,指蓋生疼。有時挖得深度不夠,拔不出來,蒲公英的葉片斷在手里,奶白色的汁液沾在他手上,又混上泥土,弄得手又臟又黏。
“你以為呢。有用的東西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嗎?”老聞瞥一眼簡秋,見她腦門上已浸出汗。“挖不動就別挖了,拎袋子吧。”
簡秋真就放棄了努力,拎起塑料袋,跟在老聞的后面。
老聞也挖得吃力,秋陽在近午的時候也很威猛,他腦門上也是汗津津的了。簡秋說:“真不明白,這婆婆丁就這么幾個小葉片趴在地上,多大的風也刮不走,有什么必要長那么壯的根?不成比例嘛。”
“你不知道,它吸收了多少陽光,多少土地的營養,就是要成就自身的藥用價值吧。”
“我們這么忙活,誰知道是不是瞎忙?我摸著腫塊沒什么變化。”
“還是今晚讓我來摸摸吧,沒再長,證明努力有效。”
“我都喝夠了,太苦了。”
只聽清脆短促的一響,老聞手里一截根出來了,另一截斷在土里。“小時候吃婆婆丁蘸醬,都是吃葉兒,從沒吃過根,我現在吃口嘗嘗。”老聞說著,將手里半截菜根擦了擦泥土,咬了一點在舌尖上,立刻一口口連吐吐沫。“真苦。”
簡秋笑著說:“你以為你挖得不容易,我喝得就容易嗎?”
“都不容易。”老聞說,“干活的不容易,享用的也不容易。現在這社會,咋都活得不容易。”
“我可不想回答這么傷腦筋的問題。”簡秋在一個清閑的單位上班,思想簡單地活著。
四
老聞挖出一棵,站起來再找一棵,簡秋也跟著一會兒站起來,一會再蹲下。快到中午的時候,簡秋的手機響了。“喂。”她看一眼老聞,放下塑料袋,起身走到一邊去了。
來電話的是稅務局副局長肖云峰,怪不得簡秋那天在窗口看著面熟呢,原來是中學同學。老聞不在期間,他們見了一面,是在他辦公室,當時他下班剛走出大門,而她下班回來剛要進小區,他喊她:“簡秋!”她愣過后,馬上笑著點點頭。他說:“看來你把我忘了,我是肖云峰。”她這才將早年并不深刻的印象拼接起來。那時候,分班太頻,跟肖云峰做同學也就一個學期吧,后來他上了大學,畢業后在外地工作。聊起來她才知道,他最近這是剛調回來。中學時,他是個瘦猴子,現在整個人膨脹了一倍都不止,怪不得她認不出了。“沒想到你也會胖成這樣,沒少腐敗吧。”肖云峰難為情地一笑:“你沒怎么變,還是那么漂亮。我可是你的粉絲。”“假話吧。”簡秋嘴上這么說,心里很受用。
肖云峰說晚上要請簡秋吃飯。她扭頭看了一眼老聞,他正眼睛盯著手,心無旁騖地在挖。她知道他張著耳朵呢,不由得腳步邁動著,慢慢走遠了。等她收起手機回來,老聞瞄她一眼。“看你挺開心的,臉上甜蜜蜜的。”
“瞎說。”“誰呀,說這么半天?”
“一個朋友,你不認識。我再去給你找一棵。”簡秋背對老聞,彎下腰移動腳步,瞪大眼睛,真的想找到一棵婆婆丁,掩住自己的不自在。
“你腳下就踩著一棵,還瞎找什么!”老聞站直了,盯著簡秋的臉。“是個男人吧?”
“你管呢。”簡秋蹲下來,開始挖腳下那棵蒲公英。
老聞“唉”了一聲蹲下去。“聽說稅務局的肖局長對你好。”
簡秋心里“咚”的一跳。“他對我好是他的事,該我啥事?”
“他可是有老婆的人。”
“那是他的事,該我啥事?”簡秋的小刀子一下下戳著地,只是一個動作而已。
“你小心,現在這些當官兒的,哪個屁股干凈?說不定哪天他犯了事兒,小三兒小四兒的都抖出來了,看你臉往哪兒放?”
簡秋忽地站起來,怒視著老聞:“我又沒說真的要跟他好,你吃的哪門子醋?”
“你喜歡他這樣吧?我從你臉上都看出來了,又不是小姑娘,還喜歡所有的男人都圍著你轉嗎?”
“你……”簡秋扭頭走了兩步,又回來:“他說能給我兒子找工作,我相信他有這個能力,你能嗎?”
老聞挨了簡秋一棒子,撲地坐在地上。簡秋硬著心腸,匆匆往城里走了。她要去做個臉部護理,再做一下頭發。她突然明白今天為什么會陪老聞一起來野外,是心懷愧意,但轉而一想,也就輕松了,老聞不是也有個女人嗎,說是不處了,誰知道真假,那一周,誰知他是不是真去兒子家了?
簡秋住的這幢樓房,跟對面的稅務局只隔一條不太寬的街道,怎么會這么巧呢,她竟然是這樣與肖云峰相遇。每天,他都提前來辦公室,站在窗口朝她的窗口望,她上班走之前,到窗口站一下,兩人對對眼兒,笑一笑,做個手勢。她曾笑著對他說:“你們男人,但凡有點出息,就開始不講道德。”他說:“男人根本就沒有道德感,喜歡一個女人就是喜歡,跟道德沒關系。”跟老聞吵架的那天晚上,肖云峰請簡秋去的是西餐廳,那里面不容易碰上熟人。她問他:“你不覺得對不起老婆嗎?”他說:“事情應該隔開了看,此時此刻,在這個空間,就咱倆,這就是合理的。”簡秋與肖云峰的交往便放松了。反正她不會笨到還幻想他會離婚娶她,既然如此,大家各自為自己負責,不為別人背包袱。
那天晚上,跟肖云峰分手回家,門口堆著一個大塑料袋,里面的蒲公英根比她摔下臉子離開老聞時多出一倍。她拎起來,手一沉,心也跟著一沉。不過,時間有點晚了,這一天內容也很多,她有些累了,將那一包東西丟在陽臺上曬著,洗洗睡了。
隔了四五天,老聞來電話了。簡秋說喂,老聞說喂,然后就是沉默。簡秋等著老聞說話,他先打電話過來,還是有話要說吧。過了幾秒鐘,老聞說:“你沒忘了熬水喝吧?”
“那些婆婆丁……”
“堅持下去,對你有好處。快上凍了,不好挖了,再說也不大有了,我想再去給你挖一些,哪天你跟我一起去?多挖點存著。”
“哪天?我可能沒時間。”簡秋正琢磨撒個什么樣的謊,老聞在那邊說:“過兩天就是中秋節了,我上你那,還是你上我這兒?”
“中秋節,我姐可能要來。”
“那好吧。中秋節我去我兒子家過。”
手機里傳來嘟嘟聲,簡秋松口氣,又若有所失。她走去陽臺上,看到那些野菜根半干了,這些天她一次也沒熬水喝,說不上是沒心思還是沒時間,乳房的腫塊她也沒檢查,當初那種憂戚怎么漸漸消失了?是習慣它的存在了,還是被老聞帶給她的安定感,抑或是肖云峰帶來的歡愉消彌了?
中秋節這天,簡秋起得晚,收拾完屋子,半上午過去了,剛坐下來喘口氣,肖云峰的電話來了。“你到窗前看看我。”她手機捂在耳邊,走到客廳窗前,就見肖云峰正正當當站在對面一個窗口,兩人可以平視。她問:“你辦公室不是在二樓嗎?”“嘿嘿,為了看你,我把辦公室調到三樓了。”他向她擠擠眼睛。她笑。他說:“我馬上過去,中午陪你一起過節。”
肖云峰拎來一袋紅提葡萄和一瓶紅酒,放在餐桌上。簡秋心知肚明,晚上,他得陪老婆。中秋實際上討的是月亮的喜,大白天的,吃啥喝啥都沒氣氛。但今天陰云低沉,說不定什么時辰雨就下了,月亮圓不圓,對大家都公平。
簡秋的心又亮起來,兩人一起到廚房包餃子。一個剁肉,一個和面,很快就進入搟皮包餡階段。肖云峰冷不防給簡秋的臉上抹了一道白面,簡秋立刻反擊,卻不能得逞,正膠著,門鈴突然響了。
兩人立刻安靜下來,互相望一眼。簡秋小聲說:“不管是誰,不理他,現在是我們倆的世界。”他們放輕了動作,繼續包餃子。門鈴又響了一遍,再無聲息了。簡秋輕腳走到門前,眼睛貼到貓眼上。樓道里沒人。她輕輕打開門,門口旁邊放著一個塑料袋,是蒲公英的根,帶著新鮮泥土,不過不是很多。她拎進來,放到離門最近的小屋去,又回到廚房。
“什么情況?”肖云峰問。“不知道是誰,以為家里沒人,走了。”
簡秋洗了手,擦干,拿起一張皮正要打餡兒,聽到手機來短信了。她又跑到客廳茶幾上抓起手機。只見老聞寫道:“簡秋,對不起,有人給我介紹了一個女人,這回是真的,上次是我放出風去騙了你,因為我受不了孤獨。這些是最后的婆婆丁了,真想給你多挖一些,可天冷了,真的沒有了。你好自為之。”
鼻頭一酸,眼淚刷上來,簡秋生生逼了回去。她急忙跑上陽臺,老聞應該從那過去,卻沒有影子,密不透風的灰云堵滿了窗口。肖云峰問她干什么呢,她抓了一把已經干透的蒲公英的根,換上一副開心的表情,回到廚房。“是什么?”他好奇的目光盯著那團褐色的東西。
她不答,只嘩嘩啦啦找出菜盆,放進手里的東西,接了水泡著。轉過身,臉上快樂的表情更加夸張,一邊包著餃子,一邊講起單位里的人那些可笑的事,還有手機短信里可笑的段子,然后開心大笑著,一直到坐下來吃飯,兩杯紅酒喝下,她的話遲頓起來。
“我喝多了……今天真開心……哦,喝得太多了……”
簡秋趴在桌上,臂彎里傳出抽泣聲。

王春華,杭州市康橋中學語文老師,業余喜歡故事與小說創作,2008年開始發表短篇小說,作品散見于《短篇小說》《上海故事》《故事林》《意林》《人民文學》《青年作家》等雜志,多篇作品被《讀者》《青年文摘》轉載。
責任編輯/董曉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