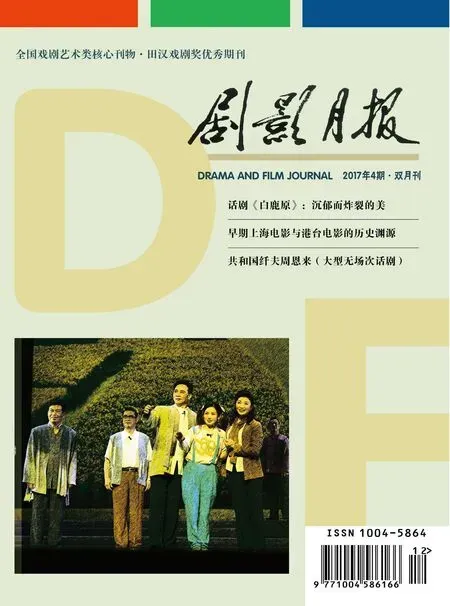錫劇的傳承與發展
■仰淵文
錫劇的傳承與發展
■仰淵文
“錫劇”這個名字,早在我兒時就進入到我懵懂的心靈,各個年齡段都有著各不相同的理解。我父親是個“錫劇迷”,從收音機到錄音機,再到現在的DVD,劇不離身。從小的熏陶,使我深深愛上了錫劇,走上了錫劇專業的道路。錫劇這一劇種在戲曲百花園中有著獨特的魅力,從大的范疇來說也是地域文化的魅力,這種魅力恰恰是錫劇能生生不息得以傳承的源泉。就如我,首先經歷了父親的愛好,我的好奇,漸漸進入到滲透,覺得錫劇原來有這么美的曲調,再加上科班對形體的再造,然后成為了一名合格的錫劇演員,這不就是一個完整的傳承過程嗎?所以說,傳承要靠行動,路就在腳下。
說到傳承,首先我們要從這一種藝術形式的根說起,那就是地域文化對戲曲的影響,我們要從中國的“五大語系”說起,即粵語、吳語、湘語、閩語、贛語。不同語系發展出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而不同的地域文化又孕育出不同的地方戲曲。無錫一帶就在吳語范疇之中,在這片土壤上,孕育出了錫劇、越劇、滬劇、蘇劇、婺劇等吳語劇種,錫劇發源于蘇、錫、常一帶,有著較深的群眾基礎。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成為了江蘇四大劇種之一,傳播地域北達鹽城(大豐錫劇團、東臺錫劇團、靖江錫劇團),東至上海、啟東(嘉定錫劇團、青浦錫劇團、啟東錫劇團),南到浙江(嘉興錫劇團),西至安徽(郎溪錫劇團)等地,發展地域之廣實屬罕見。
隨著時代的變遷、多元性文化的介入,錫劇這一劇種也自然受到了不小的擠壓,錫劇這一劇種隨著人們年齡的更替相應疏遠。如何保持錫劇在地域文化中的定力與地位,就需要我們每一個“錫劇人”做好錫劇的傳承工作。
傳統錫劇素來都是以“人”為核心,不論是在日常的演出中,演員通過唱、念、做、打,富于美感地展示自身對于角色的形象塑造與刻畫、心理狀態的描摹與外現的表演藝術,還是師徒傳承的技藝延續方式,都充分體現著戲曲將人體自身的能量作為戲劇最本質的表現手段,及其對演員身體表現性的重視和張揚。藝靠人傳,錫劇藝人用自己的生命把錫劇傳承了下來。錫劇的實體也正是借助著一代代錫劇演員精湛的表演、傳承與創造,才得以穿越時光不斷重現。人在曲傳、人散曲終,對傳統錫劇藝術節的保護和研究,顯然還遠遠不夠。因而,當下更應重視的是搶救、傳承與弘揚。
尤其是戲劇程式,作為前輩留下的經過數代人積累、提煉的特殊遺產,具有著非凡的形式美和表現力,更是輔助戲曲演員塑造人物、抒發人物情感的重要手段,已經不僅僅是技藝,其中蘊含了強大的文化信息,并非短時間內就能被“消化”,須先將之原汁原味地繼承,才可能在日后真正進入到融會、化用的階段。因而,戲曲藝術的傳承和延續,是一個經過死學之后才能再進行活用的過程。尤其是對于青年演員來說,程式是根基,以“形”來接近“神”,由外而內地深入和提升個人的藝術能力,才能最終走向個性化的藝術創造。這是戲曲發展的一個規律,在此基礎上的創新才可能獲得成功,實現多贏。
對于錫劇唱腔藝術傳承,在錫劇諸多傳統技藝的繼承和化用的過程中,在長期的舞臺摸索與實踐中,很多錫劇藝術大家創造并形成了各具特色、凝結著自身演唱藝術精華的不同流派,如王彬彬、梅蘭珍、姚澄、王蘭英、沈佩華、王漢清、鄭永德、張雅陸、倪同芳等都有著鮮明的唱腔特色,形成了自己的流派,令錫劇的藝術表現力在舞臺上更為鮮活、傳神,對錫劇藝術做出了創造性的貢獻。
解放初期,錫劇靠著師徒間的口傳心授來學戲、傳戲。往往一出老戲要經過幾代人的研究、推敲,才能去粗存精,日趨完美。因此,得到真傳的骨子老戲的演出往往會令觀眾眼前一亮。縱觀錫劇史上的前輩名家,哪一個不是通過具體劇目的傳承、“一對一”的指導和打磨、自身大量的舞臺歷練以及在不同流派中的兼收并蓄,才日臻化境、自成一家的?這無疑也是錫劇藝術得以世代流傳而不衰的不二法門。
因而,在新創優秀劇目匱乏的當下,復排優秀劇目愈發顯得必要。在復排的過程中,不僅可以用優秀劇作的傳承,培育、磨練新一代的錫劇演員,令他們的技藝更上一層樓,有助于培養當下觀眾的欣賞品位,而且,老戲新排,在恢復原有框架的基礎上重新打磨和精修,也讓原創的優秀劇目重新獲得了生命力,避免了浪費。
當然,只有創新才能滿足觀眾日益增長的審美需求。但是,脫離傳統,又將失去民眾固有的、認同的欣賞基礎。只有充分發揮、開掘出民族戲劇傳統中的現代感,才有可能創作出真正兼具思想性和藝術性的戲劇作品。而正是中國戲曲自身存在、流傳和發展的特性,決定了其創新的前提必須是繼承,程式更是不可妄動,我們的地方戲劇,更應遵守這一點。只有在程式的基礎上,從創作理念、劇目的素材選擇、舞臺表現手法和導演的藝術形式運用等方面,充分配合、發揮演員個人的藝術特點,賦予傳統戲劇以新的色彩和韻味,才是當下戲曲創新的正途。
只有在保持民族化、地方化和個性化的同時,實現傳統與創新的和諧統一,才是一切創新的根本原則。那些創新獲得成功并能常演不衰的優秀錫劇劇目,如:《珍珠塔》《玉蜻蜓》《雙珠鳳》等,無一不是遵循著中國傳統戲劇自身發展的規律,緊緊抓住了戲曲的本質特點,以簡潔的舞臺手段、真摯的情感和精湛的表演藝術,將劇作所蘊含的豐厚內涵和現代意識傳遞出來。像省錫新排的《珍珠塔》《雙珠鳳》等優秀劇目,就是凸顯劇種自身的藝術特點進行創新而成功的典型。
《珍珠塔》以繼承為創新的根基,錫劇表演程式中極具藝術美感的“跌雪”被加以強化,以優美的身段,高腔入云的唱腔,合理將方卿這一人物在落難時悲慘的情景發揮到了極致。因而,全劇不僅以錫劇傳統的藝術表達,昭示了錫劇自身的個性和特色,而且以程式為“根”、并吸收了舞蹈的一些現代元素,深刻反映了方卿頑強性格的人物內涵,以一出精品劇目的常演常新,將古老劇種的傳統藝術精髓與時代融會并發揚了出來。同時,以創新來傳承古老的劇種,不僅使古老的程式得到了“復活”,更是戲曲藝術在精神上的一種傳承和發展。
錫劇傳承,說到底是人的傳承。這里面既包括演員的傳承,也有觀眾的傳承。就演員而言,要形成階梯式的人才隊伍,老中青三代結合,才能適應觀眾的不同需求。就觀眾而言,我們尤其要注重年輕觀眾的培養,不能總是黑頭發演給白頭發看。對沒看過錫劇的年輕觀眾而言,他們剛開始可能只是看看扮相、聽聽嗓音,但入門之后,他們慢慢就會懂得品味,能看出一部戲的好壞。這就需要我們能跟上時代,通過網絡、微博等新形式進行推介,多創造讓年輕人接觸錫劇的機會,培養新一代受眾群。
培養新的受眾群,從娃娃做起應該是一個很好的點子。大家都知道,八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一些新穎的文化進入了社群,例如流行歌曲顯然成為了當時的歌臺主流,一些傳統戲曲開始走向低谷,大有淡出人們視線之感。隨著時間的推移,流行的都“流”了過去,可傳統戲曲的受眾群顯然有一個明顯的“隔層代”,并嚴重影響下一代。因此現在補救的辦法就是從娃娃做起,把我們地方特色的地方戲曲錫劇推進小學特色班,通過特色班,向小學生普及錫劇知識,從而使學生愛上錫劇,并讓他們有上臺表演的機會,使家長也參與其中,我認為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傳承方式,不光傳承了錫劇藝術,還培養了一大批新的錫劇觀眾。
總的來說,要使我們的傳統錫劇有更好的發展,就必須要有堅守陣地的耕耘者,“錫劇人”有著義不容辭的責任,無論是外來文化的沖擊,還是時代的變遷,只有堅守我們的陣地,把準時代的脈搏,才能使我們的地方戲曲永葆地方特色,得以更久遠的傳承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