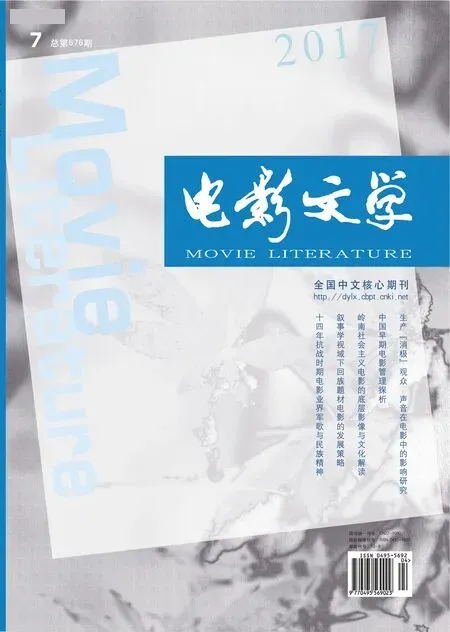由“小妞電影”看美國社會主流文化趨向
蘇 紅
(西京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3)
電影作為一種文化藝術產品,是社會文化的重要反映形式之一。新近崛起的小妞電影,無論是故事內容的豐富性,還是精神價值的深刻性,其與社會主流文化之間都是不太相稱的。前者實在渺小,后者太過龐大。然而,能夠將二者黏合一起、相提并論的根本因素,還是小妞電影亟待挖掘的諸多特質。不必引入煩瑣的理論來升華小妞電影豐富的知識內涵,只須了解小妞形象是美國年輕女性群體的代言,年輕女性追逐時尚美的內在驅動是引領美國消費文化變遷的主力。僅憑此兩點,就已經分解出消費和時尚兩大主流文化。再走進小妞電影內部,從其堅持獨立人格和實現自我價值的女性形象,能夠彰顯美國文化界一直強調的,個人奮斗與公共意識雙管齊下的價值觀。當然,一直被譽為思想“奔放”的美洲大陸,自然不能遺漏小妞群體“自我放縱”的人性魅力。
一、個人價值的體現
美國人尤其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個人能力證明的過程很容易被國人解讀為自私自利的性格特征,繼而將其上升到個人主義的高度。形成與東方“犧牲小我,保全大我”的文化沖突。不得不說,這是誤解了自我價值與個人主義之間的區別。自我價值的認定是美國主流文化之一,且不說《變形金剛》《蜘蛛俠》《蝙蝠俠》系列弘揚個人英雄題材的影片所極力贊揚的價值取向,即便是較為低調的小妞電影,也無處不在地肯定自我價值。
一方面,獨立人格是美國小妞們不容動搖的根本。盤點系列小妞題材影片,女主角事業有成的形象遍布其中。如《流行教母》中的模特海倫·哈瑞思,《丑陋的真相》里的艾比,都是堪稱絕世美女的代表,她們擁有魔鬼般的身材和漂亮的臉蛋,不過并沒有因此陷入不思進取的沉淪中。哪怕是《風月俏佳人》中的薇薇安,也不是因為依賴男人的金錢而自甘墮落。美國小妞始終以獨立的人格和事業有成作為自己的生存法則和首要目標,她們清晰地認識到,情感上只有做到人格獨立,才不至于失去自我,繼而掌握愛情主動權。事業上也只有能力過硬方可博得其他人心悅誠服的認同。探究背后的文化因子,個人主義是繞不過去的話題。他不等于自私自利,也不是唯我獨尊,與中國“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古言有相似點,而又更強調社會獨立性。明白至此,就不難理解為何成年后,美國父母常會“狠心”地將子女推上社會的浪尖,讓他們自主謀生。并非不顧及親情,而是深受主流文化影響。
另一方面,肯定自我價值并非拋棄公共意識。一味地強調個人觀念和追逐自我價值勢必造成削弱公共意識,甚至“小國寡民”的局限性。包容性極強的美國文化,自然不至于跌入此陷阱。只消品味美國小妞電影中的團隊精神和捐助意識,就能明白他們的公共理念是不亞于任何國家的。《丑陋的真相》中,為了艾比的愛情,同事麥克及其他好友全線出擊,只為博得本不適合她的科林。或許故事較為老套,不過是一群人與一個人斗智斗勇的范例,與《速度與激情》《美國隊長》之類為國家、地球生存而戰的勇士們相比,確實卑微得可憐。然而其背后承載的精神和意識是不容低估的。與美國大學運轉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校友捐贈的案例相似,麥克這類為朋友,貢獻自己力量和個人愛情的事跡,雖不是一個系統,卻貫穿著相同的捐助意識。更何況他們合作得如此天衣無縫。團隊精神與個人奉獻一直都是美國主流文化所積極倡導的價值觀。
二、女性地位的轉變
“小妞”的稱呼雖然不帶有貶義或輕視的色彩,但或多或少存在情感定性的判斷,她們或許是燈紅酒綠場所的舞伴,或許是商店的銷售人員、公司底層端茶倒水的員工,總之,很難將其與嚴肅大氣的場面直接關聯。而其形象也多是妖嬈嫵媚、花枝招展、鮮艷動人的,不足與威武正直的成功人士相提并論。但是,這些“通俗之論”在美國小妞電影中都或多或少地被顛覆。
首先,社會地位的轉變。誠然,美國小妞們還沒有擺脫以往的諸多窠臼,但在工作領域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沒有人能夠想到,執掌時尚界,擁有數萬人生殺大權的是一位打扮高貴,不沾一絲煙火氣的女性米蘭達(《穿普拉達的女王》);也不會想到知名出版公司的高管,會是一位比男人更強勢、氣場更陰冷的女性Margaret(《假結婚》)。員工見之,叫苦連天。對手遇之,如臨大敵。最令人驚詫的是《律政俏佳人》中的艾莉·伍茲,一頭金發,身著粉衣,腳登紅鞋,牽著寵物狗,混跡于法律專業學校。而學校里的其他人都是著裝樸素暗淡,顯得非常沉穩,畢竟他們都將走上嚴肅的法庭,面對人情冷暖最“黑暗”的場所。艾莉簡直就是一朵“奇葩”。她的成功不是在講述奇跡,而是證明女性權利地位的多元滲透。以上數位女性的成功都鮮明地揭示,小妞不是任人玩弄的花瓶,而是擁有不輸于任何人的才能,只要她們努力,同樣可以站在社會之巔。
其次,平等自由的落實。“小妞”社會地位的轉變固然離不開她們自己的刻苦努力,但更重要的還是自由平等觀念的落實。在高唱平等權利的今天,不否認于諸多領域已經取得很大進步,然當真正觸及自身利益時,很難做到“人格的尊重”。常常聽到招聘工作時,有歧視女性的現象,也不止一次聽說,婚姻選擇須門當戶對之類的勸告。這些都是小妞電影格外關注的焦點,其中以《風月俏佳人》最為典型。薇薇安本來是風月場所的妓女,出身十分卑微,麻雀變鳳凰的童話很難降臨到她身上,而導演蓋瑞·馬歇爾似乎就喜歡以此作為看點,諳熟電影宣傳之道的他并沒有將此故事落入俗套,而是訴諸更高層次的主流文化。當擁有大企業的愛德華·劉易斯向薇薇安表白時,她驚人地說出,不要因為我是妓女,就可以隨便玩弄,要么付出你真心的愛和尊重,要么我們之間僅僅是錢色交易。出自紅燈區小妞的自由平等宣言是多么薄弱,然而其震撼力不亞于馬丁·路德·金在數萬黑人面前的高聲吶喊。小妞電影當然不足以與歷史運動同日而語,然而由此審視美國主流文化的嬗變是綽綽有余的。
三、消費成為時尚
美國是消費大國,支撐其背后的消費觀念及文化一直都是社會學家們樂此不疲積極追問探討的主題。我們無意于全面闡釋美國消費觀的具體內涵和特征,只是試圖透過“小妞電影”,來窺探此主流文化在當代女性群體中的具體表現。
先說消費觀念在影片中的呈現姿態。“小妞電影”的主角是引領美國當代潮流的年輕女性群體,無論是貢獻的消費數額,還是被消費的對象,都直接代表了美國人的整體取向。幾乎所有小妞電影的女主角都是“光鮮亮麗”地出場。亮麗的背后需要衣著、化妝品、首飾、鞋包、手機及其他各種生活用品的襯托,而這些都與消費文化緊密相關。且不說擁有《27套禮服》的珍,也不必舉翻手即可攪動美國潮流的米蘭達·普雷斯麗(《穿普拉達的女王》),最能直接展現消費文化的非《一個購物狂的自白》莫屬。女主角麗貝卡收入并不高,但她為了得到自己喜愛的東西,是寧可傾家蕩產、債臺高壘的人。以東方人的觀念來看,她很容易被扣上“敗家”、不知勤儉,甚至不成熟等各種帽子,而西方人卻有著諸多信條可以說服自己和他人必須消費。如“沒有消費就沒有發展”“只要喜歡,不買可惜”“買內衣可是女人的基本權利”等等。與東方的保守性相比,從各種不同性格的小妞身上,已然能夠彰顯美國消費文化的前沿性和現代性。
再說對時尚美的追逐。如果僅僅將西方消費觀念局限在“前沿性”“現代性”等宏觀特征之下,就實在低估了驅使美國女性瘋狂購物的真正動力。就小妞電影而言,其最大的誘惑是對時尚的追逐。《穿普拉達的女王》中,米蘭達·普雷斯麗為何能夠以“女王”的身份輕易決定無數攝影師、模特的未來,數萬家服裝店、生產公司的命脈,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指標?因為她對“時尚”有著常人不可比擬的敏感和準確的把握。須反思的是,如果沒有女性消費者對她時尚審美的認同,沒有她們的“慷慨解囊”,是不可能成就米蘭達今天的地位的。在贊嘆“女王”眼力過人的同時,切不可忽視一切動力的源泉。因此,影片中小妞們的外部形象是足以反映美國主流消費文化和時尚觀念的。
四、人性美的綻放
東方人通常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化在愛情和性方面是十分奔放的。20世紀末,中國電影中談性色變。而在美國電影中,卻細致刻畫,顯得十分“濃重”。由此,很容易粗率地得出西方思想開放等結論。其實,并不是開放與否的問題,而是文化觀念的差異。美國人十分注重追求自我,不會因為某些不成文的教條式準則而違背內心的渴望。繼續深挖,放縱自我又何嘗不是另一種人性美的綻放?
第一,自我身心的放縱。盤點美國小妞電影的情節,幾乎每部都有女性為心底的欲望而奮不顧身的相關敘述。如《女人們》中克瑞斯托·艾倫寧愿背叛好友瑪麗,也要得到自己所愛;《假結婚》中瑪格麗特對權利霸占的迷戀;《風月俏佳人》里灰姑娘薇薇安與王子愛德華的結合,不可否認有機關算盡的欲擒故縱。更直接的還有《欲望都市》中凱莉、薩曼莎、夏洛特、米蘭達四位女性,已經年過半百,卻每日濃妝淡抹,既不掩飾自己對性的渴望,也確實積極地付諸行動,且毫不避諱性與愛情的沖突。理解這類小妞,是需要走進美國追求自我的主流文化當中的。小妞們對身心的放縱有系列的理論根據,近者有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學的影響,抑或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推動,乃至生命健康科學都明確提出,過度壓抑欲望只會令人更加抑郁。遠者則是清教徒文化的根深蒂固。因此,小妞電影中女性的放縱行為,反映的是美國人更健康、快樂的生活理想。
第二,人性美的綻放。將身心放縱歸于理想生活的同時,不妨再放大“愛情”元素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管是一夜情,還是性伴侶,都不可能做到“只性不愛”,哪怕是短暫的“興趣”,也存在情感的合法性。《愛情無線牽》中的艾瑪具備一切西方女性的優點,如工作認真負責,是醫院的頂梁柱;朋友之間和睦仗義,是大家公認的好伙伴;對待父母孝順有加,是鄰里鄉親嘴上的好女兒。然而,她最大的心理障礙是愛情,與此激烈沖突的又是對性的需求。當她向亞當提出“只性不愛”的要求時,觀眾自然將其歸入《欲望都市》中四位女性的范疇。須指出的是,不是艾瑪不想愛,而是怕對亞當造成無謂的傷害,其動機如此善良純真,折射出的是人性美的光環,而不只是生物本能的需要。人性美在小妞電影中隨處可見,《律政俏佳人》中艾莉為了愛情選擇自己根本不適合的法律專業;《西雅圖未眠夜》中安妮本可以和自己的未婚夫平靜生活,卻抵擋不住內心的憐憫和真正的愛情,而對遠在西部的薩姆牽腸掛肚。凡此,皆是美國小妞人性美的閃光點,推而廣之,很容易與美國愛情至上、樂于助人等普世文化相勾連。
綜上所述,小妞電影確實可以透視出美國主流文化的趨向特征,須提醒的是,引入主流文化論題不是將二者牽強附會地拉扯起來,而是為了彰顯一直以來小妞電影被忽視的深刻內涵和精神價值。這些極具典型性的小妞個案,是值得花功夫拿出來單獨考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