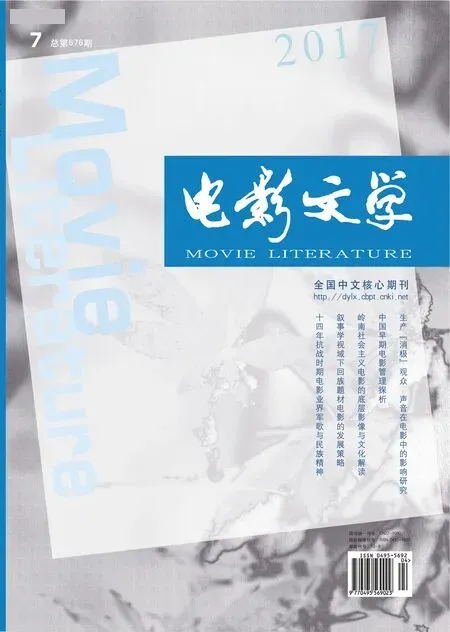朋克電影:偽現代主義下的亞文化類型
石立國
(武昌工學院外國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5)
對“朋克電影”的概念指涉與當下形態的再度考辨,這是電影藝術研究者乃至文化領域的學者亟須進行探討分析的話題,并在分析的同時,找尋電影本身各個維度中涉及的身份確認及文化價值。
一、“偽現代主義”語境下的DIY美學
“偽現代主義”語境下的DIY美學,這是決定朋克風格電影的獨特性的主要組成部分,DIY美學也被眾多電影研究界的學者看成定位于利用“朋克電影”理念的核心根據。很早就投身到“朋克電影”研究工作中的著名導演大衛·郝伯曼曾經發表過如下見解,為了呼應紐約“朋克文化”領域曾轟動一時的“無浪潮”音樂,“無浪潮”藝術工作者拍攝了許多畫質非常低劣的影像,就是人們說的“超8電影”,他們與“無浪潮”音樂人聯手向世界證明每個人都可以動手追求的美學思想。從他們眼中的DIY美學意識來說,大眾推崇的千篇一律的類型影片以及“新浪潮”主義中透露出的高姿態,只是在排他思路的影響下,將電影這一藝術形式遮掩得更加神秘并推崇出一種毫無意義的階級感。
著名電影人德里克·賈曼的作品《慶典》,畫面中對血腥暴力和性都沒有加以任何藝術處理,而是以一種DIY美學的雜陳風格直白地表現出來,因此這部影片被電影研究者與賈曼另外的作品區別對待,并將其視為英國電影界首個區別于“儀式抵抗”的解讀范式。然而,“后伯明翰”的文化研討把“DIY美學”主導下的這種獨特的文化范疇放在后現代藝術的大環境中進行論斷。本文選取了其中兩個具有代表性的觀點進行闡述:其一由戴維斯提出,朋克文化和后現代藝術風格有兩個地方具備共通性,即如何看待社群文化以及如何對其進行回收;其二由摩爾提出,朋克文化大量運用了后現代藝術的獨特手法,例如拼接、反諷性自嘲、雜陳等。假如我們將“DIY”美學的藝術思路當成朋克電影與后現代文化相關的主要特征,我們將面臨一個問題,“DIY美學”抵抗類型的特立獨行是不是會直接埋沒在后現代文化漫無邊際的風格海洋之中的,而且,朋克電影這一概念在大時代文化背景下是否還具有合法存在的“身份”?
著名文學批判理論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曾經站在解構主義的角度對后現代文化進行解讀,在資本全世界流動以及其邏輯導向下,能夠表達的思想和已表達出的思想逐漸剝離,剩下的只是一些符號堆積的毫無意義的游戲而已,這種局面就是我們所說的后現代主義。
基于此,詹明信又對“朋克文化”與后現代主義風格影片的關聯進行了分析解釋。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代表“朋克文化”的諸多特性,例如手拿攝像機拍攝、敘事結構的意識流等,以及以法國著名導演戈達爾的影片為代表的先鋒作品中的特性,例如跳脫拼接、嘲諷性暗指等,都在許多“后朋克”風格的電影中能找到被借鑒的影子,例如山姆·曼德斯的作品《美國麗人》以及達倫·阿羅諾夫斯基的作品《夢之安魂曲》等。《美國麗人》中融入了自我反指角度的第一人稱敘述、超越現實的意識流場景拼接等非主流的藝術手法,表達了在消費社會的背景下烏托邦幻夢被打碎的陰郁和傷情,這是好萊塢慣用的一種主題。而《夢之安魂曲》中對于“朋克文化”和非主流風格的滲透更為明顯,這種風格與類型片的傳統敘事架構兩者融合,打消朋克文化的另類與主流文化的間隔,朋克文化本身也成為主流文化“懷舊”的一種。
阿蘭·科比對于“朋克文化”與后現代主義的關聯發表了反對意見,他認為,現在的文化模式,用后現代主義的理論來進行界定是不恰當的,事實上,它的生產模式更靠近于“偽現代主義”的概念。時下的文化發展在后現代主義眼中已經被奇觀化,如同一個人觀看景觀一樣旁觀著,對于其本質上存在的問題卻愛莫能助,只能停留在外在的注視上。正因如此,電視熒屏和大銀幕是它們重要的媒介。而“偽現代主義”是繼后現代主義之后的一種現象,它極重視個體的行為,并將其視為文化大環境發展的重要因素。縱觀那些“偽現代主義”的影片,它們走出了旁觀的角度,也不光是對當下的“真實”提出疑問,它們完全轉換了一種全新的角度,將當下的現實用隱喻的手法設定成與影片持續互動的重要個體,即自我。比如以影片《女神布萊爾》為代表的小成本作品,它們選擇了樸素的寫實手法營造出現實記錄風格,讓觀眾產生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
假如我們將“DIY美學”放在“偽現代主義”的思想下進行分析,就很容易弄清楚“DIY美學”在抵抗類型化文化生產模式道路上的失效因素。所以,面對這樣的情形,假如我們繼續將“DIY美學”的分析重點側重在表象和風格之上,極其容易得到朋克文化被當下的文化生產所收編的結論。所以,站在具體案例形成模式的角度進行研究,以此探明時下文化生產中“DIY美學”本身形成的全新類型,并被文化大環境景觀化的形成內容,找到“新朋克電影”能夠衍生出來的條件,是一項應當被重視并努力進行鉆研的突破性話題。斯泰西·湯普森曾經發表觀點,在時下的文化生產中,“朋克電影”依舊具有其自身的“亞文化身份”,并有其抵抗類型模式的道理。只有在打破了美學與經濟學的間壁,將“朋克電影”看作一種工業生產行為之后,才能完成對真正的“DIY美學”進行分辨的任務。基于這樣的理論,湯普森將大衛·芬奇的作品《搏擊俱樂部》和影片《粗魯的男孩》進行對比研究。《搏擊俱樂部》中鮮明的“朋克文化”獲得了青少年觀眾的濃厚興趣,影片中電腦特效的利用更是令觀眾產生了身臨其境的感覺。而影片《粗魯的男孩》從美學范疇來看,其拍攝模式和制作模式都被“前景化”處理,更重要的是,影片中的“DIY美學”意味并沒有被制片方、投資方、后期團隊等方面所控制,它以獨立的形式純粹按照創作者的意圖來進行發揮,實現了“后景”與“前景”的一致。兩部影片最為本質的不同就在于,《搏擊俱樂部》依然帶有好萊塢類型影片的輪廓,而《粗魯的男孩》則完全發揮了“DIY美學”在消融了美學、經濟和工業制作等多領域界定之后的策略。湯普森的理論為“反類型DIY”在時下文化大環境中找到了合理的立足點和生存策略,并且也點明了其將要面對的全新的收編模式。
二、作為“可寫性文本”的朋克“邪典”
具有靈活性電影文本解碼的受眾美學與亞文化風格的形成關系密切且直接,在電影評論體系中的伯明翰學派解釋道:具有抵抗意識的亞文化風格是受眾群體對電影“邊緣”或“中心”文化表征的重新組合或照搬。電影中所反映的受眾美學的亞文化文本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權威評論、主流文化意識對亞文化的拉攏或叛逆化;二是亞文化抵抗者的再創作和情感認同。但是,從后伯明翰評論學派和后亞文化評論學派的接受程度來看,早期的伯明翰學派對當代電影的亞文化受眾意識進行評論時,過分強調了抵抗性編碼和亞文化風格的自然聯系,忽視了它們之間的本質區別。同時,劃分了邊緣受眾群體和主流文化的界限。所以,在當代電影的“偽現代”或者“后現代”文化趨勢下,電影評論者應該重新審視觀眾的期待視野和影片的文本結構,以期達到更符合當代電影文化及文本書寫的要求。
20世紀70年代,電影《洛基恐怖秀》的上映引起了觀眾對“儀式化”影片的討論。同時,該類電影被評論界稱為“邪典電影”,此后,“邪典電影”被正式列入類型電影的評論視界。意大利哲學家艾柯的《互文性拼貼與邪典電影》把“邪典電影”的“互文性”看作該類影片的文本特征。從此,“邪典電影”真正進入了世界電影的舞臺。時至今日,觀眾對“邪典電影”的認識還流轉在“美學的顛覆性”和“受眾的特定性”兩個研究脈絡之間。如果對比朋克電影的DIY理論或者垃圾美學范疇內的“濫用與回收”,可以看出,對于觀眾可闡釋的開放性來說,朋克電影與“邪典電影”具有相同的屬性。與其這樣說,不如說朋克電影是具有一定的“邪典性”或者被“邪典化”的亞文化影片。比如比格羅導演的《末世紀爆棚》是典型的具有“邪典”味道的朋克電影。雖然該片具有一定的商業企圖,但由于操作者對院線以及主流工業文化的把控的缺失,使得該片票房慘淡。然而,一小撮“邪典電影”的迷戀者對該片的趣味性、“朋克味”以及反烏托邦意識甚是著迷,并將之“邪典化”,使得該影片逐漸具備了朋克因素。
英國學院派電影工業理論研究者認為“朋克電影”是可寫性文本,而好萊塢主流電影則是可讀性文本。在英國工業文化背景下,該評論體系將好萊塢主流電影的運作機制看作大眾消費品,電影的風格和內容也是固定的,在某種意義上好萊塢主流電影對觀眾的主觀創造力產生了抑制作用,是典型的工業文化產品,這是與“朋克電影”的最大差異。朋克電影被定義為一種亞文化類型片或反類型片,是因為它的文本具有可寫性、開放性和召喚性。同時,那些與主流電影相抵抗的“邪典影片”逐漸被亞文化群體所改寫、介入或認同,構成一種經典“編碼—解碼”的“朋克邪典”意識,如電影《發條橙》《回收人》等。然而,在后現代文化消費環境下,伯明翰學派理論中的解碼、抵抗意識也就不再成為朋克電影的開山“風格”。當朋克電影合理融入主流工業文化后,邊緣受眾與主流的界限也就變得愈發模糊了,如影片《低俗小說》《猜火車》《逍遙騎士》等。
如上文所述,現代語境下的朋克電影是一個電影生產層面上的編碼過程,它涵蓋了文本敘事的“未來”和工業文化的“過去”。如果從“朋克電影”的文本接受方面來看,必須將“朋克風格”的“可寫性”和偽朋克電影的“復制性”區分開來,由受眾的亞文化群體來確定朋克電影是否應該獲得“邪典”的地位。從而,將對朋克電影的認知提高一個維度,認為其是電影動態發展史中的一個必然形成。這個維度必然會將被重寫或被追認的“邪典電影”引入到“朋克”風格的研究范疇之中,引領當下亞文化受眾群體和評論學派對“反類型”電影的文化意識和存在形態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三、結 語
綜上所述,正如法國著名電影評論家安德烈·巴贊所說:“如果創作者將電影理論的構建看作提出問題的普遍推演,并將這種推演視為一種文化活動,那么,在電影的創作方面我們會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電影的創作是一種對立框架的建立,它從我們耳熟能詳的特定事件出發,設立問題并進行回答。這一活動并未丟失理論的構想,是一種電影創作的中間法則。”對于朋克電影來說,《新朋克電影》評論中的空降模式具有一定的統攝性和宏觀性,是朋克風格的完美概括,該模式易于個案的地方性和動態性闡述,易于類型化理論的糅合。在當代電影評論語境下,朋克電影是該進入博物館還是將其發展為后朋克電影或新朋克電影的爭論,可能會在未來的延續中影射出更加深層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