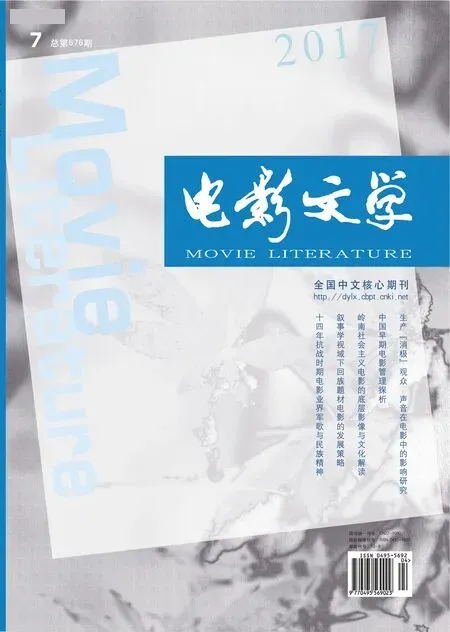約翰·吉約諾作品中的暴力美學研究
孫 偉
(法國蒙彼利埃大學電影學院RIRRA21研究院,法國 蒙彼利埃 34000)
作為法國著名的導演兼作家的雙棲藝術家,約翰·吉約諾(Jean Giono)在電影與文學兩個領域著作頗豐,聲名鵲起。作為一個一戰劫后余生的堅定的和平主義者,他通過藝術作品呈現戰爭的千姿百態。而縱觀其創作生涯,吉約諾由意識形態的和平主義者逐漸成為虛構想象層面的藝術家。
藝術通過虛構和想象,使藝術家最終實現了矛盾的對立統一。藝術創作表現出一種高度抽象總結的能力,通過這一虛構抽象化,藝術家能超越現實世界,從而構建其自有世界。因此,藝術對于吉約諾而言,既是慰藉,又是娛樂,并憑借其出色的創作和改編能力通過娛樂消遣的悲劇性需求這一主線將戰爭與藝術完美地融合。吉約諾認為戰爭作為一種娛樂消遣的方式,是終極災難。在其作品中,他意識到源于藝術的無法逃避的恐懼:要么無聊至死,要么娛樂而生,而后者又視死亡為瑰麗極致的娛樂消遣。由此可見,藝術與戰爭二者盡管有云泥之別,卻都源于娛樂消遣的必然性,并各自派生:戰爭是墮落的力量,而藝術則剛好相反,代表一種臻于完美的升華力量;戰爭代表人類惡的一面,而藝術則是善的象征。吉約諾的暴力美學原則正是利用藝術的力量徹底改變他一貫反對的戰爭及其帶來的恐懼。藝術是對戰爭這一廣泛的政治暴力的升華,是現實矛盾與藝術家自我及其人物主角所不斷追求的自由與幸福的價值取向的綜合。
本文旨在研究吉約諾作品中的戰爭恐懼,并剖析其暴力美學的特征,尤其是鮮血之美、殺戮快感。此外,吉約諾的暴力美學闡述及其風格化處理,在文學創作、電影編導領域極具借鑒意義。
一、鮮血美學
鮮血是吉約諾作品中主要的美學標的,在其作品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并將其美學價值付諸藝術創作過程。吉約諾坦言其對于鮮血美學的靈感源于一戰戰場。吉約諾不惜渲染赤裸裸的血腥場面來展現戰爭的殘酷,從而揭示生命無價,同時也凸顯了鮮血的美學價值。
吉約諾在其作品中試圖從娛樂消遣的必要性出發來詮釋鮮血的美學價值。在其筆下,寒冬中白雪茫茫象征著近乎純粹的無趣,而正是這無趣的白色凸顯了鮮血光鮮亮麗的紅色。吉約諾正是透過《百無聊賴的國王》中反面主角M.V來呈現白雪之中紅色鮮血迷人的美,而這一幕瑰麗之美卻暗含暴力消遣的必要性:這正是其為了自娛自樂而進行一系列殺戮行為的根源。無聊是犯罪的動機,亦是罪惡之源:“一切罪惡皆源于此,只因沒有比殺戮更具有快感的消遣。”[1]M.V只為自娛自樂而殺戮。在吉約諾的作品中,無聊似乎是無人能幸免的罪惡,即便是虔誠的教徒,譬如《癲狂的幸福》中的桑達·瑪麗亞(Santa-Maria delle Grazie)神父。
事實上,藝術創作對于作者本身而言亦是一種消遣過程,只不過這種消遣通過對暴力和殺戮的美學包裝,從而揭露了罪惡。這一救贖式創作給予作者極大的愉悅感,而基于暴力美學的藝術創作又使作者滿足了感官享受。吉約諾救贖性的寫作風格體現在一方面滿足了其暴力的美學快感,另一方面又不至于讓暴力持續升級。從M.V開始,作者將創作過程中的快感通過一系列角色傳遞并分享給讀者。雪中的鮮血激發了人們的美學快感,從而潛意識地代入到M.V這個反面角色之中。緊接著,貝格(Bergues)在追蹤緝捕嫌疑犯M.V時,以及朗戈羅瓦(Langlois)在審訊M.V時都為雪中鮮血的美學價值所感染。尤其作為一個正直的法官,朗戈羅瓦在意識到這一消遣的必要性無法實現時,選擇自殺來終結心中強大的邪念。小說的結局可以說也是人類悲劇的結局。這一幕悲劇性的快感升華震撼人心,曇花一現又無可奈何。狂熱的欲望促發的暴力在追逐絕對極致的快感時,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以至于只能訴諸死亡得以解脫。
自殺抑或殺戮,是經歷戰爭卻不事殺戮的吉約諾(作者)或者認定殺戮快感不可取的朗戈羅瓦(人物主角)所要面臨的選擇。作者與其人物角色各自以其獨特的方式,實現了欲望的滿足。朗戈羅瓦死后幻化于天地間,猶如作者將其欲望的升華訴諸華麗的文字中。吉約諾的藝術創作旨在開發人類的詩性源泉,象征性地通過M.V這一角色,發掘鮮血本初的美學價值。這使作者本人逐漸意識到其創作的深層次意義及藝術作品的象征性價值:“作品中心人物是M.V而非朗戈羅瓦。而人物角色的活動隱約總有作者本人的身影,猶如塞尚畫中的蘋果之于塞尚本人。”[2]可以說,M.V與朗戈羅瓦這兩個人物分別是作者吉約諾本人多面人格的化身,展現了作者想要彌補的人性罪惡面,以期在作品中追求人性的純良。
吉約諾從人物角色的暴力中發現美學價值,并將暴力的意義升華。他賦予鮮血美學一種神圣的血祭價值,以區別于基于經濟利益或政治意圖的殺戮。吉約諾認為,戰爭是通過美學世俗化使殺戮和罪惡升華為神圣的血祭。也正是血祭的升華力量當年促使眾人追隨先知阿伯拉罕與以撒到摩利山區向神獻祭。暴力美學重構了血祭的真實價值,猶如一件藝術品,通過其色彩美感與和諧感來感知其內在神韻。而作品對于作者而言,就是“血祭”的祭品。
通過暴力美學,藝術最終融合了美學的諸多創造性價值,實現了相對于現實層面更高級的抽象升華體系。美學從此成為唯一的價值標準,吉約諾正是利用鮮血賦予其作品一種形式與升華的力量。這一升華的力量本質是永恒不朽的:“生命不僅是肉體的存續,更是靈魂的不朽。”[3]藝術同時也代表著對生命的禮贊。當其臻于完美,便是克服虛空最好的方式。然而,藝術猶如那鮮血,美妍之中又暗含暴力與悲劇。
二、詩化重構
作為一種生存的必然屬性,吉約諾將暴力罪惡升華為獻祭。對于吉約諾而言,創作本身也是一種自我啟示與覺悟的過程,代表著一種更好地認識自我的嘗試,同時也是一個理解生命的過程:先是構建世界本來的樣子,然后再通過某種 “詩化重生”的作品來重構這個世界。而鮮血和暴力在此過程中則被賦予價值性、悲劇性及神圣性。
吉約諾關于暴力美學的文學創作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創作的苦痛需要借由暴力渲染來慰藉,誠如巴謝拉爾(Bachelard)所言:“久經積累的苦痛并不會無端消解,得需要釋放。創作的苦痛則須由暴力渲染來慰藉。”[4]另一方面,創作的苦痛又加深了其一直以來想要擺脫的令人絕望的戰爭恐懼。對于戰爭失望之余,他也表達了對于生命的絕望。而這種絕望一如戰爭,是我們所不能規避的宿命,只能任由其走向悲劇的深淵。
事實上,吉約諾著力刻畫人物角色的悲劇性,一則為了取悅自己,二則為了便于觀察他們最終如何從不幸的悲劇中解脫。總之,創作對于吉約諾而言是自娛自樂,通過刻畫人物來描述謀殺要比作者本人現實生活中去實現殺戮更可行,而從想象虛構的視角來描繪鮮血場景遠比從白雪茫茫的現實全景去觀察來得更容易。創作過程中,作者充當了一回罪犯的共犯,卻又無須承擔被指控的罪名。藝術在此充當了生活的替代品,真實生活中的犯禁能夠在藝術作品中得到容忍和默許。換言之,藝術作品除了充當現實審判的合法驗證外,同時為作者提供了豁免和保護。據此,對于作者而言,并不存在任何的禁忌,至少在其親手創造的世界里不受約束。無論如何,在純粹的虛構情況下,作者感到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現實所羈絆。這種自由是作者孜孜以求的結果,并力求主導事物內在感知而非事物外在形式,這也是作者創作的使命、作品的靈魂。
自此,吉約諾在其虛構的世界中隨心所欲地暢寫人類史詩般的悲劇。戰爭給他提供了素材,文學賦予他浪漫主義風格,并以鮮血這一生命的本源為契機展現暴力美學。吉約諾作品中的暴力不再只是一種趣味性、娛樂性的必然需求,更是一種美學存在,一種風格化的應用。
三、暴力風格化
暴力的風格化應用恰恰是吉約諾這個和平主義藝術家所發掘出來的。死亡的戲劇性成為暴力的一種重要的風格體現。吉約諾作品的人物名字極具隱喻性:他自述一戰中“我們是最后的幸存者,維頓和我”,其中維頓(Vidon)是他所在軍團的上尉。而維頓上尉或許就是吉約諾本人,Vidon(s)(vider的變位,意為逃離)意味著作者渴望從長久的戰爭創傷中解脫。而《百無聊賴的國王》中的M.V代表著維頓,名字的變更以一種類似于風格轉變的方式使得作者能夠切換現實,通過他的角色轉變實現不同代入。維頓上尉即朗戈羅瓦,M.V又代表著維頓,而朗戈羅瓦正是殺死M.V的人,爾后其自殺,那么經過這個過程,作者一箭雙雕地實現了兩種不同的謀殺消遣方式——刺殺和自殺,這就為我們提供了作者及其人物角色暴力風格化應用的鮮明例子。
暴力風格應用的另一個例子是關于刺殺的方式及其背后的美學動機。比如朗戈羅瓦刺殺M.V的方式是徑直走向他,在距其幾步之遙時立馬拔出手槍往其腹部連開兩槍置其于死地。其實槍擊腹部在其作品中非常普遍,比如小孩子們襲擊克羅地亞哨兵、詐降敵軍刺殺阿維耶諾(Aviernoz)將軍等,皆以此方式,而腹部恰恰又被認為是“勇氣所在的中心”,這與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中關于日本武士切腹自殺的論調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無論是使用白刃抑或火槍襲擊腹部的方式,都強化了暴力殺戮的美學原則。暴力殺戮似乎擁有一種獨特的魅力,而吉約諾本人在描述那些冷血的暴力場景時,實際上同時也分享了謀殺者的快感。
在《癲狂的幸福》中主人公昂基洛依據一路血跡去追尋殺手蹤跡的過程也被賦予了強烈的風格化暴力,尤其是吉約諾將其改編成電影時,“用一系列動作來強化期待和懸念,用雙胞胎逃跑時呼吸的急促節奏感來替代追逐者的壓迫感。類似于西部片的戲劇化懸疑感極大地強化,凸顯了畫面感和觀感”[5]。這種由期待所激發,越來越緊迫的追逐,先聲奪人,用被追逐者的逃逸動作與急促的呼吸聲來強化暴力的升級,成為吉約諾第三種暴力的風格。
作為吉約諾作品中接近完美的人物形象,昂基洛具有貴族氣息,且對于美有著執著的追求。他不但追求體態優雅,甚至對于武器的屬性也刻意區分。他認為被火槍射殺之后所流淌出來的鮮血并不如高貴的刀劍所刺而飆射出來的鮮血具有吸引力。因此,美學不僅與美麗的女性形象、優雅的姿勢以及高雅的品位相聯系,同時也與武器的屬性相關,而這武器的屬性也反映了使用者的性情:“昂基洛鐘情于刀劍,因其是最高貴完美的武器。”[6]當他在《癲狂的幸福》中使用火槍時,確切地說是為了表達對于其對手的蔑視,只因使用刀劍是一種表達敬意的機會,而其他武器則不配。
蔑視是吉約諾在意識形態層面反對政治勢力、反對政治領袖的有力武器。蔑視形同暴力,也是一種美學風格。蔑視是一種獨享的樂趣,猶如藝術對于藝術家而言。昂基洛體會到其作為埃斯雅·巴蒂(Ezzia Pardi)女公爵私生子的地位賦予他蔑視的權利,也只有蔑視才帶給他恒久以來一直追尋的升華的幸福感。他想要獨享這一樂趣,不允許任何人僭越,這正好說明了他為何狂熱又粗暴地朝那個對其流露輕蔑之情的年輕步兵腹部猛刺,并在其刺殺對手時獲得了強烈快感。當他奮力一刺時,感受到來自手腕處令人興奮的顫抖,這泄露了其無法掩蓋的感官的快感。那“一刺”同時也賦予了作者風格化的隱喻。
作品以弒兄悲劇終結:昂基洛親手殺死了其胞兄吉塞普(Giuseppe)。通過“抱住”與“直刺”等一系列動作,標志著一種完成、成功與控制的風格。一切都在這樣一種古希臘悲劇式的暴力風格中完美收官。作為始于《歡樂仍駐》,終于《百無聊賴的國王》的一系列殺戮中的最后一幕,吉賽普的死是吉約諾作品的暴力美學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