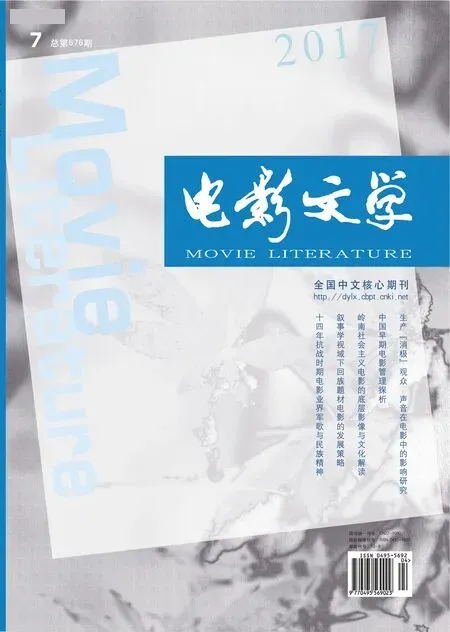論吳天明《百鳥朝鳳》的文化敘事沖突
王委艷
(信陽師范學院文學院,河南 信陽 464000)
吳天明導演遺作《百鳥朝鳳》自2014年殺青到2016年公映,其間經歷太多“磨難”,影片的遭遇與片中嗩吶的遭遇互為隱喻,展現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矛盾。吳天明對于電影猶如影片中嗩吶王焦三爺對于嗩吶的情感,他說:“嗩吶不是吹給別人聽的,是吹給自己聽的。”它詮釋了藝術家對于生命與藝術之間關系的深刻理解。2014年2月,在《百鳥朝鳳》精剪完成一個月之后,吳天明導演猝然離世,其后,影片歷經太多坎坷,勉強公映而票房慘淡,直到出品人方勵驚天一跪,情況才得以逆轉。無論是對于吳天明個人還是我們的傳統文化,《百鳥朝鳳》都可謂是一種悲壯的堅守。
一、影片中的文化敘事沖突
影片呈現了對漸行漸遠的傳統文化的思考。在當今這個時代,傳統文化式微,消費思潮盛行,這已然成為一種社會性憂慮。影片《百鳥朝鳳》為我們呈現了處在文化轉型期的中國的文化矛盾。影片通過幾個方面來呈現這種矛盾:
其一,城鄉矛盾。影片選取了吳天明熟悉的陜西黃土高原為背景,這應該是吳天明對小說《百鳥朝鳳》最大的改編之處。有學者認為吳天明以《人生》開啟中國西部片的審美方向:“《人生》這部影片把西部黃土高原上的民俗風情推向了世界,并且把西部高原大自然的雄渾之美與西部人心靈善良質樸之美融為一體,一下子就在人們的心中確立了西部影片的審美觀念。”并指出這種審美方向是“遠離政治,追求表現人性的審美內涵。人們在自然狀態下謀求個體生命本能的宣泄和釋放。作品表現出一種獨特的民族審美意識和民族面臨生存危機時的一種自發的反抗意識”[1]。
誠如斯言,影片《百鳥朝鳳》以陜西黃土高原,黃河岸邊金、木、水、火、土幾個村莊為背景,敘述了傳統文化的變遷過程。嗩吶王焦三爺作為“百鳥朝鳳”的唯一傳承人,他要做的是將他認為的“匠活”嗩吶傳下去,并且保證繼承人能夠像他一樣,不計利害、品德純正,有一股對“匠活”的堅守精神。因此,他選擇了游天鳴而非天分更高的藍玉,因為他明白,天分代表不了堅守,相對于必須用生命堅守的匠人精神,天分是可以通過后天努力來彌補的。事實上,焦三爺沒有看錯人。但焦三爺沒有看清這個時代:他堅守的事業實際上與古老中國的農耕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當農耕文明式微,工業文明、商業文明大行其道的時候,處于農耕產業的農民實際上再也難以用“躬耕+手藝”的模式來生活了。再加上現代娛樂方式的多元化,更使傳統曲藝的處境雪上加霜。事實上,焦三爺的徒弟們正是這樣逐步逃離農村走向城市的。
其二,金錢利益與道行規矩。像《變臉》中的變臉王“傳男不傳女”的手藝人行規,焦三爺對繼承人的選擇更具有普世情懷。為了把嗩吶這門“匠活”傳下去,確切地說,把“百鳥朝鳳”傳下去,焦三爺處心積慮,他一遍遍考驗游天鳴,他想尋找一位藝品和人品俱佳的、“能把嗩吶吹到骨頭縫里”的接班人。在“傳聲”儀式上,焦三爺決定把他的絕活“百鳥朝鳳”傳給游天鳴,也是看到游天鳴的藝品和人品,并把人品放在了第一位。面對洶涌的市場經濟,對行規德行操守的堅守顯得那樣奢侈與悲壯。同樣面對金錢塑造下的當今社會,焦三爺、吳天明們多少顯得有些孤單,那些過去純粹的、讓人敬畏且不會隨便表演的儀式,已經變成了當今掙錢的演出,甚至一個偏遠的少數民族山村也難以幸免。那些令我們敬畏的信仰,正在和曾經攜帶這些信仰的文化形式嚴重分離,正像焦三爺的嗩吶那樣,面對金錢利益,道行規矩還剩下多少呢?
其三,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矛盾。在慶壽的時候,游家班遭遇洋樂隊,景象慘淡。傳統嗩吶在洋樂隊的沖擊下生存艱難,各個村上的紅白喜事不再請游天鳴他們去吹嗩吶,就連村頭的聾子死后也請洋樂隊而不請游家班的嗩吶了。洋樂隊只不過是現代文化的代表,中國社會在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信息化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有太多淺層次的現代文化泡沫被大規模復制,而其內在的精神內涵卻并沒有隨之建立,空洞的能指符號支撐起一種虛幻的繁榮,而傳統文化在這種沖擊中式微并逐漸退出,隨之退出的還有優秀的精神遺產。
綜上所述,影片中為我們呈現了傳統與現代兩種文化的沖突。它實際上是傳統農業文明以及建立其上的價值規范,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正變得脆弱不堪。堅守傳統文化及附著其上的精神價值,成了一種悲壯的行為。曾有論者不無樂觀地指出:“中國文明建立在農村人口一貫壓倒城市人口的基本社會建構上……但是,當今天這個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們無法辨認農業社會的本來面目的時候,卻不能不相信,中國的文明和文化真的到了脫胎換骨、浴火重生的時候。”[2]但這個“脫胎換骨、浴火重生”的過程注定是一個痛苦的掙扎過程,一方面是傳統價值觀的喪失,一方面是新的價值觀并沒有隨之建立。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維護優秀的傳統文化,堅守優秀的傳統價值,才是《百鳥朝鳳》的核心所在。
二、道德沖突與中華禮樂文化
中華禮樂文化源遠流長,幾千年不曾中斷。禮樂文化倡導和諧,《禮記·樂記》中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這里強調了禮、樂之間的關系,即和諧和秩序必須統一才能達到禮樂相濟,社會才能安定,人民才能樂業。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孔子把仁作為禮樂的基礎,恢復禮樂首先要使人“仁”。因此,修身是一切根本。事實上,當前的中國社會,建立在工業文明基礎上的資本價值成為判斷一切的標準,這種工業之“技”我們已經非常成功地植入了我們這個傳統的農耕文明之中,但我們并沒有隨之建立起工業文明契約精神之“道”,價值失范帶來的惡果正一遍遍在我們這個社會上演。這種沖擊表現在多方面、深層次,已經嚴重動搖了我們傳統文化的根基。《百鳥朝鳳》為我們呈現了多重的道德沖突。影片中的有些道德沖突是圍繞禮樂文化展開的。
首先是師徒矛盾。傳統民間藝人的師徒關系是一種倫理關系,維持這種關系的是傳統的道德規范與行業規范,而非契約。因此,當經濟價值作為衡量一切的價值規范的時候,實際上這種靠道德倫理維持的師徒關系就變得十分不穩定,影片中就為我們呈現了這種狀況。比如焦三爺怒扇二師兄。吳天明非常清醒地揭示了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民間藝術傳承方式的道德危機。此外,這是工業文明、市場經濟對農耕文明的碾軋,使建構其上的精神價值正一步步走向消亡。“在社會現代化的巨大變革中經濟價值成為衡量一切東西的根本標準,曾在鄉村社會中占據統治性地位的傳統禮儀和倫理秩序在現代化的沖擊之下失去了此前的規范作用和崇高地位,隨著‘禮崩’而來的必然是‘樂壞’。”[3]
其次,行業規矩遭到破壞。游天鳴為兒時的同學——木村的長生結婚吹奏,但他并沒有享受到接師禮。游天鳴和焦三爺對行規遭到破壞耿耿于懷,師父焦三爺連聲說:“沒規矩了,沒規矩了。”傳統的禮節正在隨著社會的變遷而成為一種被認為無足輕重的存在。禮崩會產生樂壞的結果。以往,嗩吶藝人為送葬吹奏,孝子賢孫跪倒一大片,那不是對藝人的敬畏,而是對禮樂的敬畏。
最后,“百鳥朝鳳”的道德內涵。“百鳥朝鳳”作為嗩吶名曲,本來是一種歡快的曲子,在影片中被吳天明改為大悲的曲子,即是為了烘托曲子的嚴肅莊重,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改動使該曲子蘊含了更為豐富的精神內涵。不但德高望重的人才配享此曲,而且只有德藝雙馨的人才能夠繼承此曲。因此,當焦三爺說自己死后四臺嗩吶足矣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對傳統文化堅守的民間藝術家謙遜的美德和對中華禮樂文化精髓的理解。
綜上所述,中華禮樂文化其核心價值在于人的修為,“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圣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禮記·禮運》)。這種把禮義放在人生價值之首的傳統禮樂文化與當今的資本價值下的金錢評價機制水火不容,禮樂文化失落源于這種根本性矛盾,而表現在日常行為方面則是道德沖突與價值失范。
三、票房與藝術:《百鳥朝鳳》的悲壯選擇
本文開頭說過,《百鳥朝鳳》作為吳天明導演的遺作,已經將自己對電影藝術的堅守融入了影片對焦三爺形象的塑造之中。在當今電影市場以明星、金錢、炒作等為基礎,以奪取票房為目的的大環境下,對藝術的追求似乎變得無足輕重。吳天明說,他選演員不是選擇最貴的,而是選擇“對的”。為票房還是為藝術一直是電影導演最頭疼的選擇,這種選擇隨著電影由賣方市場到買方市場的轉變變得越來越現實。且追逐利益已經成為電影的主流。因此,導演不得不花費大量資金用于選擇明星演員。明星演員的片酬如今已經成為天文數字。有的電影直接靠明星支撐,在藝術性、敘述技巧方面則談不上有所作為;有的則用蹩腳的敘述去講一個“明星故事”。電影界已經變得浮躁不堪。
影片《百鳥朝鳳》充滿了懷舊情結,這些懷舊情結是通過以下幾個方面表現的:
首先是男耕女織的生活方式。我們注意到電影開頭設定了1982年,20世紀80年代初是一個處于現代與前現代臨界點的年代,農村傳統的生活方式還沒有被破壞,建立在傳統農耕文化基礎上的價值觀念也是當時農村社會的主流。影片給我們呈現了黃土高原鄉野之美。農民在田里勞作,沒有機械化等現代生產工具,閑適、充滿田園溫馨。師父和師娘每天做得最多的就是下地勞作。影片對師娘表現最多的是她的紡線與織布,這使影片充滿了對傳統男耕女織生活的某種詩意表達。
其次,農民對手藝(技藝)的敬仰。游天鳴之所以被父親送到焦三爺那里學習嗩吶,主要原因是他父親小時候想學嗩吶但沒有師父收他,他要在兒子身上圓這個夢。殘酷的饑餓記憶在中國農民心里形成一種潛在的意識:災荒餓不死手藝人。這些藝人在長期的演藝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的行規和傳承規則。《百鳥朝鳳》通過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人們價值觀念的極速變革,呈現這些民間技藝在農民心中的位置逐漸滑落的過程。
最后,淳樸簡單的學藝過程。影片表現了焦三爺收徒的“考試”過程,如從瓢中吸水、吹雞毛、口中吸水吹木板等,這些考試簡單有效、充滿樂趣。尤其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焦三爺帶著兩個徒弟到蘆葦、野花、野草叢中靜聽鳥語,師徒模仿鳥叫,相互唱和。這是影片充滿詩情畫意的一筆。吳天明通過這種方式表達了對傳統文化式微、對當今不良社會生活方式的憂慮。一個有追求的電影人的擔當精神通過純凈的電影語言表達了出來。
上述這些充滿懷舊情緒的電影鏡頭,是通過樸實的敘述方式表達的,吳天明在電影中并沒有在敘述上耍各種花樣,而是以傳統的線性敘述呈現故事的發展脈絡。吳天明通過簡單的敘述和電影鏡頭來對抗現代化的電腦制作,用充滿濃烈情感的藝術追求來詮釋他終身堅守的藝術原則。在票房與藝術中,他毅然選擇后者。吳天明說:“過去我拍農村片,現在拍城市題材,其實都是一根筋,那就是對國家民族前途和命運的一種關注,就是所謂憂國憂民的情懷。”[4]吳天明導演的“一根筋”表現在《百鳥朝鳳》中,是否可以解讀為對電影藝術傳統價值的一種堅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