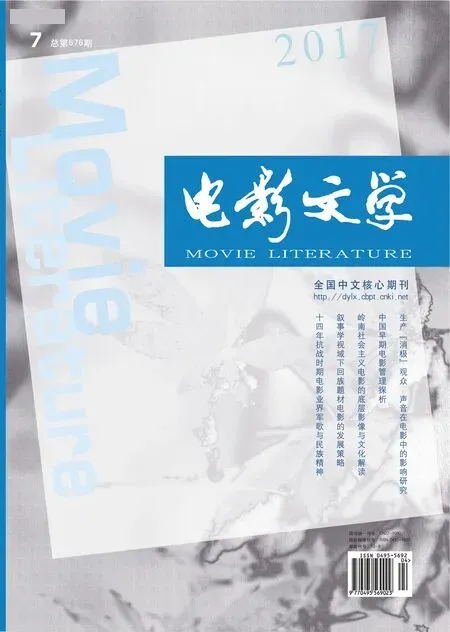電影《紐約紐約》文化中的藝術美學
張 放
(廣西建設職業技術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7)
如果將電影與文化相互剝離,那么電影無疑成了無本之木,失去了創作的靈魂。文化是電影創作的根基,透過一部電影能夠看到創作者所處時代的精神面貌與文化環境,以及創作者對于文化的理解與觀點。同時代的電影都有相似的文化理想訴求,最終匯聚成集體的聲音時常反作用于文化。因此,將文化納入電影研究與電影批評有著先在的必要性,同時從電影的角度出發去解讀文化,也是一次頗具意義的審美活動。電影《紐約紐約》是以20世紀90年代上海“出國熱”為背景的愛情片,深刻反思了“出國熱”對人們精神和思想的扭曲,以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對中國的“文化侵略”。片中人物的情感聯系、人生選擇、生存狀態等,無一不與變革中的社會文化息息相關,所有的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被卷入這場聲勢浩大的時代大潮之中,順勢而為地成為時代文化的建構者。這種從歷史與文化中汲取靈感、創造電影美學的過程具有深入研究的價值。
一、歷史文化的審美基礎
時代變革與社會發展始終是電影創作的素材和靈感之源,在電影語言的豐富表現力之下,創作者透過大銀幕向觀眾表述著自己對于這個時代社會的理解和見解。在反觀與審視歷史的過程中,歷史文化逐漸在電影藝術的表現之中呈現出美學韻味與審美價值,導演如何創作關于歷史文化的電影,觀眾又用怎樣的審美價值觀去欣賞,這個過程也正是歷史文化美學建構的全過程。
人無法脫離社會文化的大環境生存,透過電影鏡頭觀察人,首先要觀察人所處的時代、社會、文化背景,然后才能看到人在環境當中表現出的人性的深層一面。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的天翻地覆的變化以及時代的變革對人性的廣泛影響,是中國第六代導演作品集體關注的共同點。第六代導演關注改革開放中的中國社會是源自他們自身的成長歷程,從個人歷史中提取經驗,進而衍生出對有著相似或共同經歷的群體的人文關注。如賈樟柯始終關注著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的點滴變化,從城市風貌到大眾思想,尤其是現代化進程推進過程對偏遠地區的影響,在他的電影中都成為反映時代流變的鏡子。
電影《紐約紐約》表現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人對西方世界、西方文化趨之若鶩的集體狀態,人們對美國代表的西方社會的向往、對美國文化代表的西方文化的熱愛,都表現出集體對本民族文化的背叛以及對西方文化的主動接受與融入的愿望。這種隨著改革開放而爆發的“出國熱潮”尤其以上海為代表,在當時已經形成了一種文化現象。
同樣是表現改革開放對中國社會帶來的顛覆性影響,導演羅東卻從另外一個文化角度,去表現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影響。最年輕的五星級酒店領班路途,一心想去紐約實現“美國夢”的女孩阿娟,初出茅廬、涉足酒店服務業的阿坤,從美國歸來的精明的成功商人米先生,所有人的命運都因洶涌澎湃的出國熱潮而關聯在一起。眾人的工作、生活和情感,都因涌動在上海灘的“出國潮”而產生了某種共性,無論是對美國不屑一顧的路途,抑或是為了去美國不惜一切代價的阿娟,他們的人生都與這段歷史文化緊緊地拴在一起,無法掙脫。因此,片中描繪的所有人的情感軌跡都深深地烙印著這段歷史文化的印記,無法脫離歷史去看待。
二、集體記憶的審美意識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出國潮”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衍生品”,為了加快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改革開放打開了中國的經濟大門,也為西方文化“侵入”中國敞開了大門。當時的人們對外國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美好幻想,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和價值觀迅速地侵蝕了人們的頭腦,讓封閉已久的中國人相信出國就意味著擁有了美好生活,擁有一張美國簽證就是擁有了一把通向完美的幸福生活的鑰匙。這場出國熱潮尤其在前沿都市上海席卷得尤為猛烈,幾乎每個生活在上海的人都對出國心心念念,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也是如何能夠出國。出國熱潮來得如此快速而猛烈,瞬間成為當時“上海人”的集體記憶,也是當時想出國的中國人的共同記憶。
電影《紐約紐約》將這些被卷入“出國潮”中的“上海人”的集體記憶用影像化的方式呈現出來,用懷舊美學的思想還原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空間。影片當中,面對西方世界為中國人敞開的大門,大部分人都想借此機會改變自己的生活,當時的人們對于西方世界的想象、對西方文化的熱愛、對西方生活的憧憬等,都具有普遍的、相似的想象范式。
片中杜鵑飾演的阿娟是一個上海女孩,面對大上海的紙醉金迷,阿娟的家庭卻支離破碎、窮困潦倒。母親從小對她灌輸長大要找個有錢男人的思想,而母親自己卻始終逃脫不開被男人玩弄和拋棄的命運,只能將“咸魚翻身”的全部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女兒阿娟身上。阿娟面對破敗不堪的家和自怨自艾、勢利的母親,也逐漸成長為一名徹底的物質女孩——只相信金錢和權勢。同時,當這場席卷上海灘的“出國風潮”在阿娟面前經過時,她將出國看作自己擺脫失敗的母親、破舊的家庭的唯一出路,也是改變自己命運的唯一出路。于是,她想盡一切辦法去接近能夠為她提供出國機會的人,直到有一天她遇見了路途,路途成為她去美國的“救命稻草”。阿娟不惜犧牲自己的色相勾引路途,用自己年輕的肉體交換路途對自己的信任,雖然自己對路途同樣動了心,卻在不斷被拋棄的母親的陰影下不敢付出自己的真感情,她只相信:唯有自己出國,災難一般的生活才能結束,新生活才能真正開始。而路途作為一個小小的五星級酒店領班,能給予她的只是去美國的一張簽證而已,無法給她真正的生活。
阿娟作為當年上海“出國潮”中的一員,代表了千千萬萬企圖利用出國來改變自身命運的青年男女,他們對新文化、新思想的接受度和包容度都要遠遠高于老一輩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在他們的眼中就是遍地黃金的烏托邦。阿娟最終背叛了路途,跟隨米先生來到渴望已久的美國紐約,她卻依然無法依靠自己的雙手和實力在美國生存,依舊逃離不了母親希望她找個有錢有勢的男人的宿命。阿娟“美國夢”的實現是有著銅臭味和宿命論色彩的。因此,雖然阿娟的個人經歷具有個人色彩和特殊性,但是阿娟對出國的渴望和憧憬卻是一種源自集體的共同記憶,具有普遍的審美意識。
阿娟、托馬斯等人雖然成功辦下了去美國的簽證,成功踏足這片土地,他們看似是“人中龍鳳”、成功者,但實際上是徹底的失敗者。阿娟雖然身在美國,卻重復著與上海的母親相似的生命軌跡。當初在“紐約紐約”酒吧舉辦歡送派對、風風光光出國去紐約的托馬斯,多年后與路途在美國重逢時,卻在紐約做著最低等次的工作,比在國內時更加窮困潦倒。阿娟和托馬斯是這場“出國潮”和文化變遷過程中的成功者,也是犧牲者,他們匆匆忙忙地踏上了去紐約的輪船,卻沒有一技之長能夠在紐約成功掘金,他們關于“美國夢”成就又破碎的體驗和記憶依然具有集體記憶的共性,讓諸多有著共同出國經驗的人都能產生共鳴,也滿足了想象“出國”的觀眾的心理期待。
三、懷舊意識下的美學表達
導演羅冬和張藝謀一樣是攝影師出身,拍攝電影《紐約紐約》初次轉型成為導演,也與張藝謀的導演處女作一樣,有著攝影師的身份印記和風格特色。《紐約紐約》極度強調電影的鏡頭語言,尤其強調利用光影畫面營造情緒氛圍,多數時候都是通過鏡頭和畫面達到敘事目的。導演羅冬在《紐約紐約》當中構建了一個充滿懷舊韻味的、色彩飽滿的影像空間,最大限度地還原了20世紀90年代的上海灘和紐約。
主導《紐約紐約》美學空間構建的核心依然是文化,是對文化的懷舊意識,以及透過20世紀90年代的文化內容提煉的美學意識。片中的上海和紐約,分別指代了中國和美國,一個代表中國文化,一個代表西方文化。上海和紐約具有十分鮮明的共性:在城市建筑風格上,上海的建筑很多都是殖民地風格,隨處可見的異域風情時刻表明了自己多元文化融合的身份特征;美國雖然摩天大樓林立,但是昏暗的燈光照射的街道卻時常顯示出與上海共同的都市氣質。在文化層面上,同樣作為一線國際化大都會,身處其中的人們對金錢和權力的欲望都難免會膨脹、放大,無論是上海還是紐約,都是一個紙醉金迷的、容易讓人迷失的物質社會。因此,觀眾看到片中的上海和紐約時常表現出共同的環境特征和情緒氛圍。
為了凸顯上海和紐約兩座城市的共同特征,導演羅冬在表現兩座城市的景觀時,刻意將白天的場景用冷色調展現,而夜間場景如霓虹燈的光線效應用暖色調呈現。尤其是影片利用大量的夜戲,來表現上海這座城市的紙醉金迷,甚至夜晚的上海要比美國紐約更給人以國際大都市的現代感,紐約夜晚的街道雖然也閃爍著五顏六色的霓虹燈,但相對于上海而言有些清冷和孤寂。
在羅冬的電影鏡頭中,光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元素。光在羅冬的鏡頭語言中是塑造人物形象的工具,也是營造情緒氛圍的工具,同時也是打造文化空間的重要元素。街道、酒吧、房間內,都充滿了暖色調的燈光,酒吧里閃爍著的粉色光線的臺燈,街道上閃爍的五顏六色的霓虹燈牌匾,在夜間場景的每一個鏡頭中,都會出現霓虹燈的影子。無論是直接將霓虹燈閃爍的光線納入畫面鏡頭中,還是將鏡頭對焦于前景人物,將霓虹燈虛化為背景的一抹光暈,還是利用鏡面反射的霓虹燈光線收入鏡頭畫面當中,閃爍的霓虹燈正是羅冬認為的蠢蠢欲動的欲望的象征,夜上海隨處可見的閃爍的霓虹燈,也正是象征著人們涌動的欲望,對金錢、肉體、權力等的欲望在整個城市中涌動。上海城市空間中四處涌動的欲望,大背景是風云突變的轉變中的大時代背景,這也是上海獨特的文化氛圍,在導演羅冬的鏡頭當中呈現出了別樣的關于欲望的美學表現,也產生了懷舊美學的審美價值。
四、結 語
電影《紐約紐約》是導演羅冬的處女作,大眾對于該片的評價過于嚴苛和片面。導演羅冬從文化著手,通過展現20世紀90年代的上海“出國潮”,來表現新舊文化、東西方文化的猛烈沖擊和融合,借以比對當今文化全球化的文化融合狀態。影片中的阿娟、托馬斯以及為了獲得美國簽證不惜傾家蕩產的人們,都表現出一種對于西方文化的極大的信任和狂熱,甚至盲目地對西方社會產生了無限放大的憧憬,這種集體性質的行為特征和思想特征顯示出對于西方文化的主動接觸和接受,這種主動接受的文化心理也適用于今天中國人的集體心態,幾十年之后依舊具有文化審美價值和反思價值。導演羅冬的這種基于文化生成的美學創造極具審美價值,也正是電影《紐約紐約》的成功之處。只不過導演更傾向于利用鏡頭和畫面敘事,很多表述的內容都蘊含在了鏡頭語言當中,這與觀眾對商業電影的審美范式是相悖的,傾向于藝術電影的表達方式勢必會遭到市場和觀眾的冷落,但這也正是影片做出的頗具理論價值和審美價值的藝術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