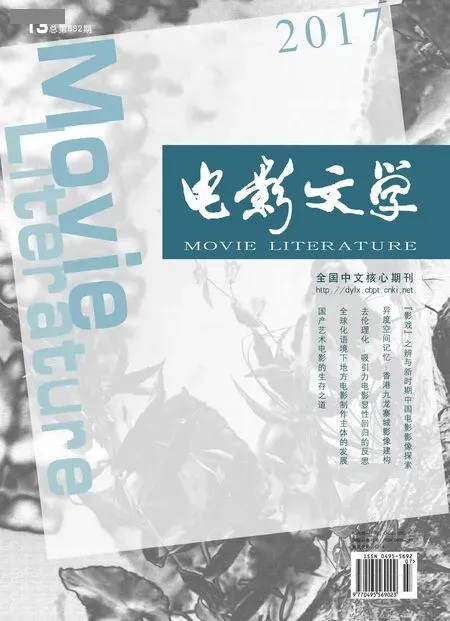“影戲”之辨與新時期中國電影影像探索
張燕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學,陜西 西安 710055)
在新時期(1979—1989)電影理論思潮中,“影戲論”是基于中國電影史而進行的一次關于電影本體問題的探討。中國電影發(fā)展之初被稱為“影戲”,在“影戲論”的語境里,“影”(影像)是電影本體元素,是電影獨有的,而“戲”(敘事)則是電影與小說戲劇等敘事藝術共有的,并非電影的本體屬性。
鐘大豐在《論“影戲”》一文中提出“‘影戲’是中國電影的濫觴。‘影戲’是一個由‘戲’和‘影’兩種因素組成的矛盾統(tǒng)一體”①。“影”和“戲”分別代表電影的手段和目的、形式和內容、電影本體及其外部功能,在電影發(fā)展歷程中時常表現(xiàn)為一種此消彼長的二元關系。通常,電影思潮的活躍期也是電影影像本體探索的活躍期,如,20世紀20年代的歐洲先鋒派電影運動中的純電影和詩電影探索,40年代末的意大利新現(xiàn)實主義電影,50年代末的歐洲新浪潮電影,在電影觀念上都曾不同程度地表現(xiàn)出敘事的弱化和對影像本體的強調。相反,相對保守的商業(yè)電影體系,電影影像探索更容易按部就班,譬如在美國好萊塢電影歷程中,幾乎沒有出現(xiàn)長時段的影像實驗期,其完善的電影生產體系和市場機制培育了一套關于電影敘事與影像關系的保守模式。在中國電影發(fā)展進程中,新時期是一個電影思潮的活躍期,“去戲劇化”的電影理念,使中國電影影像創(chuàng)作在新時期電影實踐中直接或間接受益,不斷獲得外部形式的豐富、表意功能的增強以及對于影像真實的深入探索。但在“影戲論”的辨爭中作為電影本體的“影像”與作為電影功能的“敘事”這兩個維度被不恰當?shù)貙α⑵饋恚袊娪坝跋駭⑹卵芯康娜趸苍诒藭r埋下了隱憂。
一、弱化敘事,以本體的名義——本體論語境下的電影影像形式探索
始于新時期之初的電影影像形式探索,源于中國電影本體意識的覺醒。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國電影創(chuàng)新思潮首先以“電影語言現(xiàn)代化”“電影和戲劇離婚”“電影應該是電影”等關于電影性與戲劇性關系問題的探討拉開帷幕。白景晟發(fā)表在1979年第1期《電影藝術參考資料》上的文章《丟掉戲劇的拐杖》,首先對電影的戲劇性傳統(tǒng)提出質疑,認為“戲劇”或“戲劇化傾向”是當時中國電影的主要癥結;同年2月,謝鐵驪在答《電影創(chuàng)作》記者問時談及“電影創(chuàng)作中舞臺劇的習慣勢力巨大”;6月,《電影藝術》發(fā)表張暖忻、李陀的《談電影語言的現(xiàn)代》,文中用“裝在鐵盒子里的舞臺劇”形容時下中國電影存在的問題,提出從形式上向世界電影學習、實現(xiàn)電影語言現(xiàn)代化的課題;次年3月,電影理論家鐘惦棐先生在會議書面發(fā)言中提出“電影和戲劇離婚”,理由是“任何藝術形式, 只有當它足以和鄰近的形式相區(qū)別的時候, 它的造型運動才算告一段落”。這些討論的共同觀點是:反對戲劇性,強調電影本體形式探索。盡管隨之而來的探討中有理論家從學理和邏輯上對“戲劇化”與“舞臺化”、“戲劇化”與“虛假性”、“現(xiàn)代化”與“現(xiàn)代性”等問題進行過論證和糾偏,如邵牧君的《現(xiàn)代化與現(xiàn)代派》、譚霈生的《舞臺化與戲劇性——探討電影與戲劇的同異性》、余倩的《電影應當反映社會矛盾——關于戲劇沖突與電影語》等,但多數(shù)電影人還是本能地以更大的興趣接受了“電影應該是電影”這一強調電影藝術本體性和純粹性的觀點。其中原因可以想見,當時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中國電影創(chuàng)作急于掙脫一切固有思想和藝術成規(guī),走向了電影的本體探索和形式創(chuàng)新,尋求電影區(qū)別于其他敘事藝術的戲劇(舞臺劇)文學(經典小說)獨特之處,特別是影像形式上的獨特之處。電影的本體論爭使得電影創(chuàng)作和電影批評逐漸擺脫了原有單維度的意識形態(tài)批評,于影像創(chuàng)作上給予更多關注。電影創(chuàng)新,很大程度上被歸結為影像創(chuàng)新,影像被認為是電影彰顯其獨特性的最重要元素,是其他藝術所沒有的,是電影獨有的。
造型意識的覺醒是新時期之初電影創(chuàng)作的標識性變化。最初的形式探索表現(xiàn)為一種形式的狂歡,電影創(chuàng)作者挖空心思以實現(xiàn)影像形式的標新立異,以至于有導演感嘆“最近電影界‘創(chuàng)新’‘探索’的意義好像被慢動作、定格、時空跳躍等技巧所替代”②。這種狂歡式的形式探索多少有些炫技雜耍的意味,如《小花》《苦惱人的笑》等打破常規(guī)、利用過期膠片、鏡頭進光、單色調處理等制造視覺效果上的意外和不同,雖有創(chuàng)新但相對淺表,也十分短暫。反思期很快到來,比如關于形式與內容、真實與唯美、形式的內斂與外顯等二元關系的思辨,后續(xù)電影中關于造型的探索始終持續(xù),隨后的階段造型形式探索融入電影現(xiàn)代性探索,比如第五代電影實際是沿襲并強化了電影本體探索期的形式意識,《一個和八個》《黃土地》《紅高粱》等以對造型形象的象征和表現(xiàn)性挖掘,充分顯示了造型的力量,并以此完成了中國電影第五代的代際標識。
新時期由電影本體思考所引發(fā)的這段形式探索的另一個重要價值,在于關于電影獨有表現(xiàn)形式的探索,以及將藝術形式先于內容進行設計的創(chuàng)作思維。例如,吳貽弓導演在《城南舊事》導演闡述中,探討了影片敘事視點的問題,影片選擇主人公英子主觀視點的敘事,“最初只是在原作基礎上的一種形式選擇,但發(fā)現(xiàn)這一形式選擇能夠將人物和事件統(tǒng)一起來,創(chuàng)作者才發(fā)現(xiàn)形式實實在在地成了內容的一部分”。黃健中導演也探討過意識流手法作為形式給電影影像創(chuàng)作帶來的變化,認為“意識流影片不注重故事, 而注重含意,是因為生活中的許多哲理通過視覺和聽覺的形象來反映比通過一個故事更直截了當、更生動一些”。一般而言,電影創(chuàng)作的出發(fā)點大約有三種情況:從思想出發(fā)、從故事出發(fā)和從形式出發(fā)。③這提出了從形式出發(fā)思考創(chuàng)作問題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新時期的電影創(chuàng)作探索了這種思維的可行性與合理性,只可惜這樣的探索止步于初期階段,而轉向了象征性與符號化的形式探索。所以進入商業(yè)大片時代,形式探索仍然與炫技等同起來,至今,中國電影影像在形式維度上仍然缺少一種可以品味和把玩的形式感,一種與內容(敘事和表意)相互依附又獨立于內容之外的形式魅力。
二、弱化敘事,以真實的名義——紀實主義思潮中的中國電影影像寫實探索
在對西方電影理論的譯介和學習中,克拉考爾和巴贊紀實主義電影理論在中國被放大和抬高。這使得中國電影攝影及時跟上了世界電影攝影紀實主義美學探索期,長鏡頭、自然光效、低照度等以寫實主義為核心的攝影觀念與技巧,進入中國電影攝影創(chuàng)作視野。
真實,是新時期十年創(chuàng)作闡述中出現(xiàn)頻度最高的詞匯。背景有二,一方面是“文革”之后,中國文藝反對虛假追求真實的藝術訴求,另外,西方寫實主義電影理論的全面引入和傳播,特別是巴贊關于電影攝影影像本體論的闡釋,將紀錄性提升為電影的本體屬性。這一時期,中國電影思潮中的影戲之辨表現(xiàn)為電影真實性與戲劇性之辨,以及電影生活流和戲劇流的分野。敘事性的弱化,客觀上導致了影像的凸顯。這一時期的《沙歐》《青春祭》《鄰居》《野山》等成為中國紀實主義電影攝影的優(yōu)秀作品,影像真實探索從觀念的更新、技術的進步,最終走向美學的成熟。
自然光效和戲劇光效概念的提出和理論總結,是新時期電影攝影探索對于寫實主義電影思潮的積極呼應。電影攝影師鮑蕭然在《探求攝影藝術的自然光效》一文中首次用“戲劇光效”概括經典好萊塢電影照明的觀念與技巧,并將其與寫實主義的“自然光效”照明理念加以區(qū)分。戲劇光效是對經典好萊塢時期因電影的商業(yè)性和明星制的需要發(fā)展起來的一整套照明體系的總結。戲劇光效的主要特點是假定性和風格化。為了獲得立體感和美化畫面。除了注重五種光效的匹配、直射主光的類型以及所謂交叉反測光的模式伴隨人臉左右轉動, 交替互為逆光和反側光外,還要用花哨的逆光勾勒輪廓, 美化人物, 修飾畫面, 用類型光彌補臉型缺陷, 用投影完成構圖等。至于這些光效是從生活環(huán)境中哪里來的, 則不深究。戲劇光效強調光的戲劇表現(xiàn)力,忽視光線的自然規(guī)律;按照戲劇內容的要求以及人物內心活動運用光線,常用腳光、頂光、局部照明以及各種效果光來處理人物形象,來烘托氣氛、增強戲劇效果或刻畫人物的心理狀態(tài)。而自然光效追求光線的真實感,具體表現(xiàn)為:(1)光質上,追求與人們日常生活狀態(tài)的光線質感的接近,散射光和漫反射光,強調光源的單純性,盡量采用現(xiàn)場的固有光及自然光,少用人工光;(2)光強度方面,追求日常生活常態(tài)光線照度,即低于100LUX的低照度光域;(3)光源設計(畫面光源及光源方向)方面,強調畫面光源的合理依據(jù),不主張使用假定性光源,反對“五光”俱全,少用輔助光,不用修飾光。自然光效,引發(fā)了攝影照明上的一系列探索性實驗,如,《大橋下面》《野山》《青春祭》的探索都深入到低照度光域,生活中的室內散光, 一旦太亮, 就會完全吃掉那種柔和的自然感,接近生活常態(tài)的低照度光線才能表現(xiàn)出常態(tài)生活的自然情趣和質樸美感。
寫實主義電影思潮對電影敘事性的弱化具體表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題材和故事選擇上對敘事性的明顯弱化,二是電影敘事手法和影像形式上的反戲劇性。電影《野山》就是后者,用鮮明的紀實風格影像將影片內在的戲劇性包裝成生活流的模樣,使電影看上去自然真實但又極具張力。《野山》的攝影師米家慶贏得了當年的中國電影攝影師學會獎。米家慶的《野山拍攝散記》一文開頭引用巴贊的話作為題記,《攝影造型不是畫》對“用光作畫”的攝影觀念提出了質疑和反思,在《野山》的探索中真實影像原則是用一系列“不”字建構的,“不用那些可以使觀眾察覺的攝影技巧,包括不用變焦距鏡頭、特寫鏡頭、不正常的大俯大仰視點等”“放棄繪畫性的完整構圖”“放棄‘用光作畫’的造型觀念,不拍‘美人照’,不拍‘風光照’”“少用光和不用光”“基本只處理環(huán)境光,不加人物光”④。使用常規(guī)視角、標準焦距、常見景別、自然光效、固定機位、長鏡頭等拍攝手法。強調了真實,弱化了形式,將技術技巧和造型降至最低限度。
藝術的審美始終是在逼真化和陌生化的二元關系中尋找均衡。新時期攝影探索中有極致的自然主義寫實派,也有所謂繪畫派和唯美派,但傳統(tǒng)意義上的戲劇光效和相應的攝影手法被摒棄或改進了。崇尚生活流的作品中,敘事維度被理所當然地淡化了。
三、弱化敘事,以表意的名義——現(xiàn)代性辨爭中的中國電影影像表意探索
1984 至1988年,中國“影協(xié)”舉辦數(shù)屆國際電影講習班,尼克· 布朗將電影符號學、精神分析學、意識形態(tài)批評、解釋學、敘事學等西方學院派電影理論帶入中國電影語話體系,此后,這些理論經由學術刊物及各種研討活動廣泛傳播。在此期間,中國電影史學研究者基于對中國早期電影的淵源研究提出“影戲”論,但這場因中國電影的影戲傳統(tǒng)之名進行的討論,并非為電影的敘事性尋找原初依據(jù)。在當時的大背景下,影戲說本身卻攜帶了對影戲模式的否定意味。這一點,影戲論提出者鐘大豐在若干年后發(fā)表的《是否有重談“影戲”的必要》一文中有清晰描述:“從理論思想的淵源上,‘影戲理論’說的提出,是20世紀80年代初電影創(chuàng)新運動以非戲劇化為武器否定‘文革’電影經驗理論的產物。因此在歷史描述的措辭和理論的價值取向上都帶有明顯的否定性傾向。”⑤影戲論,實際是再度推進電影的非戲劇性特質。隨后的1986年,因青年學者朱大可的《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一文引發(fā)的“謝晉模式”大討論,電影的現(xiàn)代主義和精英主義實際勝出,影像的隱喻和象征意義變得重要和凸顯,與80年代之初的形式探索形成接續(xù)關系,又與第五代的反思意識和批判精神不謀而合。但其中明顯的精英文化意識和現(xiàn)代性思潮,再一次讓中國電影偏離了敘事傳統(tǒng)。
影戲論和謝晉模式大討論,現(xiàn)代主義電影思潮蓋過經典電影傳統(tǒng),影像再次因現(xiàn)代性之名被強化,影像的象征性符號化運用受到鼓勵和推崇,影像的表意探索超越敘事成為時尚。今天再翻閱《黃土地》⑥《黑炮事件》⑦《一個和八個》⑧等影片的創(chuàng)作闡述,可以看到字里行間對主題和意象描述的關注遠勝于敘事意義上的時空氣氛描述。
新時期電影在造型形式表現(xiàn)性和象征意義上的挖掘,與西方電影現(xiàn)代主義思潮相一致,也與中國文藝傳統(tǒng)中“文以載道”“意在筆先”相契合,但缺少影像敘事維度上的深入探索。之后田壯壯在回顧《獵場扎撒》的影像風格時明確表示:“那個時候比較極端,排斥劇作、排斥對白、排斥交代,排斥一切非影像化的東西。從《獵場扎撒》到《盜馬賊》,已經到了非常極端的程度。”⑨
四、重回敘事: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電影影像探索的敘事轉向
盡管東西方語境中關于敘事的討論早已有之,但敘事學是20世紀60年代末期在俄國形式主義以及西方結構主義理論的雙重影響下才發(fā)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以1969年法國文藝理論家茨維坦托多羅夫首次提出“敘事學”概念為標志。之后,大量關于敘事作品結構分析的理論著述開始出現(xiàn)。20世紀70年代初期,電影結構主義理論開始由電影符號學轉向電影敘事學的研究。80年代中期,敘事學理論開始被逐步介紹到中國,而電影敘事學理論進入中國電影創(chuàng)作視野是在90年代之后了。
筆者查閱1979至1989年十年間包括第四代導演《小花》《芙蓉鎮(zhèn)》及第五代導演《黑炮事件》《紅高粱》等重要影片的三十余篇電影導演和攝影創(chuàng)作闡述,其中少有對于影像敘事的關注。攝影師的言說和創(chuàng)作闡述中,帶有中國傳統(tǒng)意味的“意境”一詞的使用頻度遠高于西方電影師經常強調的“氣氛”描述。“氣氛說”著眼于敘事和寫實(時代氛圍、地方特色、生活氣息、主體處境和情緒狀態(tài)的描述),“意境論”則著重于意象表現(xiàn)(具象畫面的抽象喻意)。意境與氣氛的微妙差異,恰恰反映著新時期中國電影影像創(chuàng)作的審美訴求。
拍攝于1987年的《末代皇帝》是對中國電影影像創(chuàng)作影響較大的一部影片,該片攝影師斯托拉羅及其“用光作畫”的言說在國內攝影師中頗受追捧,但不同時期中國電影攝影對于《末代皇帝》的關注點有細微差異,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年中國電影對《末代皇帝》的影像研究主要集中于該片色彩光線的象征意義,比如皇帝兒時的紅黃色調是對于皇權和帝王生活的表征;皇帝青年時代的綠色和白色調是對于成長和西方文明啟蒙的隱喻;而戰(zhàn)犯管理所的段落采用的灰冷基調則是對末代皇帝沒落和頹態(tài)的描摹。90年代后期的著述中開始出現(xiàn)影像敘事層面的分析,劉勇宏《用光參與敘事和表意的電影攝影理念》(2001)分析了該片運用光線和色彩元素對敘事結構的謀篇布局,⑩杜昌博的《聊聊電影〈末代皇帝〉銀幕劇作的敘事視點》關注到影像的敘事視點與攝影機視角設定之間的關系,穆德遠《故事片電影攝影創(chuàng)作》中則用《末代皇帝》中大量實例進行影像造型輔助敘事的細節(jié)分析:英國教師莊士敦要求皇宮內務大臣同意皇帝戴眼鏡一段的長鏡頭,光線輔助刻畫了兩個相互對峙的人物(莊士敦和內務大臣)的情緒變化,光線變化的節(jié)奏與戲劇情節(jié)發(fā)展的節(jié)奏相呼應。攝影師通過獨特的光線造型設計,既忠實于真實的空間環(huán)境,又發(fā)展或是說超脫了現(xiàn)實環(huán)境,既敘述了故事情節(jié),又充分發(fā)揮了具有個人特色的表現(xiàn)主義風格。
影像,是重要的電影本體元素,也是電影表達的基本語匯。在故事電影中,影像的最基本任務是敘事,包括時空描述、人物及人物關系描述,也包括影像對于情節(jié)發(fā)展的推動,影像在懸念、暗示等情節(jié)和細節(jié)上作用的發(fā)揮。一直以來,中國電影發(fā)展的主導因素在意識形態(tài)主導、藝術主導、市場主導之間變化更迭,新時期電影是中國電影的轉型期,電影的主導意識從“文革”時期的意識形態(tài)主導轉向藝術訴求為主要導向因素,重“影”輕“戲”雖然讓這一時期電影影像創(chuàng)作獲得了良好的發(fā)展空間,但也造成電影敘事研究與拓展的弱化,當中國電影市場化到來時,影像的形式訴求被推到極致,缺少敘事支撐的電影形式追求走向了單純的視覺奇觀,這是當下電影影像研究中應予以重視和補償?shù)摹?/p>
注釋:
① 鐘大豐:《論“影戲”》,《北京電影學院學報》,1985年第11期。
② 滕文驥:《〈都市里的村莊〉導演闡述》,《電影藝術》,1983年第12期。
③ 王志敏:《現(xiàn)代電影美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頁。
④ 米家慶:《野山拍攝散記》,《西影30年》,第77頁。
⑤ 鐘大豐:《是否有重談“影戲”的必要》,《電影藝術》,2008年第3期。
⑥ 張藝謀:《〈黃土地〉攝影闡述》,《北京電影學院學報》,1985年第6期。
⑦ 王新生、馮偉:《〈黑炮事件〉攝影闡述》,《當代電影》,1986年第5期。
⑧ 張藝謀、肖鋒:《〈一個和八個〉攝影闡述》,《北京電影學院學報》,1985年第6期。
⑨ 査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田壯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版,第408頁。
⑩ 劉勇宏:《用光參與敘事和表意的電影攝影理念——斯托拉羅的攝影藝術》,《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