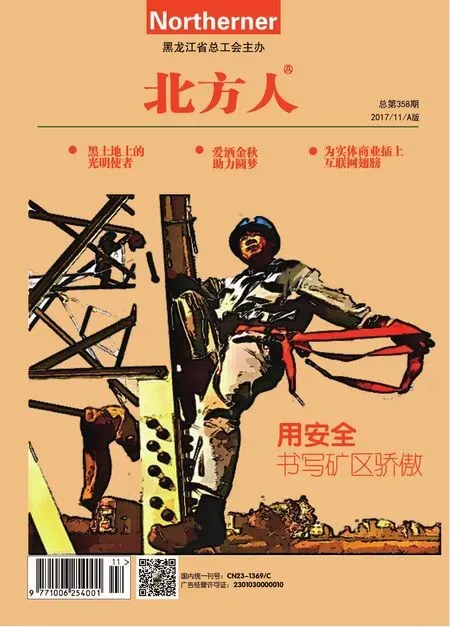母親的頭發
文/ 賀寬葉
母親的頭發
文/ 賀寬葉

大半天了,母親的心口一直微溫,大姐和弟弟一遍遍用手去試探,總以為母親會突然翻身醒過來,去給我們做飯或者給孫輩做棉衣。母親穿著壽衣——她這輩子穿過的最昂貴的衣服——躺在屋外間的木板上,我們姊妹六人圍攏著坐在她身邊的稻草里。以前這樣圍攏著母親,是她在灶前攤煎餅,攤下一個,卷起來,一撕兩半,一頭給兒子,另一頭給閨女。
母親一直厚待兒子,卻也不漠視閨女。大姐拿梳子給母親細細梳理頭發,我給母親剪下一小縷,花白、干枯、無光澤,收在羽絨服內里的口袋中。
我從不記得母親年輕時候的模樣,因為家事操勞,印象里好像剛一見母親,她就已然有了老態。可我卻清晰記得母親的頭發。母親的辮子黝黑烏亮,有韌性,手腕般粗細,垂下來及腰。夏天的時候,母親蹲在月臺下洗頭發,我提一壺溫水,瀑布一般緩緩澆到她頭上,水花四濺,陽光打過來,形成小小的彩虹。
三個姐姐也遺傳了母親的基因,都有一頭烏黑油亮的好頭發。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母親和三個姐姐的辮子都沒了,都成了短頭發,原來是剪掉辮子賣到村供銷社換錢了。剪了辮子的母親和我的兩位嬸子拍了張照片,時間大約是1979年的夏末秋初。
那是9月,學校開學的日子,也是繳學費的日子。家里還買了一小簸箕干巴魚,也是母親和姐姐們的辮子換來的,我和哥哥嘴饞貪吃齁著了,咳嗽了半夜,還是拿她們賣辮子換來的錢買了止咳藥水才睡了個安穩覺。
母親頭發濃密,母親的心思比頭發更細更密。
我每次從城里回到鄉下老家,晚上都在母親床下搭個地鋪,娘兒倆嘮嗑說話,一直到深夜,有時候一直到天亮。
母親嘮叨的都是些瑣瑣碎碎的小事,每一件她都妥妥記在心上。莊里鄉親,七大姑八大姨,六個兒女六個家庭,家里的每一件事情,她都落不下、忘不掉。不知道是不是這些無窮無盡的小事耗干了她的心血,母親的頭發慢慢變得花白干枯,開始縷縷脫落,稀稀疏疏露出了頭皮。
母親再也不能留長頭發了。
母親病倒了,那年她六十八歲。
在醫院的一個月,中間病危一次,搶救了一整天,死神擦肩而過。母親亂蓬蓬花白的頭發遮掩著前額和半邊蒼白的臉,手無力地低垂在床邊,呼吸急促、眼神迷離,仿佛隨時都會閉上永遠不再張開。病情稍有好轉,母親立刻就叫姐姐給她擦臉擦頭發。母親這么在乎頭發,是不是心里一直記念著她的頭發帶給孩子們的歡樂和享受?我不敢去問,只是猜測。
母親那縷花白的頭發我一直保存了許多年。裝在一個透明的小長條塑料袋子里,做書簽用。書,看了一本又一本;時間,過去了一年又一年,一晃十年。十年來搬家兩次,書籍舍舊納新,夾著母親頭發的那本書再也找不到了。
十年來夢見過母親多次,仍舊是烏黑濃密油亮的大辮子,莫不是在另外一個世界,母親依然在用她的長發給子女積攢歡樂和享受?我想,一定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