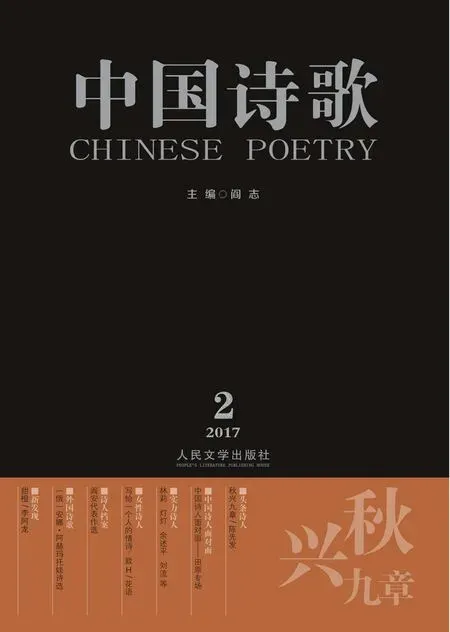給靈魂一桿綠色的戰旗
□車延高
給靈魂一桿綠色的戰旗
□車延高
就生命的直感體驗來回答,我相信“沒有溫度的擁抱,焐不熱寒冷的影子”是一句真話。所以張元把詩稿發我郵箱之后,我就在想:給了米,怎么給一個不曾謀面的人做好一次生口難調的有米之炊?惟一的終南捷徑當然是閱讀詩稿。
詩性語言如果借理性語言和眼睛捉迷藏,那么欲揭謎底本身就是一種帶入。張元的文字就有這種特定的誘惑力:
“那些涉嫌遺憾的謊言/最終,讓生活習慣了悲傷”
“一半的黑色分不出左右/一半的白色辨不清好壞”
“意想不到的相遇/習慣了開出隱藏的薔薇”
詩人的作品如果讓你讀著讀著進入了思考,感覺另有所得,這就是倍增性發散。張元就用詩句向我暴露了一個有潛質的年輕哲人。這估計就是一個詩人的寫作風格的初現端倪。它的力量在于逼迫人把心靜下來,坐于孤獨中,但又要將大腦開動到大馬力,用隱藏在詩意間的思考來為自己的思考拋光。
從詩歌表達的意想抓取看,張元是很注重捕捉細節的,這是咀嚼生活的能力,可謂眼不走空路,心不遺錙銖。這給定他大腦中詩意元素以豐沛儲備和流量,而且是把書本上所學的和生活里所見、所思、所識的東西有機地混交為自己所需的提取元素。落定紙上,有自己的篤定和自信。
讀者則想:不在倒春寒的突襲中和哮喘有一場不歡而散的邂逅,就很難把“寒冷和春天共同流浪”這種倒行逆施的句子不期而遇地撰寫進自己的詩稿里。
看來年輕并不等于他的腦丘就埋不下深邃,相反倒是能量過剩與社會浮躁的不對稱排異使他的思索無法進入凈空無塵的廣袤冥想。所以他如何埋頭于生活的積累把自己的情感寫進詩歌,然后再從厚重的生活積累中把自己的情感表達寫到獨樹一幟,就成了他和讀者共同關注的焦點。
張元的本領在于不出手,就直接抓住眼球,然后無商量,又迅捷地鞭辟入里。讓人感覺好句子是直面撲過來的,但不是他來搶奪你,而是你要搶奪時間一口氣讀下去。
我必須信手牽幾行出來,不止是因為我喜歡:
“當我一個人在月光的角落時/再也無法躲藏自己落魄的影子”
“每一個春天的擁抱都讓我害怕/短暫的重逢,永遠是離別的假象”
“孤獨地活著/是對生命的最大尊重”
“我的口袋裝滿我的憂傷/那些憂傷有著和遠方土地一樣的顏色”
“阿嬤常說,草原是我們牧人最大的財富/死了,也要貼緊,給靈魂一桿綠色的戰旗”
說真話,讀這樣的詩句,我會情不自禁地猜想,接下來他會怎么寫?結果詩人替自己的心一開繡口,吐出越來越多的好句子。
這時寫序就不再是包袱,覺得張元把這活兒交給我也算一份承讓,使我得以先睹為快。這種感覺特好,我想借他的詩句來描繪:
我的雙目緊閉,嘴角上揚
我的心,無休地幻想,一個人搖晃
寫著寫著就感覺張元成了我的老師。我寫《微言心錄》一年多了,雖未寫至“山窮水盡”,但也到了“山重水復”之時。他把詩稿發我,也算無意間遞來一把鑰匙,沒推任何一扇門,我豁然開朗,另有了一廓洞天。
張元應該屬思考型詩人,如他所言:“我們看生活,不過是看生活里的自己,思考是我最喜歡的方式。”所以他的哲思苦想在詩句中隨處可見,基本做到了讓形象思維攙扶著理性思維在相得益彰地行走。作為90后詩人代表他算出類拔萃的。
張元詩歌的特點在于:讓文字去隨心所欲,但手里始終有一根看不見的韁繩,你可以“一夜踏遍長安花”,但我“停車坐愛楓林晚”,絕不讓一盞金樽空對月。他會很巧妙地在想象中揉進一些比學術更具有實用性的思想,讓人讀得雋永綿長,心生百結。比如:“遺憾把悲傷喚醒 /像激情一樣漫長”,“我無法去接受,沒有立場地犧牲,和奉獻 /不想聽命于注定的安排,碌碌無為成了最后一只螻蟻”,“愿望總會實現,精神,極其地富裕 /但卻早已分不清黑白,罪證,倒立還是直挺”。從表面看張元的詩句都像捫心自省,不想和別人過不去。其實骨頭里賭的那口氣在詩句里回腸蕩氣,吐露得不留一點余地。叫人感覺有思想的詩人比有才華的詩人咬文嚼字更入木三分。
在詩句里求證思想和實踐的距離,這本身就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和形式主義者在表現手法上為藝術打擂。
輸贏不說,結果是打完了就要一個人坐在那里,像思想者一樣托著腮,似乎頭腦里裝著全世界人的沉重思考。如果這個人是詩人,洞見力引他先于別人在見識上遠行,這本身就就鑄就了他命運中曲高和寡的一份孤獨。
寫作離不開文字組合技巧,它可以于變化中增強文字的張力,從而形成閱讀沖擊。于是有人提出語言構建的陌生性;詩句關聯的錯位銜接;形象化語言表達理性破繭……等觀點。目的是要扳轉眼球聚合強度。
問題是現實中人們的閱讀審美不與之配合,一旦寫作技巧大于表達內容,就文字寫作看,生活中積淀的重力、情感、意境、畫面等自然景致就容易被擠出字里行間。直如現代城市建筑造型別異,風行鱗次櫛比,結果是比森林更像森林的水泥森林把生活擠壓成了單調、板結、死寂的硬結構空間。沒有了鳥獸行跡,也沒有了蛙鼓蟬鳴。
所以張元的詩在這一點上要把握好度,否則其長處有可能變為其短處。因為理性外衣穿得太厚,會顯出一種笨,笨再往前走可能是與之不同屬性的板結。到這時靈性就無目的私奔了,剩下的真的就是無共鳴的孤獨。
如果不追求曲徑通幽,讓自己從理性概括和單純抽象中分離出來,想象自己坐在有一沓詩稿的書案旁陪時間品茶,偶爾抬頭用白話的方式和風聊天,這時的張元就丟了有些做作的老成持重,詩句由自然而靈動,不知不覺中去修飾化。詩句像說出來的,有素顏的美!
這樣的句子樸素、平白,但出自于內在情感流露,不需發酵靈泉甘露,掬一捧就沁人心脾。
“媽媽,故鄉一直就是我的圓心/沒有鄉愁的快樂,是最可恥的遺忘”
“盡管那些收攏不住的溫暖 /總要賜予我潦草的陽光 /留下的鄉音,一聲比一聲長”
“荒廢掉的日子和死亡沒有什么不同/機械地重復,其實也等同于浪費”
所以我們可以說詩歌是神曲,但不要誤以為自己的作品就是寫給神看的。我們就是凡夫俗子,沒有那么大能耐,我們寫的東西首先自己要知其然,也要讓別人知其所以然。
進入情感寫作時,張元很善于卸載,思想在靈魂的底部下潛,理性被毫無批判地拋棄。這時出現在他筆下的文字又和想象中 90后寫手的筆調格格不入。詩句突然間被一種樸素思維打理,瞬間就返璞歸真,文字顯出遒勁、老道,似乎從一個經歷過許久世事滄桑人口中說出,一看就仿佛是從古道車轍的沉重里撿起來的句子,可以把一雙眼睛讀得千腸百轉,如:
“再也沒有一個懷抱/還會在寒風中等待我冰冷的身軀”
“過故人莊已無親人/寒冷留下最疼的憂傷”
“走進了一片熟悉的風景/卻再也不能安放我多余的悲傷”
“你還能在我年輕的眼睛里讀懂一些心酸/在城市的高樓中看到我不再挺拔的脊梁”
“那些積累的理由,總有說不出的源頭”
“媽媽,故鄉一直就是我的圓心/沒有鄉愁的快樂,是最可恥的遺忘”
類似這樣的句子和理性分娩不搭,一定從內心流淌出的情感重力明顯大于漢字構架。
我不知道追求透明的靈魂是否能讓自身得到放蕩不羈的自由,但從張元詩歌里大量出現的記述或想象中漂泊、流浪的場景,我可以想象詩人是把自己置身于詩歌之江湖的。
因此他所謂的漂泊、流浪是精神追求詩性的自我畫面設計。因為他的詩句在這個年紀顯得太過理性,所以他的漂泊不同于一般人的流浪。他是扛著一顆有眼睛的心行走。相同的月光下,他闖入與別人完全不同的空間。他見過“流淚的蝴蝶”、“寒冷的拐杖”、“喘氣的脈搏”、“顛簸的青山”、“倔強的鄉愁”、“不會饑餓的思想” 和“四只眼睛的城門”。
寫作風格如果作為風骨去認定,它就折射出詩人自身所持有的定力。寫作無異于一種跋涉,而年輕詩人在起始階段常常認為路是極其可疑的。不管探索和漂泊、流浪是否可以在一條河流里行船,但所去的江湖大了有些人就難做到“在最模糊的時候,與沉默簽訂協議”。
我不了解張元的生活經歷,在詩歌里他似乎反復在陳述自己曾經有過的一段漂泊和流浪,也許是精神上幻想的,但落定在詩句上,是包含沉重的:
“我的靈魂已經磨損,歲月蒼老”;“我給大地打滿補丁,向天空歌唱感動”;“我們心照不宣,繼續隨著節拍干涸 /我離開時光芒不朽,歸來時,卻是凡人”;“混淆是非的開始,并不全是雜亂無章 /我所咀嚼的每一口,都是,生存與斗爭的保證”。
僅從詩句本身的描述看,若不是少小負重,過早地承負了生活的苦累,是很難把情感作秀到這種境界的。更重要的是他不迷失,不曾忘記故鄉的方向。
詩人是用心熬血打造詩句去征服讀者的,要做到“在萬千喧囂中,色彩鮮明,素顏而生”必須有“清水出芙蓉”的定力。若對應于戲劇,其扮相、架勢、表演皆為虛假浮生。
詩的力量在面具背后,這種產自于內心的怦動與靈感不期而遇,又在某個節點驀然回首,讓人觸目所及時會突然明白:有美人,才有作為背景存在的燈火闌珊處!
張元很清楚“濃妝淡抹總相宜”的道理,所以不企望靈感成為舞臺上走板的西皮流水,更不去任由差遣,把短調生生地拖成長腔。
其實針尖就那么一點,所以能錐刺見血。靈感不是普世的智慧,這也決定了詩人把自己混成詩人容易,但要讓靈感闖進詩人的魂靈長久駐扎下來很難。
就這一點看,張元可以走很長的路,也必須走很長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