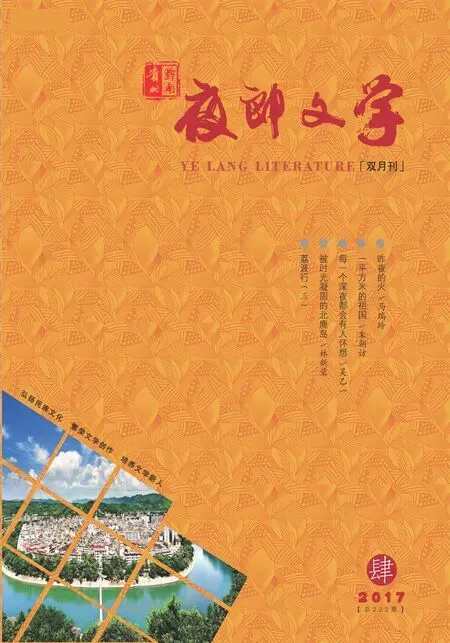爺爺的藍色古瓷碗
◎ 常忠魁
1
我們那里搞新農村改革,鄉親們告別四合院,住進了單元樓,如果想做飯,打開閥門就是冒著藍色火苗的天然氣,這時,我卻想起了拉煤土的爺爺。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農村洗衣服用的是煤土,即是膠泥土;膠泥分紅色和白色兩種,紅色的膠泥是生煤火時和泥煤子用的,為的是將煤黏在一起。紅膠泥到處都有,村南的支漳河兩岸的田野、路邊、溝渠里到處皆是,而爺爺走街串巷換的是白煤土。白煤土實際就是白色的膠泥,社員們習慣地稱呼這種白膠泥為“白煤土”,它的特點也是非常粘,特別是含堿量很大,洗衣服時只要放一些白煤土,一搓就干凈。白膠泥可不比紅膠泥好找,當時邯鄲縣只有三陵公社王官莊村一代的田野里有,只要刨開薄薄的黃土地皮,下邊盡是白色的膠泥。
于是,爺爺拉著排子車走街串巷,“舊鞋換煤土嘞——”“破鋪針爛套的,小孩不戴的舊帽的,都能換啊——。”爺爺渾身冒汗地一邊走一邊吆喝著,一聲接一聲的吆喝,招呼著還在燒煤做飯取暖的村民,用聲音把他們從各自的家中“拉”出來。
哦,當時還不是“村民”,是社員,因為當時是人民公社時期,每個社員不歸自己管,歸公社管。沒看公社,就無法吃飯。當時實施公社、大隊、小隊三級核算,土地是大隊的,社員自己沒有土地,爺爺弄這白煤土,事情不大,被抓了,就能被扣上“資本主義尾巴”的帽子,所以爺爺像是游擊隊員一般,晚上偷偷地去拉,白天到遠遠的鄉下去出售。當然,遠處的社員也沒有錢,就用家中被淘汰的破爛來換取煤土,爺爺再把這些換來的破爛送到公社采購站去賣,變成幾毛錢或者塊把錢的收入。在鄉親們眼睛里,爺爺就是干這個行當的。
其實,爺爺是位小知識分子,喜歡讀書,家里很收藏了不少的書,可惜在文革中被紅衛兵燒了。爺爺還會講故事,講三國和《水滸傳》,買完煤土回家,用一盆子水沖洗一下,爺爺就坐在院子里的大棗樹下,給我們講故事。爺爺支持他的兒子,我的父親考學,在爺爺的支持下,父親是邯鄲縣風雷中學的第一批畢業生,后來考入邯鄲地區財貿學校,是村里有名的文化人。
在那個“一大二公”的年代,僅僅靠在生產隊掙工分,無法養家糊口,何況還有我的父親上學,所以爺爺天天與人力車(村里稱作排子車)為伴,這排子車,就是爺爺養家糊口的工具,爺爺與排子車形影不離,時時維修、加木塞兒、換軸膏油(膏,邯鄲方言,往軸承上抹油)、矯車圈(讓車輪更圓)、換拉襻兒、補車底等。這輛車是他的好伙伴,用它養活了全家,爺爺親切地稱呼排子車是——老伙計。爺爺的大半輩子拉著排子車轉遍了整個邯鄲縣和永年縣的所有村莊。他不怕路遠,也不怕刮風下雨,只怕排子車里的煤土賣不出去。爺爺走過這兩縣的每個村口橋頭,十字街頭,走遍鄉間的每一條黃泥窄道,路上留下了爺爺辛勤的腳印。
2
在中國,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鄉村,存在一種東西叫——命運。命運是奇妙的,不歸當事人自己管,被一只看不見的手牽動著。
七十年代末,幾乎當了一輩子“社員”的爺爺終于好夢成真——有了屬于自己的土地,再也不用聽生產隊的鐘聲下地,也不用聽隊長的大呼小叫的咋呼了。我們家還分到了一頭小毛驢,這頭小毛驢是一頭叫驢(農村稱雄性的驢為叫驢,母驢稱作草驢)。有了這頭小叫驢,爺爺再去挖煤土和拉煤土,已經不用人力拉車了,但這頭叫驢是非常喜歡調皮搗蛋。在農村,誰都知道叫驢不好調教,凡是村里的男孩子不聽話時,就會被長輩人順口丟上一句,“真是一頭小叫驢兒”。
叫驢就像對一匹烈馬難于駕馭,你吆喝它往哪兒拐彎,它偏偏不聽話,主人一甩鞭子,它就尥蹶子踢人。爺爺賣煤土雖然不用拉車了,但用在叫驢身上的心血比原來還多。爺爺麥煤土每走到十字街頭和街心,都要先找個大石磙、大石碾這樣的東西,好把把叫驢拴上到上面,要知道大樹上絕對不能拴叫驢,因為怕這家伙啃樹皮。如果啃了樹皮,就成了“事件”,辛辛苦苦賣的錢還不夠賠人家的樹錢。只有拴好了叫驢,才能放心地吆喝:“鞋幫鞋底鞋后跟,麻繩頭子碎鐵絲兒,舊車胎,猴皮筋,鉚釘螺絲大頭針兒,破布條,碎布塊,毛巾襪子爛手絹。罐頭盒,瓶子蓋兒,碎銅爛鐵麻袋片兒。一件一件又一件,不要別的凈破爛兒。”
我放暑假后,偶爾纏磨爺爺,跟著他去賣煤土,最喜歡聽的就是爺爺賣煤土的吆喝。我們家生活稍微好些的時候,父親勸阻爺爺別出去麥煤土了,可是,誰也無法阻止爺爺趕著毛驢車去賣煤土,爺爺已經習慣了把謀生當作生活樂趣;因為爺爺有文化,有的時候就在鄉下幫人寫信,還寫出告狀的狀子,挨近春節的時候,就幫助所去的村莊村民寫春聯……從這個角度說,爺爺也是名人。那些買煤土的村人都習慣于聽爺爺的吆喝,幾天見不到爺爺的小毛驢排子車,見面后就關切地問,怎么這長時間沒有見你了?
能阻止爺爺的不再賣煤土的,不是家人的勸阻,而是科學技術的進步。隨著堿面和洗衣粉的問世,人們不再使用白煤土當作洗滌劑了。因此,白煤土就如蒸汽列車一般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爺爺的“賣煤土”這個職業也就退出了歷史舞臺。這時的爺爺也年近古稀,大街小巷里再也聽不見爺爺的熟悉的唱聲,那是他的生意歌、養家歌、更是他一生辛苦勞作的人生經歷譜寫的。很多人喜歡爺爺走街串巷的吆喝聲,喜歡聽爺爺編的順口溜,尤其是小孩子對爺爺的吆喝更加喜歡。爺爺“創作”的順口溜強調了兒化音,像是和鄉親們聊天,十分動聽,至今依然背得滾瓜爛熟。
3
爺爺有文化,自己干了多半生的換煤土的生意,就編出了這一套順口溜。爺爺在大街上邊走邊喊著,還有唱腔,就吸引來了很多家庭婦女們出來用“破爛”換煤土。有時候,干這換煤土行當的人也手稠(同行人多),走碰頭了也不好賣出去,就要往更遠的鄉村去。越遠越辛苦,饑一頓飽一頓是經常的事,爺爺不管嚴寒酷暑,還是風雪載途,都要堅持出去,為了這一家子人的生活,爺爺再苦再累,也覺得沒啥。
爺爺平生一生沒有積蓄,但他有一個寶貝——一只細瓷的藍色大碗。這是爺爺賣煤土的時候,用煤土換來的。爺爺平生和善和氣,從不和人爭論,告誡我們“吃虧是福”,可是這只涼冰冰的細瓷藍色大碗,卻點燃了爺爺的火氣,惹得爺爺被外村人到我村找村干部告狀,說我爺爺多管閑事,要好好管教一番。
事情還要從細瓷藍色大碗說起:細瓷的藍色大碗出土的大土疙瘩,原來是一個村莊,叫南葛臺村。這個村子本來煙火很旺,,可是在六百多年前的燕王掃北時踐踏,村民死的死,逃的逃,人煙漸漸稀少,后來成了一片廢墟。村人閑時就到廢墟挖古董,有挖出大銅盆的,也有挖出青花瓷盤子……我家只有幾個湖藍色的青花瓷細瓷碗,是爺爺用煤土喚來的,據“明眼”人說是明代的,上面有美麗的圖案,在陽光照耀下閃爍著迷人的光亮。可是畢竟年代久遠了,再加挖回家后保存不妥,幾個珍貴的藍花細瓷碗,大都碎裂壞掉了,最后只剩下一個,爺爺心疼極了,小心翼翼地唯一幸存的古瓷碗收藏起來。
當時附近村落的人,常常合伙到南葛臺遺址挖土,平整土地,實際上是為了挖古董,爺爺就看到眼睛里,急在心頭,那幾天竟然不再買煤土了,而是走進靠近南葛臺村土疙瘩附近的幾個村子的大隊部,找大隊干部講道理,企圖阻止破壞文物的做法;那些村干部漫不經心的態度惹火了爺爺,就罵這些大隊干部是“歷史的罪人”。這些村干部不知這位氣憤填膺的老頭子是什么來頭,忍住了火……后來找到我們村,我們村的村干部說了很多好話,才把告狀的人哄走,然后把我爺爺叫到大隊部進行教育,當然,鑒于我爺爺在村里的威望,他們不敢發火,只是讓爺爺再不要管這樣的“閑事”。
4
爺爺到底是停業了,那輛跟隨爺爺的排子車也休息了。爺爺不滿意這樣的休息狀態。有一段時間,他每天看著自己老伙計——排子車,久久地發呆。只要我們雀躍地放學回家,爺爺就會把我們拉到他身邊,給我們講述這輛破舊排子車的經歷,還經常唱著他的賣煤土順口溜,臉上泛出甜甜的笑意。我們上初中后,學了魯迅的《祝福》,對爺爺千篇一律的“故事”,已不感興趣,覺得爺爺像是《祝福》里的祥林嫂,其實爺爺的順口溜是全家在貧困年代為生存而拼搏的歌謠。
爺爺是個有心人,為了永遠記住沒有自己耕地時的生活,便把一捧白煤土放在了最后一個瓦藍大細瓷碗里,放在窗臺上,存文物一般細心保護它。爺爺老了,天天凝視大細瓷碗,生怕它跑了似的。遇到下雨天和寒冬的季節,爺爺就把大細瓷碗挪到屋里,怕白煤土被雨水淋泛和弄裂了那只珍貴的藍色瓷碗。
人有人的命運,文物也有文物的命運。在一個悶熱的夏天,院子里樹上的老母雞太熱了,一奓翅,從樹上飛到了窗臺上,爪子一撥拉,把盛著白煤土的藍色古瓷碗蹬翻在地。白煤土也撒了一地,大瓷碗立即碗碎了,摔成了一堆碎片。從此爺爺不再給我們唱賣煤土的歌謠,臉上的溝壑間蘊藏的快樂再也難覓,他終于病倒了。
又要過春節,需要燒火蒸饅頭,家里人清掃院落時,沒有征求已臥床不起的爺爺意見,就把那輛破舊的、車廂早已成為朽木的排子車劈碎,燒火用了。那年3月,爺爺隨著那輛破舊的排子車燒成的縷縷青煙走了,爺爺去世了,離開了他勞作一生的人世。
爺爺在彌留之際,還在說那只藍色古瓷碗,我知道爺爺到了另一個世界,依然會掛念他的那只藍色古瓷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