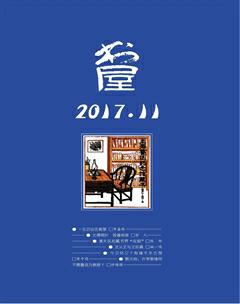能則服人 寬則得眾
王仁宇
自1931年7月出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到1949年9月辭職,馮友蘭執掌清華文學院長達十八年之久;抗日戰爭期間,他還兼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院長,為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尤其是人文學科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一、能則服人
馮友蘭對清華的最大貢獻,首先是在學科建設和發展上。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學術研究和思想發展就進入了西學東漸和中西交融的時代。這是時代發展的潮流和學術變化的趨勢。中國要告別古代,走向近代和現代。西方較中國早走了一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向西方學習。馮友蘭說:“向西方學習,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主流,好像一道長江大河,無論什么朝代,什么黨派,只要違反這個潮流,就要被沖刷而去。”這在學術研究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自然科學自不用說,那全部是從西方引進的;社會科學,諸如經濟學、法學和政治學也從西方引進來的;人文學科也是在西方學術的參照下發展的,哲學是這樣;語言學、歷史學和考古學也如此,它們已經不是中國傳統的音韻學、考據學和金石學的翻版。現代學術尤其是人文科學的發展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中進行的:既不是泥古不化、抱殘守缺;也不是崇洋媚外、數典忘祖;而是融合中西、綜合創新。1935年,馮友蘭在談到當時歷史學的趨勢時指出:“中國近年歷史之趨勢,依其研究之觀點,可分為三個派別:(一)信古,(二)疑古,(三)釋古。‘信古一派以為凡古書上所說皆真,對之并無懷疑。‘疑古一派推翻信古一派對于古書之信念,以為古書所載,多非可信。‘釋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盡信古書,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傳說。以為古代傳說,雖不可盡信,然吾人頗可因之以窺見古代社會之一部分之真相。”他說:“‘信古‘疑古‘釋古‘為近年研究歷史學之三個派別,就中以釋古為最近之趨勢。吾人須知歷史舊說固未可盡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殺。若依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講,則‘信古、‘疑古、‘釋古三種趨勢,正代表‘正、‘反、‘合之辯證法,即‘信古為‘正,‘疑古為‘反,‘釋古為‘合。”這里說的“釋古”其實也是對外來文化和本國文化進行結合和闡釋從而實現創新。在當時,“信古”是一味保守中國固有文化拒斥西方文化,“疑古”是簡單引入西方外來文化否定中國文化,而“釋古”則是用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進行闡釋,做到中西會通,綜合創新。吳宓、陳寅恪和馮友蘭的這些主張在清華大學文學院得到落實和實現,就形成了著名的“清華學派”。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后,中國的現代學術體系和學術派別已經基本成形。清華大學文學院做得比較成功,形成“清華學派”。關于該學派,清華大學校友、著名學者王瑤認為其特點是“對傳統文化不取籠統的‘信與‘疑的態度,而且在‘釋古上用功夫,做出合理的符合當時情的解釋。為此,必須做到‘中西貫通,古今融會,兼取京派與海派之長,做到微觀與宏觀結合。”對于哲學系,馮友蘭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總結道:“過去二十年中,我的同事和我,努力于將邏輯分析方法引進中國哲學,使中國哲學更理性主義一些。在我看來,未來世界哲學一定比中國傳統哲學更理性主義一些,比西方傳統哲學更神秘主義一些。只有理性主義和神秘主義的統一才能造成與整個未來世界相稱的哲學。”北京大學哲學系賀麟等主要是把西方唯心主義和中國陸王心學結合起來,而清華哲學系馮友蘭和金岳霖主要是把西方新實在論和中國程朱理學結合起來。馮友蘭說:“在戰前,北京大學哲學系、清華大學哲學系被認為是國內最強的。它們各自有自己的傳統和重點。北京大學的傳統和重點是歷史研究,其哲學傾向是觀念論,用西方哲學家的名詞說是康德、黑格爾派,用中國哲學的名詞說是陸王。相反,清華哲學系的傳統和重點是用邏輯分析方法研究哲學問題,其哲學傾向是實在論,用西方哲學的名字說是柏拉圖派(因為實在論是柏拉圖式的),用中國哲學的名詞說是程朱。”
就個人而言,在“清華學派”眾多的學者中,馮友蘭的成就無疑是最大的。他不僅有研究治學之文才,而且有行政做事之干才,在事功和學術兩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在繁忙的教學和行政之余,馮友蘭焚膏繼晷,發憤著述。在清華大學的二十余年里,他先后寫下了《中國哲學史》、《貞元六書》和《中國哲學簡史》等傳世經典。貫穿在這些著作的基本精神就是“中西貫通,古今融合”與“綜合創新,舊邦新命”。《中國哲學史》是第一部完整地用西方現代分析方法系統闡述中國哲學發展的著作,“取西洋哲學觀念,以闡明紫陽之學,宜其成系統而多新解”。它向世人宣告,即便以西方的標準去衡量,中國同樣有哲學。這不僅堅定中國人的文化自信,而且推動中國哲學的現代化。《貞元六書》吸取西方理性主義和邏輯分析方法,對中國哲學進行梳理,對西方哲學進行反思,實現中國哲學的現代化,西方哲學的人生化,做到“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國哲學簡史》是運用西方人熟悉的方法闡述中國哲學的特質,左右逢源,出神入化;舉重若輕,深入淺出;讓西方人聽得明白,中國人覺得親切。特別需要強調的是《貞元六書》。這是由抗戰催生的中國現代哲學,其創作的直接動機是為抗戰指明出路并提供精神支持。由于它把握住中國社會轉型的脈搏,切中了中國文化復興的主題,在中國思維方式革新和人類精神境界提高方面,在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探索方面和對傳統倫理的現代闡釋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獲得永久價值,成為不朽的經典。在抗戰時期,同樣受到抗戰的啟示和激發,清華大學及西南聯合大學的教授大都發奮著述,以報效國家。金岳霖的《論道》與《知識論》(初稿寫于抗戰時期),熊十力的《新唯識論》、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略稿》,以及錢穆的《國史大綱》等,這些都是中國哲學和史學研究領域迄今無法超越的經典著作,都是知識分子以學報國的絕佳典范,但它們都未能像《貞元六書》那樣,為抗戰提供一套理論根據,并對現代化建設做出系統論證。究其原因,是因為它們的作者,要么缺乏馮友蘭那種以哲人立法的氣概以及替社會建立道統的自信和自覺(如湯用彤和陳寅恪),要么缺乏西學的資源以致無法引起人們的關愛(如熊十力),要么便是其純西方的思維導致人們對其學說無法理解和欣賞(如金岳霖),所以在建立新統和社會影響方面,便不能不讓馮友蘭獨占鰲頭、獨領風騷。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馮友蘭是“清華學派”的領軍人物。他在學術上卓越的成就受到文學院教授們的敬佩。清華大學教授劉文典學問大,資格老,恃才傲物,眼中無人,曾半開玩笑地說,西南聯大只有三個教授,一個是陳寅恪,一個是馮友蘭,半個是唐蘭,半個是自己。此話雖為戲言,亦足見馮友蘭在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們心目中的地位。endprint
二、寬則得人
清華學派地位之重要、影響之巨大,清華學人才學之全面、造詣之高深,舉世罕見。成就這一盛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得天獨厚的教育優勢,穩定整齊的教師隊伍,寬松和諧的文化氛圍等,都為“清華學派”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這些與馮友蘭的得力領導是分不開的。清華校長梅貽琦先生有句名言: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說的是辦好一所大學,師資最為重要,只有一流的教授才有一流的大學。此話說來容易,行則艱難。可清華大學文學院卻真正做到一點,它聚集一批當時人文學科一流學者。1936年10月《國立清華大學教職員錄》載文學院名錄如下:院長馮友蘭;中國文學系,主任朱自清,教授陳寅恪、楊樹達、俞平伯、劉文典、聞一多、王力,專任講師浦江清,講師趙萬里、唐蘭,教員許維遹、余冠英,助教李嘉言;外國語文系,主任王文顯,教授畢蓮(美國人)、陳福田、吳可讀(英國人)、吳宓、溫德(美國人)、翟孟生(美國人)、錢稻蓀、葉公超、華蘭德(德國人)、陳銓、吳達元、專任講師楊業治,講師黃偉惠、秦善鋆,教員張錦宏、朱木祥、雷夏、史丕司烈夫(俄國人)、徐錫良、譚秀紅,助教蔣思鈿、王友竹;哲學系,主任馮友蘭,教授金岳霖、鄧以蟄、沈有鼎,專任講師張蔭麟,講師賀麟,助教李濂、張岱年、王森;歷史學系,主任蔣廷黻,教授劉崇鋐,陳寅恪、噶邦福(俄國人)、雷海宗,專任講師張蔭麟、王信忠、邵循正,講師齊思和、譚其讓,教員吳晗,助教揚風歧、何基、魯光桓、谷光曙;社會學系,主任陳達,教授吳景超、潘光旦、李景漢,講師楊堃,助教倪因心、史鏡涵、蘇汝江。抗戰時期,馮友蘭除了擔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外,還兼任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資料》記載,西南聯合大學在抗戰八年間,文學院各系所聘教授名單如下:中國文學系,教授朱自清、羅常培、羅庸、魏建功、楊振聲、陳寅恪、劉文典、聞一多、王力、浦江清、唐蘭、游國恩,副教授許維遹、陳夢家、余冠英;外國語文系,教授葉公超、柳無忌、莫泮芹、陳福田、燕卜蓀、黃國聰、潘家洵、吳宓、陳銓、吳達元、錢鐘書、楊業治、傅恩齡、劉澤榮、朱光潛、吳可讀、陳嘉、馮承植、謝文通、李寶堂、林文錚、洪謙、趙詔熊、聞家駟、陳定民、溫德、黃炯華、胡毅、副教授袁家驊、田德望、卞之琳;歷史學系,教授劉崇鋐、雷海宗、姚從吾、毛準、鄭天挺、陳寅恪、傅斯年、錢穆、王信忠、邵循正、皮名舉、向達、張蔭麟、蔡維藩、噶邦福、吳晗、陸伯慈、副教授張德昌;哲學學系,教授馮友蘭、湯用彤、金岳霖、沈有鼎、孫國華、周先庚、張蔭麟、馮文潛、賀麟、鄭昕、容肇祖、王維誠、陳康、郭福堂、王憲鈞、熊十力。這些都是國內當時一流的學者,出類拔萃,名揚天下;其中不乏千載難遇的曠世奇才,留名史冊。這么多杰出文人學者聚集在一起,在中國文化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學術史上也是少有的。他們聚集聯大文學院,團結在馮友蘭麾下。
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既有傳統文人的浪漫、狷介和狂傲,又有現代學者的獨立、自由和個性。他們研究范圍不同,師承淵源復雜,學術觀點各異,政治傾向不一,稟性脾氣參差,興趣愛好紛呈……怎樣把他們團結起來,并做到和睦相處、和衷共濟,確實是一件十分困難可又特別重要的事情。可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卻做到了。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里,馮友蘭自豪地寫道:“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恒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這首先得益于眾多教授的寬容處世與和衷共濟,其次得益于院長馮友蘭的得力領導。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各院院長,不是校長直接任命的,是先由教授會推舉兩人,校長從中聘任一個。馮友蘭連續被推舉和聘任為文院院長,足見他在教授們心中的位置。這首先來自馮友蘭在學術上巨大的成就,贏得教授們的佩服,其次是來自馮友蘭對他們的尊敬、寬容和愛護,贏得教授們的愛戴。下面幾個例子可做說明。
早在羅家倫辭職、馮友蘭代理清華校務期間,就聘請聞一多為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聞一多此前在武漢大學和青島大學因學潮之事被搞得狼狽不堪、精疲力竭。到清華大學以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開始自己生活安定、學術輝煌的生涯。聞一多和馮友蘭在政治主張上不大一致,性格更是迥然不同,但不妨礙他們成為莫逆之交。抗戰結束后,馮友蘭赴美國講學,還推薦聞一多一起去講學,聞一多堅持在國內領導學生運動,參加政治斗爭,沒有去美國。聞一多罹難后,馮友蘭特意致函梅貽琦,建議給聞一多續發薪水,并保留他在清華的住宅。后來,清華大學按有關規定不再給聞一多遺屬提供住宅,其妻子兒女無處居住。當時馮友蘭已經赴美國講學,馮夫人邀請聞一多遺孀帶領孩子們到自己家居住。1936年夏天,清華大學評議會因張申府在課堂上講課隨便,扯了很多與教學和課程無關的東西,加上帶領學生參加反對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動,欲將其解聘。馮友蘭覺得張申府思想敏銳,認為他唯物、解析和理想結合起來的觀點合乎時代潮流,爭取繼續聘任。但這一主張遭到以評議會主席葉企孫為首的大多數評議員的堅決反對。最后,張申府還是被解聘。馮友蘭甚為惋惜。所幸他的思想傳給其弟張岱年。在他的指引下,張岱年融唯物主義、分析哲學與中國人生哲學于一爐,建立“綜合創新”的哲學體系,成為大家。張岱年也是馮友蘭聘請到清華大學的。他對張岱年十分賞識,把自己堂妹介紹給張岱年,結為姻親。再看馮友蘭和陳寅恪。抗戰爆發后,陳寅恪因料理父親喪事沒有及時隨校南遷,后來輾轉香港、桂林和成都,先后執教于香港大學、廣西大學和燕京大學,并供職于中央研究院。1945年秋,因陳寅恪未能去四川李莊中央研究院語史所報到上班,所長傅斯年甚為不滿,停發其薪水。一時間,陳寅恪一家人生活沒有著落。馮友蘭得知后,立即致函梅貽琦,建議以清華教授名義盡快聘請陳寅恪回到清華,發給薪水。這樣,陳寅恪生計才有著落,并去英國醫治眼睛。吳宓和馮友蘭性格迥異,學術主張也大不一樣。他長期為愛情所困,陷入一廂情愿、自作多情的濫情中不能自拔,卻一心謀求清華大學外語系主任一職。馮友蘭覺得其性格和為人不宜領袖群倫、執掌學系,執意不讓他當。吳宓因此心生怨恨,對馮友蘭多有怨言和微詞,這在《吳宓日記》聯大那時期的文字中多有記載。但馮友蘭并不以此為念,反而對吳宓關懷備至,不僅幫他調解夫妻關系,處理和同事與鄰居關系,而且在他度假外出講學期間例外延期。在美國講學期間,馮友蘭還多次推薦吳宓到威斯康星大學講學。endprint
再看馮友蘭和劉文典。劉文典是一代學者,帶有老派文人和名士的做派。他中年喪子,已經不幸;后來,母親終老故里,生未能盡孝養,死未能視含斂;兩個弟弟客死異鄉,無力歸葬,留下來的孤兒寡母還要他接濟。連遭喪親之打擊,劉文典意志消沉,萎靡不振,為解脫苦悶,他染上鴉片,不能自拔。有學生把這情況反應給馮友蘭。馮友蘭自己生活嚴肅,沒有任何不良嗜好,對吸食鴉片十分厭惡,但覺得劉文典大才難得,不能求全責備,吸食鴉片,雖行不可取,但情有可原。于是就問,他是在課堂上抽鴉片嗎?學生回答說,沒有,是在他自己家抽。馮友蘭回答說,人家在自己家里抽就不要管了,只要不耽誤上課就可以了。
對待同事和下屬這樣,對待學生也是如此。1933年,馮友蘭旅歐講學和游歷期間,代表清華大學和德國簽署互派留學生的協議。1935年,留學生的名額出來,季羨林已經于前一年畢業,到濟南教中學,沒有了資格。馮友蘭覺得季羨林人才難得,而家境貧寒,決無自費留學的可能,建議讓季羨林回校參加考試。清華大學接受這一建議,季羨林參加考試并勝出,后來和喬冠華一起赴德留學。1939年,清華學生錢鐘書留學畢業,歸國前給馮友蘭寫過一封信。馮友蘭接到信后就立即致函梅貽琦,建議以教授身份聘請錢鐘書到清華外語系任教,月薪不低于華羅庚和汪竹溪。1942年,隨著《新理學》、《新事論》和《新世訓》三書的出版,馮友蘭名揚天下,得到學界的推崇、民間的尊敬和政府的禮遇,被教育部聘為教授,《新理學》獲得教育部評的一等獎。1943年,馮友蘭在重慶講學,受到蔣介石的宴請。一些好事的左派學生畫漫畫諷刺馮友蘭。漫畫上畫著馮友蘭腳踏由三本書搭成的臺階去拜見蔣介石,張貼在聯大校園里。馮友蘭下課從那路過,站在那里一邊看,一邊笑著說,畫得還蠻像嘛。當天晚上,有人去告訴漫畫是誰畫的。馮友蘭回答說,漫畫漫畫,是學生畫著玩的,何必當真去計較呢?對此一笑了之。1940年8月,馮契(當時叫馮寶麟)剛從西南聯大哲學系畢業,工作沒有著落,馮友蘭請他任中國哲學研究委員會秘書,同時繼續隨跟自己研究中國哲學史。馮契后來成為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大家,和馮友蘭當初的提攜、關心和鼓勵不無關系。馮契自己在回憶文章中也曾提到。
正是因為馮友蘭能則服人,寬則得眾,在清華大學出任秘書長、執掌文學院長達近二十年,成就卓著,深得人心,穩若磐石。清華學生、著名史學家何柄棣評價說:“不少清華海內外人士對此甚為不解。馮系北大出身,與清華學堂毫無關系。北伐成功后,新被任命為清華校長的羅家倫從燕京大學延攬馮友蘭以為班底,馮初任秘書長,迅即為文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成員,兼哲學系主任。雖然梅貽琦任校長(1931年12月)以前清華屢有學潮,校長迭換,而馮能屹然不撼者,主要由于:一、頭腦冷靜,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慮周至。二、深通世故,處世和平中庸,而觀點進步,學術上有高度安全感,故能與清華資深教授(如葉企孫、陳岱孫、吳正之等)合作無間,以延致第一流學者提高教研水平為共同鵠的。三、國學根底雄厚,文言表達能力特強,初則勇于起草,繼則眾望所歸,經常被推執筆。但凡任何政治或學術會議,意見紛紜,發言者眾,愿做綜合報告者寡,凡執筆者往往被公認為最干練‘得力之人。馮友蘭在清華及聯大正一貫是‘得力之人……馮友蘭主持清華聯大人文行政二十有余年絕不是偶然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