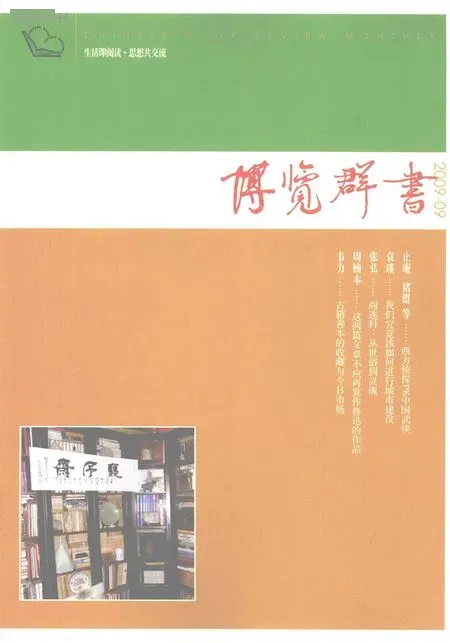我決定把家書再寫起來
趙勇
還是不死心,正月初一快晌午,我又一次去到那院新房子里,翻箱倒柜找家書。
新房其實已是舊房,那幾間房屋修蓋于1988年。在農村,修房蓋屋是大事,父親那時攢了點錢,便去找村干部劃地基,決心在他手中蓋一院房子。但省吃儉用攢倆錢不容易,也不富裕,他便只好包工不包料,把我們弟兄三個、女兒和未來的女婿都發動起來,仿佛當年的農業學大寨。后來父親每每提起那院房子,總會說:滿打滿算七千塊錢,連窗簾都置辦下來了。說這話時,父親顯然流露著某種自豪。
而那年暑假,我大部分時間也在工地張羅,曬得黑不溜秋。那時我正在處對象,工地甚至也成了談戀愛的場所。對象的父母不放心,派人找到施工現場,我只好送她回家。后來我才知道,未來的岳父岳母第一次見我是相當失望的,他們心里嘀咕:這是哪里來的民工?
一年之后,我結婚辦喜事,新房也就成了洞房,但我只是寒暑假回家小住。
父母原本是想讓大弟弟成家后成為這院房子的主人的,但又一年之后,弟弟犯事入獄,一去三年,新房也就閑置起來。而父母似乎也更愿意在老房里住著。老房的破敗,與父母焦灼、無奈、壓抑乃至荒涼的心境似完全吻合。
老房是我爺爺奶奶置辦下的。據父親說,當年買那幾間房子用了180塊大洋,合50石小米。那是1938年春天的事情。
1993年,弟弟出獄后成婚,父母也喬遷新居。但五年之后,他們又重回老房。父親說,就是那次搬家,我的書信也跟著挪了地方。
那些信是從1981年寫起的,那一年我考上大學,遠離了父母,寫信便成為我報平安、說事情的主要形式。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我讀博士時。后來,打電話越來越方便了,我也就不再寫信。2007年,我寫《書信的終結與短信的蔓延》,那自然是一篇論文,但其中或許已融入了我自己的一些切身感受。我大概寫過20年的家書,它們有多少我并無確切統計,但少說也有上百封吧。
今年元旦回家,忽然心血來潮,我想翻翻那些舊書信,但父親說:可能已經找不到了。
原來父親搬家之后,把我的書信逐一整理,按時間順序排列到一起,裝訂成冊。他把這冊書信放在一個木匣子里,時不時會拿出來翻閱一下。但重回老房,他卻沒有把那個匣子帶回來。待后來重又想起,那冊書信已不見蹤影,只有那個空匣子至今健在。
家書豈能不明不白地失蹤?我將信將疑,于是與父親去新房里翻騰一遍,結果一無所獲。但那次翻得草率,那時我似乎已寄希望于下一次更徹底的搜尋。
大年初一,我把媳婦和弟媳婦也發動起來,開始了尋找家書的重大行動。新房近年其實已重新閑置,原因是弟弟為女兒上學方便,已在城里租一間房子,一家人也就進了城。沒有煙火氣,新房已是冷清,而那間堆放雜物的房間更是布滿了灰塵。房間里摞著三個木頭箱子,還有三四個紙箱倚墻而立,里面裝滿了舊衣物舊書舊雜志。那里最有可能成為家書的藏身之處,也就成為我們重點搜尋的地方。我把箱子里的東西一一取出,又一件件翻看,希望能眼前一亮。但找了一圈,依然沒發現蛛絲馬跡,甚至沒見到老鼠咬嚙的紙屑。
弟媳婦說,她從來沒扔過賣過舊書舊報舊雜志。
而父親說,他記得那冊書信確實是放在木匣子里的。
然而,翻箱倒柜尋之遍,新房老屋皆不見。那冊家書或許永遠也找不到了。
我有些悵然,卻也只好作罷。
我至今依然無法解釋為什么我有了尋找家書的沖動。可能的原因是,幾十年之后,一個人的記憶已漫漶不清,于是遙遠的過去便被風干,變得日漸抽象起來。我想回望一下來時的路,這時已需要路標提醒。否則,路就顯豁,空空蕩蕩,既沒有風景,也沒有溝溝坎坎的細節了。
這么說,我是在尋找生命的細節?
元旦那次搜尋,母親見我找信心切,忽然想起老屋里還有一些書信,便找出來讓我翻看。但那只是二十多個空信封,其中十幾個是我寄信時所寫。我打量著信封上的筆跡,辨認著郵戳上的日期,又一封封地捏開檢查,居然發現還有五封家書留存。那應該是沒被父親裝訂起來的漏網之魚吧。它們大都寫于九十年代中后期,其中一封已非手書,而是敲進電腦打印出來的文字。那封信寫于2001年9月6日,很可能從此往后,我就不寫家書了。在我個人的寫信史上,它或許已標志著家書時代的終結。
正是從那幾封書信中,我找到了一些細節,甚至還找到了一些早已遺忘的心情。于是,我決定把那二十多個信封和五封家書帶回北京,掃描進電腦,把它們當成一種歲月留痕,妥善保存。
同時,我還決定,以后要繼續把家書寫起來,使毛筆,用宣紙,把電話里無法呈現的東西訴諸文字。我知道,在這個越來越快的電信時代,這種做法已是迂闊和奢侈,但興許這也是我贈予父母的一件禮物吧。
2013年3月4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