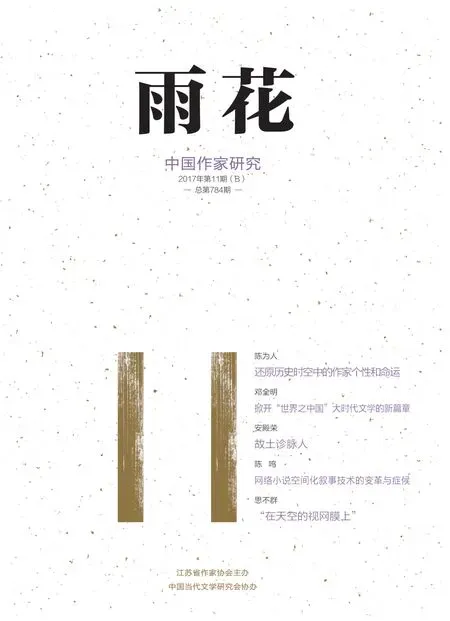靈魂之旅
——讀木心《遺狂篇》
■ 劉曉珍
《遺狂篇》出自木心散文集《哥倫比亞的倒影》,創(chuàng)作于上世紀(jì)八十年代。這篇散文可謂木心的一次靈魂之旅,旅途中“我”與莪默·伽亞謨開懷對飲,與伯律柯斯(今譯伯利克里)一起散步,陪伴培德魯尼阿斯從容赴死,目睹鐘會遭嵇康“冷遇”始末,煞有介事,頗為傳神。作品看似游戲成篇,實(shí)則大為用心,據(jù)木心對自己作品的介紹,這篇“當(dāng)時(shí)是拼命寫出來的”,足見它的分量。結(jié)合木心生平及其他作品,可知這次“旅程”并非突發(fā)奇想,而是他大半生“有所抗衡,有所肯定,有所葆儲,有所榮耀”的濃縮與呈現(xiàn)。靈動(dòng)、精致的文字背后,厚重、動(dòng)人的感情之外,隱含的是他帶著生命感悟的靈魂漫舞。
一、古詩開篇話“來歷”
開篇兩首頗具中國古意的四言詩,是整篇作品的序言,也是統(tǒng)領(lǐng)全篇的文眼。根據(jù)木心本人的解釋,他要讓“子”看到這“我”是“何等氣魄,何等來歷”,故而“都用最強(qiáng)烈最陽剛的韻”。這個(gè)“我”“喚的都是高朋”,這個(gè)“我”要“與子頡頏”、“同歸大荒”。這是在用整個(gè)生命呼朋引類,一較高低。在正文中,木心毫無保留地贊美了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映照”之美:
話說人際關(guān)系,唯一可愛的是“映照”,映照印證,致使日月光華,旦復(fù)旦兮,彪炳了一部華夏文化史。滔滔泛泛間,“魏晉風(fēng)度”寧是最令人三唱九嘆的了。
序言奠定了整篇作品的基調(diào),正如木心所說:“我來和你辯辯,挑戰(zhàn)的意思,和你比高低——整篇文章就是這意思。”①這是精神的高貴之比,是才華的精湛之比。
那么,“何其來歷”呢?細(xì)品兩首詩作,這個(gè)“我”可謂有老莊的哲理浸潤,有《詩經(jīng)》、陶潛的文辭熏陶,更有曹雪芹吞天地吐日月式的“大手筆”滋養(yǎng)。
先看哲理,“理易昭灼,道且惚恍”說的是“理容易講清楚,真理、道,講不清”,直接來自《道德經(jīng)》第二十一章:“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漆園茫茫”說的是莊子已矣,滿含著后來者“舍我其誰”之意。木心說“老子、莊子,與中國的方塊字共存”②,他對老莊哲學(xué)是相當(dāng)心儀的。他說:“‘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直通現(xiàn)代藝術(shù),直通現(xiàn)代物理學(xué)。人的精神世界,宇宙的物質(zhì)世界,都是恍恍惚惚。從‘人’的角度去觀照、去思索,更是恍恍惚惚。首先要承認(rèn)‘恍惚’,才能有所領(lǐng)會。”③
再看文字藝術(shù),木心說“詩經(jīng)、樂府、陶詩的遣詞造句,今天可用!”這兩首詩的遣詞造句即是直接繼承《詩經(jīng)》、陶詩而來。像“采采”“頡頏”“高崗”等都是《詩經(jīng)》名篇《芣苡》《燕燕》《卷阿》中的詞語。不過總體來看,筆者以為這兩首詩歌無論是詞句還是情思都更與陶淵明的組詩——《停云》《時(shí)運(yùn)》相通。《停云》詩其一曰“靄靄停云,濛濛時(shí)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dú)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其三又曰:“安得促席,說彼平生。”《時(shí)運(yùn)》詩其一曰:“有風(fēng)自南,翼彼新苗”。其二又曰:“揮茲一觴,陶然自樂。”從中即可見木心詩中的“樽中叆叇,堪息彷徨”“有風(fēng)東來,翼彼高岡”的前世身影,而陶詩中表達(dá)的“說彼平生”之意也與木心“與子頡頏”情思相近。事實(shí)上,陶潛確實(shí)是木心最為心儀的中國詩人,他說:“讀陶詩,是享受,寫得真樸素,真精致。不懂其精致,就難感知其樸素。不懂其樸素,就難感知其精致。他寫得那么淡,淡得那么奢侈。”他還說他和陶潛一樣,都不愿做塔尖,又說:“我與陶潛還有一點(diǎn)想通:喜歡寫風(fēng)。文筆、格調(diào),都有風(fēng)的特征。”④
另外,兩首詩格局上,首起“恍惚”,收歸“大荒”,又與曹雪芹《紅樓夢》之“大荒山”“太虛幻境”一脈相承。木心認(rèn)為“高大魁梧、黑膚、聲洪亮”的曹雪芹有“大師相”,并說:“他的頹廢,是北派的頹廢。我要繼續(xù)寫,是南派的頹廢。”說到曹雪芹的小說《紅樓夢》更是贊為:“大手筆!遠(yuǎn)遠(yuǎn)超過以前的小說……他睥睨千古”。⑤這里的“同歸大荒”可以說是木心對前輩文人的一種精神呼應(yīng)與致敬。
開篇一序,亮出了“我”的不凡“來歷”,氣勢宏大,筆力精健。為整部作品定下了恢弘、深邃、博雅的基調(diào)。
二、世界性視野與構(gòu)思藝術(shù)
正文四個(gè)故事,分別來自中世紀(jì)波斯、古希臘、古羅馬與中國魏晉之交。將這四個(gè)地域與時(shí)間都迥異的故事放在一篇作品當(dāng)中,體現(xiàn)了木心一貫秉持的文化觀:
所謂現(xiàn)代文化,第一要義是它的整體性,文化像風(fēng),風(fēng)沒有界限,也不需要中心,一有中心成了旋風(fēng)了。⑥
如第一個(gè)故事結(jié)尾處與“我”對談甚歡的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木心超級欣賞的正是“他的詩不重個(gè)人,不重時(shí)空,有一種世界性。”⑦正是木心對文化理解這種獨(dú)特性,使得他在故事取材的時(shí)候能夠貫通古今中外,顯示出一種異常宏闊的視野。
從具體故事構(gòu)思來看,四個(gè)故事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彼此相通又面目各異,高度體現(xiàn)了“世界性”的視野之下布局藝術(shù)。故事一:“我”勸波斯王放過一位“二手”學(xué)者,并與波斯大詩人莪默·伽亞謨暢談人生。故事二:“我”給古希臘執(zhí)政官伯律柯斯出主意,讓他宣布雅典所有雕塑他愿出資,于是希臘民眾“群情沸騰”,表示他們才不會那么吝嗇小氣。故事三:“我”處身古羅馬丞相培德魯尼阿斯府第,親眼目睹其在國王尼祿命令下達(dá)之前自我了斷,并留給尼祿“致命一擊”。故事四:“我”置身華夏魏晉之交,幸遇許多故人,親歷鐘會訪嵇康過程與嵇康被“路人皆知其心的晉文王”處死之結(jié)局。
前兩個(gè)故事相似之處在執(zhí)政者之開明,不同在于:波斯王根本不在我法眼之內(nèi),因?yàn)樗湴痢⑻摌s,而伯律柯斯,則是和“我”樂意與其一同散步的人。后兩個(gè)故事相似之處在于兩位主角都是自知必死之人。不同之處在于:對于唯美大師培德魯尼阿斯,重點(diǎn)寫其“死”之過程的優(yōu)雅從容,而對于魏晉高士嵇康,重點(diǎn)則寫其“死”前的氣度非凡。對于大家熟知的“廣陵絕唱”只字不提,正是為了避免與前者的雷同。而整體上前兩個(gè)故事中的執(zhí)政者之“兼聽”又與后兩個(gè)故事中的帝王之“狠毒”形成對比。
這種世界性組合來自木心長期的世界范圍的思想文化滋養(yǎng)。木心說“少年在故鄉(xiāng),一位世界著名文學(xué)家的‘家’,滿屋子歐美文學(xué)經(jīng)典,我狼吞虎咽”⑧,從此,確立了木心總從世界范圍來閱讀、言說與思考的習(xí)慣。說到對古人的崇敬,木心說有三位,分別就是老子、釋迦和耶穌。⑨說到最喜愛的詩人,他會說,讀莪默·伽亞謨的詩比讀李白的詩還親切!他說:“哪里有藝術(shù),哪里就有‘人’”,⑩他衡量文學(xué)藝術(shù)的品格不是看國度、民族,而是看藝術(shù)本身。由此他也會經(jīng)常看到古今中外哲學(xué)、文學(xué)、藝術(shù)的許多共通與可比。比如讀到帕斯卡的名句“那無限空間的永久沉默,使我恐懼”,就說:“這是老子的東西嘛!”?又說嵇康的“聲無哀樂論”、“鍛工雕塑”,“是非常之現(xiàn)代性的”。在小說技法上他的態(tài)度是無論古今中外,只要是好的,就“彼可取而用之!”比如在談到法國新小說藝術(shù)時(shí),贊賞“他們是有兩把刷子”,對“立體對稱型結(jié)構(gòu)”、“假伏筆”?等技法頗為認(rèn)同,這無疑都對木心這篇散文特殊的結(jié)構(gòu)形成一種啟發(fā)與影響。
三、對風(fēng)度神采等人格之美的禮贊
從作品內(nèi)涵來看,將四個(gè)故事貫穿起來的,是一條木心的“主見”之線。木心反對在作品中直接表露“主見”,他說:
哈代說:“多記印象,少談主見。”我每隔一段時(shí)日,還要想起這句話——每記一段印象,都很安逸,每說一段主見,轉(zhuǎn)身即悻悻不已。如此折騰既久,決定以印象表呈主見……“印象”是珍珠,“主見”是線,那條項(xiàng)鏈,線是看不見的,但是不能斷。?
那么,這條看不見的“主見”之線是什么呢,從四段“印象”來看,就是人格的高貴與奇?zhèn)ァ?/p>
木心說:“在這個(gè)世界上,這個(gè)宇宙中,渺小的人都是奴隸,即使當(dāng)了皇帝(包括教皇),如果人格渺小,一樣是奴隸——偉大的人,必是叛逆者。”?可見他對人格挺立的重視。在解析自己的這篇作品時(shí),他不由自主地感嘆:“古代人,就是像人。”?他要展示的就是這樣一些“像人”的人:他們高貴挺立的人格,每每想起,總是讓他肅然起敬;他們讓他“頻頻回首”的“壯舉”,又每每使他嘆為“憾事”!
精通音樂的木心,在四個(gè)故事的處理上,也是頗為講究的。四個(gè)故事仿佛一首交響樂的四個(gè)樂章,非常有節(jié)奏有張力地完成了“人格”主題的演奏。“序曲”,定下基調(diào),“我”想“與子頡頏”,“同歸大荒”的,正是古往今來世間的這樣一些“鳳”與“麟”。接下來“四個(gè)樂章”有一種漸進(jìn)感,前三段意在鋪墊,最后一段達(dá)至勝境,華彩樂章,紛至沓來,尤其最后寫到“我”參與魏晉諸名士競“比”一段描寫,有目不暇接之感。
“第一樂章”,妙境微啟。通過與波斯王一段對答,我解救了一位“奴才”。這位專事警句的奴才學(xué)者人格卑劣,先是“日夜纏著我”學(xué)得警句,接下來就去討好波斯王說是他一想出來立馬獻(xiàn)給波斯王的,被我婉曲揭穿后,波斯王差點(diǎn)要了他的命。其實(shí)這對主子與奴才都不是“我”此行的目的,“我”來原是為了“找莪默·伽亞謨談?wù)劇钡模液洼べ喼兯P(guān)注的人是有些“悲觀主義”的為萬民尊敬的所羅門、大衛(wèi),而波斯王根本不值我們勞思費(fèi)神。莪默·伽亞謨,這位被譽(yù)為“東方之星”的波斯大詩人,木心在“少年時(shí)期”即“很愛”?,出現(xiàn)在“靈魂之旅”的第一站,再合適不過。這個(gè)故事中人格問題初啟,為下文做好鋪墊。
“第二樂章”,承接前一個(gè),可謂一反一正。這個(gè)故事盛贊伯律柯斯執(zhí)政時(shí)期的一切人文的美好和人格的尊貴:建造出了希臘最好的神廟、雕像。執(zhí)政官慷慨仁慈:聽完我讓他個(gè)人出資的建議,他“真的立即”照辦;鼓舞士兵的演說句句中肯;對一群酒鬼悲憫仁慈。雅典人民個(gè)個(gè)珍惜榮譽(yù),認(rèn)為城邦的事務(wù)是大家共同的,不是執(zhí)政官一人的,大家非常樂意共同出資來完成神廟、雕像的建造;他們平時(shí)溫文逸樂,一旦上了戰(zhàn)場,英銳不可抵擋,可見“深厚教養(yǎng)所集成的勇猛,遠(yuǎn)遠(yuǎn)勝過無知無情者的魯莽”。“我”為雅典人“深厚的教養(yǎng)”所折服,為希臘的逝去而深深惋嘆:“希臘的光榮被瓜分在各國的博物館中,活生生地發(fā)呆——希臘從此是路人!”
“第三樂章”,細(xì)筆描摹古羅馬唯美主義大師培德魯尼阿斯之死。故事寫得驚心動(dòng)魄:在“酒過三巡,菜更十四,一道菜便是一行詩”之際,大師舉杯宣布:‘幸蒙光臨,不勝感慨,散席后,區(qū)區(qū)杯盞,請攜回作個(gè)紀(jì)念——今天是我的亡期。’”說得多么平常。接著示意醫(yī)士近來切斷腕上的脈管浸在水盆,便又與眾嘉賓“談笑自若”了。后來又讓醫(yī)士將脈管扎住,小睡片時(shí),這是要等待尼祿密旨的到來,他還有話要送給這位暴君。大師安詳睡去,絲毫不見懼死者的種種滑稽相。傳達(dá)密旨的人員一到,大師醒來,“神氣清爽,莞然一瞥”,把送給尼祿的話說完,就令醫(yī)士放開脈管,安然死去。通過這樣精湛地藝術(shù)演繹,“大師”圓熟的心靈與高貴的人格被展示得異常動(dòng)人。
據(jù)木心介紹,培德魯尼阿斯的故事,他是受了波蘭作家顯克維支長篇?dú)v史小說《你往何處去》的影響。?相比原著,木心的作品更具散文詩色彩,語言上簡短精煉,詩意優(yōu)雅。故事情節(jié)上也有改動(dòng),他把大師預(yù)先寫給尼祿的一封幾百字的信濃縮為臨死前說出的一句話:“尼祿是世界上最蹩腳的詩人!”這一是更加凸顯真正藝術(shù)家的無懼與自信,二也更加符合藝術(shù)大師“一語中的”的高超文字功夫。其實(shí),毋寧說這是木心心中這位藝術(shù)大師應(yīng)有的樣子。
“第四樂章”,迎來重頭戲,可謂極盡了木心的深情回望、歡欣暢快與幽幽長嘆。對于魏晉這段時(shí)期的文化,木心評價(jià)極高:
這段時(shí)期文化之高,西方還沒有注意到。其文學(xué)與生活的渾然一元,渾然一致,西方?jīng)]有出現(xiàn)過。盛唐的李白、杜甫,也未如此。不是以殉道精神入文學(xué),而是文學(xué)即生活,生活即文學(xué),這樣的渾然一元,是最高的殉道。……我認(rèn)為,魏晉風(fēng)度,就是那些高士藝術(shù)與人生的一元論。?
而這一時(shí)期的代表人物嵇康,更是木心認(rèn)為可以“稱兄道弟”之人。故而“我”一步入華夏魏晉,便高度贊美一番魏晉人的“自知之明”與“知人之明”。
正是有著高度的自知與知人,嵇康才“自導(dǎo)自演”了一步步走向死亡的這出戲。他那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正是在自知自己向來“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之下的又一次不得不為,而他也深知鐘會此來之不善,等待自己的結(jié)局已經(jīng)了然在心,既難免一死,索性說個(gè)痛快!但他不忘保全“疇昔一見,契若金蘭”的朋友山濤,為了騙過司馬昭,故而咬咬牙寫下了那封“絕交書”。
木心說,嵇康的“最高原則”,“使他不能不走這條窄路,進(jìn)這個(gè)窄門”。“窄門”出自《圣經(jīng)·新約》:“你們要進(jìn)窄門。因?yàn)橐綔缤觯情T是寬的,路是大的,進(jìn)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足見嵇康的人格在木心看來是多么高逸絕塵。因而嵇康去后,“我”“心無所托,寥落晨昏”。又借山濤之口訴說“衷情”:“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shí),猶有消息,而況人乎!”當(dāng)然,作品之外,木心對嵇康的贊美更是毫無保留的:“人格的自覺。風(fēng)度神采,第一流。”?
在《文學(xué)回憶錄》中,木心談到“我的文學(xué),有政治性,是企圖喚回人類的自愛。”?故而故事中的人物,無論是波斯的莪默·伽亞謨,希臘的伯律柯斯,羅馬的培德魯尼阿斯,中國的嵇康,個(gè)個(gè)都是極為珍視自己人格的人。正是因?yàn)橹雷詯郏嗟卖斈岚⑺古c嵇康才選擇了高貴的死亡。我們從“我”與莪默·伽亞謨所談的話題中,從培德魯尼阿斯的眼睛里,從嵇康的眉宇間,讀到了自愛之人對歷史上惡的“一再重復(fù)”的悲觀與絕望。而這,正是這部作品更深一層的含蘊(yùn)。
四、從“悲觀主義”到“悲劇精神”
籠罩全篇的,正是這樣一層揮之不去的傷悼情緒——“悲觀主義”。諸如“后來,那博士即奴才者,果然成為國際著名大學(xué)者”,“酒還是要酗的,人還是要罵的,現(xiàn)代的希臘人便是這些祖宗的后代——伯律柯斯沒有后代”,“歷史真的不過是一再重復(fù),惡的重復(fù)”,都可見作者的悲觀絕望。但木心的悲觀主義不同于常人,他對“悲觀主義”是這么理解的:
其實(shí)悲觀主義是看透了,但保持清醒、勇往向前。釋迦牟尼就是一個(gè)悲觀主義者,可是他的大雄寶殿題了四個(gè)字——“勇猛精進(jìn)”。悲觀主義止步,繼而起舞,這就是悲劇精神。?
從悲觀主義到悲劇精神,正是木心多年以來對世界人生不斷追索深思所走著的道路。
面對人類歷史悲劇之一再重演,木心經(jīng)常表現(xiàn)出他冷峻犀利的“看透”:他曾說如果他來寫老子出關(guān),那么老子“一不是隱遁,二不是仙去,三不是旅游:他老人家是去自殺的。在他出關(guān)之際,內(nèi)心的矛盾痛苦達(dá)于極點(diǎn)。”還說那五千言是老子的“絕命書”,也寫給少數(shù)后世知音的“情書”。?其實(shí)老子未必絕望,這是木心自己的絕望。然而木心的腳步并不止于這種“絕望”,“絕望”之后,他更欣賞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說希臘是他“心中的情結(jié)”:
中國的思辨,印度的參悟,還不及希臘的酒神精神更合我的心意。……希臘的得天獨(dú)厚,是正確、有力、美妙的文字,表達(dá)了不朽的思想。……真正偉大的人物都是一開始就悲觀、絕望,置之死地而后生。……希臘對死是正視的,對命運(yùn)是正視的。正視之后,他們的態(tài)度是好自為之——人道。拿人道去對抗天道,很偉大。……最了不起的,是希臘將“美”在人道中推到第一位。……美,最后帶來人格的美:勇敢,正直,戰(zhàn)死不丟盾牌。?
正是對希臘“置之死地而后生”、“戰(zhàn)死不丟盾牌”的由衷喜愛,他才戲稱自己乃“紹興希臘人”。悲觀之后,“繼而起舞”,正是木心所傾心的生命狀態(tài)。
木心反對在小說等作品中直接說理,他說:“‘思想性’只能成為小說的很遠(yuǎn)很遠(yuǎn)的背景,好像有一條低低的地平線的樣子。”?故而文中悲觀主義與悲劇精神大多流淌在字里行間,多數(shù)時(shí)候只是故事人物眉頭一鎖式的不經(jīng)意流露,有時(shí)則是通過形象的人物對話來完成。
第一個(gè)故事中,通過與莪默·伽亞謨的對話,輕輕點(diǎn)出“我”對“悲觀主義”的傾心。第二個(gè)故事中,對希臘精神的崇敬之情也寫得也非常含蓄。在完成與伯律柯斯的交游之后,“我”不禁感慨“希臘的沒落,其他古國的沒落,奇怪在于都就是不見振復(fù)了”,甚至希望“有哪個(gè)古國,創(chuàng)一例外,借以駁倒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tài)學(xué)’論點(diǎn)”。接著非常形象地寫道:
說的正高興,斯賓格勒挽著弟子福里德爾緩緩行來:
“好啊,今天的天氣好啊!”
霪雨霏霏,連月不開,我們的脾氣暴躁極了,走吧,否則要打架了。
“我”十分惋惜希臘等古國的沒落,希望他們能奇跡般地復(fù)興。而西方一些歷史學(xué)家卻在高唱“西方?jīng)]落”論調(diào)。故而“我”與《西方的沒落》作者斯賓格勒及其弟子就“話不投機(jī)半句多”了。據(jù)木心介紹,他這里之所以寫斯賓格勒,“意思是我又同意西方?jīng)]落,又不同意”,?其實(shí)流露出他對希臘精神的無限眷戀。
尤其在第四個(gè)故事中,木心借助“我”狂歡般的投身于魏晉人的競“比”之中,熱情洋溢地贊美這種精神氣質(zhì)的健康、明朗:“才愈激愈高,愈澄愈清。神智器識,蔚為奇觀。……真是個(gè)干戈四起群星燦爛不勝玄妙之至的時(shí)代。”木心所看重的,是在“干戈四起”的年代里他們卻“群星燦爛”的生命狂舞,是他們不言放棄的精神持守。當(dāng)記者問及木心作品的社會影響時(shí),他說:
尚能面臨“失控”的年代畢竟有所抗衡,有所肯定,有所葆儲,有所榮耀,尤如希臘人的“不丟盾牌”——道理粗淺如此,唯其粗淺,就不能不曲折盤旋地呈現(xiàn)它,才有可能近乎“文學(xué)”,即隱隱秉著這個(gè)棘心的意念,漫無實(shí)際的功利目的。?
這即是木心對文學(xué)功用的理解,他的文學(xué)要“曲折盤旋”呈現(xiàn)的,正是如希臘人“不丟盾牌”那般的一種人格,一種精神。
作品結(jié)尾之處,“我”回到二十世紀(jì)末曼哈頓街頭,“心中祭奠著嵇康”,明確自己“忘了五石散但飲咖啡”的“遺狂”身份,呼應(yīng)題目。“明月不來相照”流露出的是再也回不去的遺憾。身處“人類正在把地球上的詩意摧毀殆盡”?的年代,木心曾多次表達(dá)過他與現(xiàn)代文明的隔閡:“去年與林肯中心為鄰,太現(xiàn)代文明,不適意。今年搬到瓊美卡,秀木蔥蘢芳草鮮美,還不夠稱心。”?顯然,作為一個(gè)現(xiàn)代人,木心的靈魂卻屬于古代,他是一個(gè)靈魂時(shí)常游走在古代的現(xiàn)代人。
注釋:
①⑥?????? 木心講述,陳丹青筆錄:《木心談木心》,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第160頁,第138頁,第146頁,第167頁,第176頁,第147頁,第165頁,第19頁。
②③④⑤⑦⑨⑩?????????木心講述,陳丹青筆錄:《文學(xué)回憶錄》,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第209頁,第178頁,第240頁,第496-498頁,第316-317頁,第55-56頁,第233頁,第405頁,第986-987頁,第170頁,第315-316頁,第223頁,第231頁,第89頁,第169-170頁,第56-59頁。
⑧??木心:《魚麗之宴》,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第20頁,第100頁,第19頁。
?木心:《木心:我是紹興希臘人》,《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26期,第54-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