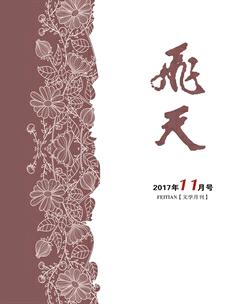現(xiàn)實主義的深厚情懷與廣闊視野
劉振華
誠如作者本人所言,“《日蝕》《月蝕》《星蝕》三部曲,可以說是我青年、中年、老年三個不同時期生活閱歷的總匯”(李廣興《星蝕·后記》)。人的社會存在決定其意識的生成,李廣興青年時代在省城上大學(xué),中年時代在西北一個小縣城的宣傳部做公務(wù)員,中年之后又在一家地級報社任社長等職,這種人生經(jīng)歷決定了他在寫小說時必然選擇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這種生活模式也決定了他小說內(nèi)容選材的“主流”傾向與時代精神。《日蝕》中處在“文革”時代的那一群個性特異的大學(xué)生,以及他們遇到的各式各樣的老師,《月蝕》中在改革開放初始古城縣圍繞于志杰與何秀女離婚糾紛先后登場的各類男女人物,《星蝕》中在改革開放深入進(jìn)行的年月以涇水日報社為中心延伸到?jīng)芩懈鱾€社會角落和層面的許許多多的人物,大都表達(dá)著他們生活于其中的那個時代的現(xiàn)實意義,體現(xiàn)著他們所蓄積的“主流”走向。李廣興的小說中,沒有坐上一片蓆子就可飛翔的魔幻,沒有只囿于一己人生的瑣屑局限,也沒有僅限于人的本我層面的赤裸性描繪,有的是人物生存于其中的鮮明的時代背景和錯綜復(fù)雜的社會關(guān)系。他小說中的各式人物的個性總是綜合著自己社會關(guān)系的本質(zhì)趨向,所以他小說中的人物都是活動在時代“主流”精神之內(nèi)的“社會人”。盡管《日蝕》中有一個叫魏靖軒的大二學(xué)生,在同學(xué)們都宗教狂熱般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時代潮流時,他卻逍遙于個人的小歡樂之中,他也并沒有泯滅將來參與社會活動的渴望,他自覺地認(rèn)為“身體是一個人的本錢,留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還是一個“社會人”。
當(dāng)然,我們在把握現(xiàn)實主義小說中人物的個性內(nèi)涵時,首先遵循的亦然是文學(xué)藝術(shù)內(nèi)在規(guī)律的要求,而不是社會學(xué)的視角,但“社會”作為各式人物生存現(xiàn)狀的大環(huán)境、大背景也是客觀存在的。李廣興的長篇三部曲《日蝕》《月蝕》《星蝕》中的人物、時代背景、生存環(huán)境都是各自獨立的,每一部都有完整的敘事結(jié)構(gòu),但三部曲中的第一人物周鱗(《日蝕》)、于志杰(《月蝕》)、宋之前(《星蝕》)的精神世界卻是一脈相承的,他們的心靈軌跡是前后呼應(yīng)與相互銜接的,構(gòu)成了“三光蝕錄”三部曲的深層依存與內(nèi)在氣場。
一、《日蝕》,現(xiàn)代迷信狂潮中的精神悲劇
《日蝕》是宏觀敘述、與正面描寫發(fā)生在中國二十世紀(jì)六十年代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一部長篇小說,其場面的宏大、思考的深度、史料的價值、結(jié)構(gòu)的匠心、人物形象的個性內(nèi)涵都是新時期以來的長篇中鮮見的,因此它具有人們認(rèn)識十年“文革”、反思十年“文革”、幫助人們樹立現(xiàn)代中國法制社會理念的豐厚意味。
中國共產(chǎn)黨在領(lǐng)導(dǎo)中國人民推翻舊世界、建立新中國的長期的艱苦卓絕的斗爭實踐中,成長起自己最英明的領(lǐng)袖毛澤東,他的偉大歷史功績誠如另一位偉人鄧小平所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可他在晚年卻錯誤地發(fā)動了一場如暴風(fēng)驟雨般席卷中國大地的“文化大革命”。也許,他的初衷是為了“反修”、“防修”,使社會主義紅色江山萬年永固。可一個沒有現(xiàn)代健全法制保障的全國范圍的群眾運動,要靠他一個人已經(jīng)樹立起來的崇高威望來指導(dǎo)和支撐。于是,黨內(nèi)一小撮政治野心家就先后粉墨登場、推波助瀾,夾雜著他們自己的政治目的,把人民的領(lǐng)袖一步一步推向“神壇”。他們大搞現(xiàn)代迷信,煽動宗教狂熱,集各種封建儀式之大成。要求人民向自己的領(lǐng)袖“早請示”、“晚匯報”、“三忠于”、“四無限”,唱“忠”字歌、跳“忠”字舞,無論吃飯、睡覺或做什么事情之前都要先背一段“最高指示”,后又在全國各地為“捍衛(wèi)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釀成大戰(zhàn)——所持觀點不同分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別(全城后來又從紅派、黑派里分化組合出一個“紅三司”),由相互之間曠日持久的“文攻武衛(wèi)”變成了大規(guī)模的“武功武衛(wèi)”,最終要拿槍桿子說話了。一腔愛國、愛黨、愛領(lǐng)袖的熱血青年,天然地成為這場運動的“得令”,即沖鋒在前的急先鋒。
《日蝕》中所描寫的金城大學(xué)中文系二年級乙班的幾個大學(xué)生周鱗、高驥、魏靖軒、徐玉雯等,就是在這場運動中出場的。他們各自不同的人生追求,在這場運動中得到了鮮明的個性化張揚。作者為我們塑造了一大群從學(xué)生到教師、到校長、到省委書記、到大軍區(qū)政委等身份,閱歷、個性氣質(zhì)、思想深度有著鮮明差異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形象,被作者永久地“貼”在那個時代的畫廊之中。周鱗是《日蝕》的靈魂人物,他在那場運動的深入發(fā)展中逐步提高了認(rèn)識,由最初的狂熱到后來冷靜的思考,反對搞“三忠于”之類的現(xiàn)代造神活動,終于對他的同學(xué)戀人徐玉雯說:“這種宗教式的禮拜只能使人們的思想更加僵化和愚昧,禁錮個性的創(chuàng)造。作為新中國的一代大學(xué)生,我們怎么能渾渾噩噩地干這種事?”徐玉雯勸他:“別去傻不癡癡做運動的犧牲品。”他沒有聽,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寫了一封持有個人看法的“萬言書”。當(dāng)然,在那個“文革”年代,任何個人的獨立思考都不會有好結(jié)果的,“萬言書”落在中央文革領(lǐng)導(dǎo)小組有關(guān)人員的手中,成了一樁“反革命”大案,周鱗被投入監(jiān)獄。在此生死攸關(guān)的時刻,金大中文系教授、著名文藝?yán)碚摷页倘鹨源罅x凜然的氣概和卓越的斗爭智慧保護(hù)了自己喜愛的學(xué)生。程瑞認(rèn)為,在當(dāng)時的那種政治環(huán)境中,像周鱗這樣的大學(xué)生能“清醒地信守一個純真正直的青年做人的原則”,是寶石般難能可貴的。他在心里想,毀了自己并沒有什么可惜的,“而毀了新中國培養(yǎng)起來的一代新人,無異于在斷送人民和祖國未來的希望”。一代名師程瑞的鮮血灑在黃河岸邊,身陷囹圄的新中國的大學(xué)生周鱗獲救,在現(xiàn)代迷信的狂潮中,他們師生共同上演了一出精神悲劇。這出悲劇,構(gòu)成了中國一個新時期的思想起點。
二、《月蝕》,只有香如故的理想愛情之花
大學(xué)中文系畢業(yè)的學(xué)生于志杰被分配到自己的故鄉(xiāng)古城縣,在縣委宣傳部做宣傳干事,他上大學(xué)以前就已結(jié)婚,在十三年的恩愛夫妻生活中,賢淑美麗但沒有文化的妻子何秀女已為他生了三個孩子。多年來,妻子何秀女相夫教子、侍奉公婆、操持家務(wù),日子平順、和睦、溫馨,在黃土高原“那孔不大的土窯洞里”留下許多他們美好的記憶。可就在這時,何秀女卻把這個家的“天”一不小心捅了個大窟窿——為了不去參加地里的繁重勞動,保住在大隊成立的一個縫紉部的工作,而失身于大隊支部書記于志仁。一生追求純潔、美好的理想愛情的于志杰,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變故,經(jīng)過一番痛苦激烈的內(nèi)心搏斗,他最終選擇了與何秀女離婚。《月蝕》就是圍繞這個中心事件結(jié)構(gòu)而成的一部長篇。
人類真摯的情愛與性愛是兩個“自然人”自己的事,可一涉及到婚姻,就是一個社會問題了,當(dāng)事者就即刻成了“社會人”。當(dāng)事者得到自己各種社會關(guān)系的支配力量的支持,那就會成為“花好月圓”的喜劇;如果支持當(dāng)事者的各種社會關(guān)系不占支配地位而處于弱勢,而反對當(dāng)事者的各種社會關(guān)系占著支配地位處于強勢,那就會釀成許多有名或無名的愛情悲劇,有名的如歐洲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中國的焦仲卿與劉蘭芝、梁山伯與祝英臺、賈寶玉與林黛玉等。《月蝕》中,于志杰與何秀女鐵了心鬧離婚,與此同時又與靈魂融為一體的戀人盧美玉海誓山盟地要結(jié)婚,但在反對他們的強大的占支配地位的社會關(guān)系面前化為泡影。這兩樁無論于志杰作了多少說明也剝離不開的婚姻事件,都帶有或形式或內(nèi)容的悲劇色彩。
首先,于志杰一提與何秀女離婚,所面臨的支配古城的社會觀念,便是他無論多么英勇無畏也翻越不過去的“蜀道”。你一個才畢業(yè)不久的大學(xué)生,拿工資,吃“皇糧”,竟然要和已為你生了三個孩子、賢惠孝敬公婆、沒有文化的農(nóng)村婦女離婚,無論你有多少條理由,古城輿論的第一反應(yīng)就給“你”一個千年有效的結(jié)論:當(dāng)代陳世美。當(dāng)年,人們看根據(jù)路遙的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人生》后,從電影院往外走時就聽有觀眾罵該劇男主人公高加林是個陳世美。他在農(nóng)村時,劉巧珍對他那么刻骨銘心地好,但招工到縣城后為了尋找共同語言、為了自己將來的遠(yuǎn)大前程,又接受了中學(xué)同學(xué)黃亞萍的愛而拋棄了劉巧珍,也活該后來雞飛蛋打,兩頭都落了空。高加林才是一個高中生,劉巧珍也才是他曾經(jīng)熱戀的人,就得如此罵名,而你于志杰是堂堂的大學(xué)生,何秀女又是已為你生了三個孩子的十三年的妻子,能不遭到詬罵嗎?一個社會形成的觀念,往往并不細(xì)究你當(dāng)事者對待這件事態(tài)度的深層原因,僅從于志杰與何秀女鬧離婚中,這一男一女、一強一弱、一優(yōu)勢一劣勢的對比,古城縣的輿論即刻都站在對何秀女同情的立場上了。在這種輿論背景中,于志杰為了給自己被打擊、被折磨的心靈尋求慰藉,為了實現(xiàn)他所孜孜以求的純美愛情的理想,又與從省城分配到古城縣廣播站當(dāng)播音員的嫵媚動人的大學(xué)生盧美玉經(jīng)歷著一場“心靈節(jié)日”般如火如荼的戀愛。盡管這驚心動魄的熱戀是他倆在隱蔽狀態(tài)下進(jìn)行的,然而,善于捕風(fēng)捉影的各類“衛(wèi)道士”們是不會放過任何蛛絲馬跡的。他們把信息傳遞給何秀女,何秀女趁干部吃飯時在古城縣委機(jī)關(guān)食堂披頭散發(fā)地一哭鬧,輿論就更讓于志杰陷入孤家寡人的狼狽境地。輿論的支持方向是一致的,表達(dá)的方式卻各有所別,有三五成群的婦女當(dāng)街相互無端的渲染,有和于志杰同住一個宿舍的小王的憑空添加,有頂頭上司高部長的關(guān)切追問,有縣委楊常委的委婉規(guī)勸,有機(jī)關(guān)同事們投來的冷蔑的眼神,也有何秀女兄長的暗中使勁。
其次,生產(chǎn)力發(fā)展水平不高、經(jīng)濟(jì)落后,對婚姻自由選擇的困擾。當(dāng)年,于志杰的父母為其娶媳婦是耗盡微薄的家資的,婚后,他上學(xué)、工作,媳婦何秀女在黃土高原上那一院窯洞里生兒育女,與公婆朝夕相處,雖清淡度日倒也溫暖和睦。可在何秀女被大隊支部書記于志仁脅迫發(fā)生那件失身的事后,一鬧離婚,對于何秀女來說更大的壓力不是社會觀念,而來自于如何撫養(yǎng)三個孩子長大成人的經(jīng)濟(jì)顧慮。盡管于志杰作出了每月從工資中給孩子劃出生活費的具體承諾,但何秀女在幾次欲尋自盡時想到的首先是三個孩子的撫養(yǎng)問題。何秀女是一個善良樸實的農(nóng)村婦女,她沒有工作,田間勞作收入低微,為了孩子,她需要一個以男權(quán)為代表的經(jīng)濟(jì)依靠,這既是何秀女在婚姻問題上沒有自由選擇空間的原因,也是她“拖”住于志杰的一個心理支撐。在這種生活現(xiàn)狀和生存環(huán)境中,于志杰的父母對兒子的婚變雖然不便多說,可他們精神上受到的打擊和對子孫們未來的無盡擔(dān)憂和愁腸恐怕是誰也代替不了的。
再次,當(dāng)時才從十年“文革”人治環(huán)境中走出來的中國的一個偏遠(yuǎn)小縣,不要說法制健全的社會環(huán)境,就連健全法制的觀念都很淡漠。自由離婚,在健全的法治社會履行法律手續(xù)是一件很平常很容易的事,可在當(dāng)時的古城就成了一件被法院“卡”住過不去的事。于志杰把離婚訴狀送到古城縣法院民事庭劉維儒庭長那里,就被以排隊調(diào)查為理由堂而皇之地“壓”在了抽屜里。劉庭長對這類案件的處理有著豐富的人治經(jīng)驗和嫻熟手法,其精華就是“拖”,直拖得當(dāng)事人撤訴。你要催他,他說那好,在當(dāng)街放一張桌子,你站在上面向過往群眾說你要離婚的理由,讓大家都聽聽。在古城,十年“文革”動輒上街批斗的遺風(fēng)依然不肯退去。一個專業(yè)的法官竟然不學(xué)法、不執(zhí)法,古城縣法制觀念的總體水平可想而知,于志杰想通過法院來判他與何秀女離婚的路子被堵住了。
由于以上幾方面的客觀原因,于志杰要與何秀女離婚的強烈的主觀愿望徹底失敗了。折騰了五年,于志杰在與盧美玉不愉快地分手時,得到盧美玉一句十分怨恨的贈言:“你就回去和你的豬老婆過去!”于是,于志杰在被現(xiàn)實碰得寸步難行時,只好又回到黃土高原那個小院的窯洞里,回到那個為自己的家長久操勞、一時失身、功遠(yuǎn)遠(yuǎn)大于過的妻子何秀女身邊。至此,他所追求的理想愛情之花,已經(jīng)零落成泥,只有香如故了。作者以現(xiàn)實主義的筆觸為讀者鮮明生動地描寫了一個愛情理想主義者的悲劇生活片斷。
三、《星蝕》,終于一個“更高水平的迷茫”
在中國改革開放深入發(fā)展的歷史時期,這部小說的主人公宋之前以一個文化人的眼光,從較為宏觀的視野一如既往地審視著這個時代的深刻變化和這種變化中的人性的多元走向。同《日蝕》《月蝕》一樣,作者在現(xiàn)實主義的深厚情懷和廣闊視野中堅守著自己宏大敘事的寫作方向。一個民族的文學(xué)作品如果沒有對自己民族生存狀態(tài)和發(fā)展要求的宏大敘事,如果沒有對社會生活重大題材的選擇、思考、揭示和描寫,就會失去主干,挺不起腰來。又由于作者長期從事新聞工作,他的小說均帶有明顯的“文化政治”的意義。當(dāng)然,他作品中反映的“政治”已不是十年“文革”語境中在文學(xué)、政治二元對立格局中的國家政治權(quán)利和政治制度,而是“我們把社會生活整個組織起來的方式,以及這種方式中包含的權(quán)利關(guān)系”。
《星蝕》以中國正在進(jìn)行并不斷深化的改革開放為背景,記敘、描寫、入木三分地揭示了西部腹地一座小城中人們的生存狀態(tài)、生活理念、思想觀念、理想境界、多元人性、多種性格以及不同的人生目標(biāo)和價值取向所形成的不可避免的沖突、碰撞。作者以直面慘淡人生的勇氣鋪開一些人在一己私利驅(qū)動下專事“窩里斗”的人性劣根現(xiàn)象,讓人掩卷唏噓。其實,在這曠日持久、高效率的內(nèi)耗中,誰都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勝利者。讓人們感到中國改革開放所面臨的諸多深層矛盾和化解這些矛盾的艱辛。
堅持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的作家李廣興始終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在《日蝕》中,他呼喚理想的民主政治;在《月蝕》中,他渴望理想的至純至真的愛情;在《星蝕》中,他又期盼至善至美的人性。《星蝕》中那個文化人宋之前,始終想保持大西北黃土高原農(nóng)民兒子的純樸本色,想以自己的真誠和善良對待周圍的人,處理身邊的事。這個文化人也在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基礎(chǔ)上敏銳而又自覺地吸納了國內(nèi)各地改革開放的新思潮、新經(jīng)驗,虛心學(xué)習(xí)發(fā)達(dá)國家的科技文化成果,以便為迅速推進(jìn)自己生活的那個小城的經(jīng)濟(jì)騰飛建言獻(xiàn)策。可在實際運作中,宋之前遇到了許多深層的矛盾糾結(jié)。這些矛盾,有的來自于舊體制的歷史慣性,有的來自于某些老觀念的頑固不化,有的來自于各種人生境界的懸殊,有的來自人性中的劣根,有的來自性格的殊異,有的來自于根本不同的人生追求。而要化解這些交織在一起的矛盾,宋之前往往力不從心。然而,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文化人,“你”卻以不向惡俗讓步、不向“地轆轆”低媚、始終保持高尚情懷并明知要付出人生代價的那種痛苦的內(nèi)心搏斗,以那種如魯迅先生一樣“精神界戰(zhàn)士”的品格感動著讀者。
與此同時,作者十分關(guān)注當(dāng)代的經(jīng)濟(jì)、文化發(fā)展和動勢,開掘出當(dāng)代社會生活諸多方面的主流傾向、價值意識,也多層次、多側(cè)面、多樣性地揭示了社會與人性的深邃內(nèi)涵。作者在社會生活“內(nèi)里”辛勤勘探,在人性深處實施聚焦,將真、善、美和假、丑、惡,歷史地審美地熔鑄在生命躍動的作品中。
《星蝕》是一部反映中國改革開放進(jìn)程中西部一個小城出現(xiàn)的諸多前所未有的問題、諸多深層矛盾、諸多困境和諸多發(fā)展思路的長篇小說,關(guān)注改革開放的各行各業(yè)的人,各個層面的人都能在這里找到一些值得思考的內(nèi)容。歷史是大眾書寫的,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指出,歷史是無數(shù)人努力的合成的結(jié)果,它不是哪個人意愿的樣子,而是無數(shù)人意愿相互補充、相互抵銷,從而達(dá)到一種平衡的樣子。作者在《星蝕》中所描寫的那種樣子,也許是帶有作者濃郁的主觀色彩的“個人意愿”中的樣子,在未來的發(fā)展中,歷史會為“誰也改變不了誰”的當(dāng)下尋找一個平衡的成為自己發(fā)展和進(jìn)步的內(nèi)在驅(qū)動力。人類對自己周圍世界、生存環(huán)境的認(rèn)識,從宏觀到微觀都是永無止境的。英國科學(xué)家查爾莫斯有句名言:“我們始于迷惘,終于更高水平的迷惘。”作家李廣興在完成他的長篇小說三部曲“三光蝕錄”之后,既有對人生理想的自覺追求的自信,又有許多迷惘的深沉感嘆。我們相信這種迷惘的感嘆,是在他自己的“更高水平”上發(fā)出的。這也許是新作品形成的出發(fā)點。
《日蝕》《月蝕》《星蝕》三部曲都以第二人稱“你”為敘事主體,這種敘事方式讓讀者感到陌生化的親切。敘述語言有著深厚功力,但貫通三部曲看,有許多地方敘述語言密度太大、太嚴(yán)肅、太板結(jié),缺少小說語言的更為理想的疏朗感與輕松感。有些敘事對豐富素材的藝術(shù)加工和提煉火候不足,正如作者自己所說,給人一種“寫生”感。尤其《星蝕》離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太近,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內(nèi)減弱了人物個性的審美功能。作者所信仰的哲學(xué)思想和幾十年的記者生涯,讓他在自己的作品中過分地看重了對現(xiàn)實的“反映”和“再現(xiàn)”,而文學(xué)在與現(xiàn)實構(gòu)成相應(yīng)的關(guān)系時,應(yīng)該是一種審美解放的“飛地”。
無論如何,耗去李廣興幾十年熱忱、智慧和心血的《日蝕》《月蝕》《星蝕》,不失為一部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中現(xiàn)實主義宏大敘事的帶有“史詩”特色的力作。
(《日蝕》《月蝕》《星蝕》三部曲由作家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