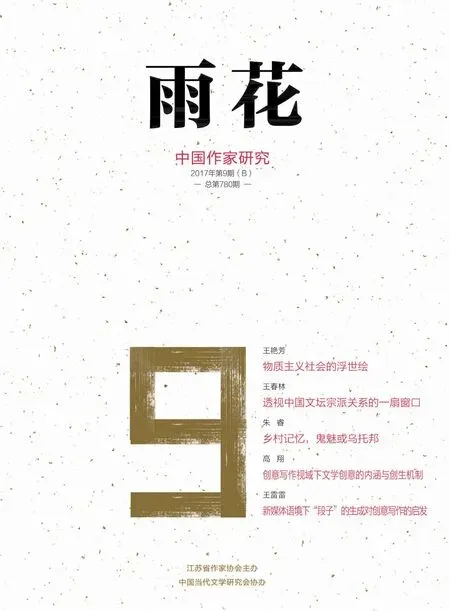游子的城市張望與精神還鄉
——陳倉中篇小說創作研討會紀要
■ 楊劍龍 溫江斌 丁莉華等
游子的城市張望與精神還鄉
——陳倉中篇小說創作研討會紀要
■ 楊劍龍 溫江斌 丁莉華等
2012年以來,陳倉已創作了二十部中篇小說,其中有17篇被刊物轉載,為作家獲得了不小聲名,其創作受到賈平凹、李銀河等人的關注和肯定。2015年八卷本“陳倉進城”系列出版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被相關媒體贊為“一代進城者的心靈史、一個大時代的傷心碑”。陳倉的這些中篇小說所關注的大多是進城者從農村到城市所經歷的命運悲歡與情感碰撞,在展現進城者的精神痛感中,思考城市化進程中農村的未來及轉型。為了能更好地認識和理解陳倉的中篇小說創作,2016年4月21日,上海師范大學當代上海文學研究中心舉行了“陳倉中篇小說創作研討會”,研討會由上海師范大學楊劍龍教授主持,作家陳倉先生、《文學報》記者鄭周明先生與會,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溫江斌、賈德靳(約旦)、王童,碩士研究生金怡、丁莉華、楊婷婷、嚴靜、李祝萍、葛英芬、張曉英、徐學斌、吳曉宇、薛翠淵、金哲羽等參加了研討。
一、鄉與城的文化地理空間
楊劍龍:陳倉原名陳元喜,他是陜西商洛山丹鳳縣塔爾坪人,母親早逝,哥哥在長途汽車墜入河中時為救他而溺亡,兩個姐姐出嫁了,他一直與父親相依為命。1998年陳倉翻過秦嶺去西安,在雜志社任編輯記者,寫小說、寫詩歌、寫散文、寫紀實文學。后來去廣州工作,2003年開始定居上海,在報社任記者編輯。陳倉最初是以詩歌創作走上文壇的,中篇小說《父親進城》刊載于《花城》2012年第6期,為《小說月報》中篇小說專號2013年第1期轉載、《新華文摘》2013年第4期轉載,此后陳倉的中篇小說不斷發表。走出商洛山的陳倉,走進西安、廣州、上海,在巨大的城鄉落差中回望故鄉,在人生苦痛的積淀與情感的發酵中,以其豐厚的生活積累、記者的敏銳眼光、詩人的激情暢想,尋找題材、編織故事、寄寓情愫,寫出了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的頹敗與衰弱,寫出都市生活中底層外來者的坎坷與磨難,呈現出游子的城市張望與精神歸鄉。
李祝萍:新世紀文學創作中,“鄉下人進城”是一個引人矚目的主題,該主題本身具有多義性,“陳倉進城”系列以故鄉為中心,即那個叫塔爾坪的地方,以這個點為中心畫一個圓,圓圈里不斷晃動著城與鄉的矛盾與碰撞。如《父親進城》與《女兒進城》兩部作品以樸實真摯的筆調,描繪鄉下人在城市生活中出現的各種不適感,父親在城里不會洗澡、不會用馬桶;女兒沒有逛過動物園等,所描繪很多故事和細節令人啼笑皆非,讀完后人們并不會真正嘲笑鄉下人的“落伍”,反而讀出一種樸實與浮華的對比。如果說《傻子進城》是鄉下人對“城”的盲目追求,是以一種出洋相式的無知表現對城市的迷戀,那么《父親進城》和《女兒進城》是“踏進”城里不能夠融入現代文明與文化的典型。
嚴靜:在陳倉的小說中,“父親”是故鄉的代名詞。《父親進城》的開篇就引用了《百年孤獨》中一句寫故鄉情懷的話,“有一個死去的親人埋在這片土地,就算故鄉了”。在作家筆下,故鄉與父親幾乎是同質一體,父親是生理上的血緣故鄉、是精神上的故鄉羈絆。父親代表著“鄉”——故鄉塔爾坪的樹的護佑者、牲口的飼養員、麥地里的耕耘者,代表了農耕文明中人性的單純、質樸與善良,他進城后的種種不適應是農耕與城市兩種文化和價值觀念的撞擊與雜糅。
金怡:陳倉用家鄉地名作筆名,可見其對家鄉深深的眷念之情,小說中還鄉是永恒的主題。鄉下人進城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滿足物質方面的需求,而已經進城的人還鄉則是精神家園的眺望。陳倉往往將城市與農村相對比,農村被看作是淳樸、良善的一面,而城市盡管繁華便利卻更多的是作為農村的對立面存在的。小說對農村常懷著挽歌式的悲戚,而對城市則采取批判的態度的。
溫江斌:如果說塔爾坪是小說反復指認的鄉村,那么上海則是小說不斷針砭的城市。相比不斷給予鄉村美好的回憶和無盡的傷感,作家對城市似乎持著一種審視和批判的目光。《木馬記》為了實現女兒上學的愿望,作為母親的張小泉,一個從農村來到城市的奶媽,無奈中不得不委身于林太太的弟弟,一個幼兒園做飯的廚師,將城市給予人的壓抑悲愴上升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小說由此進行了一場有深度的社會反思和都市批判。
葛英芬:陳倉的小說從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城市底層人的現實困境與生存苦痛,《麥子進城》里小心翼翼把自己偽裝成上海人的小記者陳元,《從前有座廟》中為了逃避法律制裁披著僧袍的假和尚陳元,《我想去西安》里為了出山做了很多荒謬事的十五歲少年陳元……陳元其實是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底層人的代表,他們在城市中拼搏努力,卻又受盡歧視侮辱,有的最終選擇回歸,有的還在都市迷茫地漂泊。
徐學斌:整體來看,“出走—歸鄉”是陳倉小說的一大主題。故鄉“塔爾平”的少年記憶都以“父親”為原點,而后擴展到故鄉的風土人情,最后抵達對都市的審視。正是透過“父親”,讀者能看到偏僻山鄉農村的空心化與頹敗。對都市漂泊者的人文關懷和城市的道德批判是其小說的另一大主題。陳倉以立足都市“闖入者”的漂泊經驗,通過外地人與上海本地人的身份對峙,富人與窮人的懸殊,城里人與鄉下人的差異,寫出了城市的利己主義和拜物教的市儈風氣。
陳倉: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地理位置,這是我未來發展方向。現在我寫的是進城,是從農村到城市,但著力點不是在農村,而是從農村到城市的路上,從文學地理角度可以寫得淋漓盡致,寫得很深入。
二、進城者精神的把脈與叩問
楊劍龍:如同沈從文一直自稱為鄉下人,陳倉內心深處也始終以塔爾坪人自居,雖然他已經在城市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在大上海生活了十四年,但是他常常以冷漠、浮躁、不安來看待生活的城市,甚至認為在城市里不安是一種常態,他在中篇小說里就常常描寫城市生活的冷漠、浮躁、不安。
吳曉宇:陳倉很精準地把握住了這個時代,寫出這一代背井離鄉者(或說追尋遠方者)心中的隱痛。農村與城市,特別是在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塔爾坪與大都市上海,這中間的巨大差異,形成了其進城故事的強烈心理張力。小說中的陳元,或者說進城的這一批有知識的青年人,雖然憑著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一份還不錯的工作,但卻始終無法將自己的根扎進這座城市里。他們的根,或者說他們的靈魂,最終還是牽系在那片埋葬著他們親人的、樸實無華的土地里。他們想將老邁的父親和年幼的女兒接進城里,讓他們感受自己所追尋所享受到的現代化所帶來的種種便利,讓他們得到更好的物質和精神享受,但卻均以失敗告終。因此他們在城市里顯示尷尬的生存境遇和無奈的內心焦灼。
溫江斌:陳倉的中篇小說不僅描寫了諸多人們進城過程中的命運變異,而且展示出時代轉型過程中進城人們的壓抑、彷徨、孤獨和疏離等心理,這種精神的分裂甚至在死后都難以得到調和,《墓園里的春天》里的一個從農村進入城市的游子離世后,最后只得將骨灰分成兩份分別安葬在城市與鄉村,在看似荒謬中流露出濃濃的痛楚。
楊婷婷:陳倉小說中人物均存在程度不同身份的缺失感,這種缺失感在父子兩代身上都有很好的展現,最為驚心動魄的卻是動物“進城”。如《小豬進城》和《羊知音》中,本該生活在山野鄉間的豬和羊卻來到了城市,在不適宜自然生存的都市空間里引發了一連串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小說從人到物,揭示出這種身份缺失感的普遍性,這種異化的生存狀態無疑具有豐富的隱喻意義。
徐學斌:陳倉小說中的“我”走出大山成為小有成就的“新上海人”,這種“出走”在遠離父輩的同時,卻背負著父輩的情感經驗和思考方式,是以“犧牲”父輩的情感需要來實現子輩個人價值的騰飛,因而“我”常常會覺得歉疚。為此,異地無根的他們又眷念父親、眷念故土,可是又總是無法回到故鄉。他們在精神上背著祖輩沉重的靈魂,“走異路,逃異地,尋求別樣的人們”,這是在現代文明的進程中城市與鄉村兩種文化碰撞的結果。
張曉英:“進城系列”寫了城市對農村的誘惑,年輕一代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為了擺脫貧困,他們渴望走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傻子進城》中的“我”以荒誕化的方式想盡辦法進城。可是當真正進入都市以后發現,現實并不如所夢想的那般美好。《女兒進城》中的“我”想讓女兒體驗都市生活的美好,可是卻處處受挫,小說中“我”的經歷也正是許多在外打拼者的真實寫照。此時的他們不禁想起了遠方的家鄉、想起了親人,故鄉成了他們心中魂牽夢縈的地方,可是卻也成了回不去的夢,故鄉已經回不去了,只好在都市無根的狀態中漂泊。
嚴靜:我注意到,陳倉小說一個貫穿的主題是故鄉,如《父親進城》中離開故鄉塔爾坪村的父親在精神上牽念著從未離開的故土;《墓園里的春天》里小姚那個不知名姓的陜西籍丈夫所需埋葬的兩個墳墓;《木馬記》里思鄉戀土的奶媽張小泉。小說選擇的故鄉總是以上海為對照的,它帶有游走于城市的人們的生存與精神困境,作家寫出了都市進入者的真實痛感。
丁莉華:人們已經進城,為何精神仍要還鄉,這是陳倉小說探討的命題。小說作了這樣的回答:一是都市的冷漠和排斥。《小豬進城》中,小豬在城市人小范的萬般折磨下流淚,小范因為在單位評職稱未能如愿,便將所有的怒氣撒在小豬身上。小說以夸張、暗示的手法和一些殘忍場面寫出未能融入城市的鄉下人所受的折磨,刻畫出都市的冷漠無情和人的精神異化。二是外鄉人自身的原因。他們對城市有一種本能的疏離,并沒有從內心真正融入這個城市,精神上并沒有真正在都市扎根。小說中諸多外鄉人在物欲橫流的都市中心生疲憊,故鄉成為精神的歸宿。
陳倉:我作品前面有一句話,“致我們回不去的故鄉”,當時為這一句話想了很多,為什么沒說“回不去的農村”,而說“回不去的故鄉”,就是想說,農村人或城市人都有自己的故鄉,其實城市人原來的故鄉也回不去了,他們出生的地方在哪兒,小時候生活的那條街、那個巷現在又在何方?
三、浸潤醇厚情感的敘事
楊劍龍: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這股日漸洶涌的大潮裹挾著諸多人,許多人離開農村進入都市,成為“都市闖入者”,他們在都市人生的拼搏與磨難中,往往又眷戀鄉村思念故土,在濃濃的鄉愁中做著故鄉的夢。一旦他們回到故鄉,常常為故鄉的凋敝零落而感嘆。當年魯迅的鄉土小說常常呈現出歸鄉與去鄉的兩種敘事模式,從而在表達濃郁的鄉愁時,呈現出對于國民性的針砭與批判。陳倉近年來的中篇小說創作,大致也呈現出進城和回鄉兩種敘事模式,常常以陳元的視角敘寫人們的進城,又常常用從來沒有走出大山農民的眼光,觀照光怪陸離的大的都市,呈現出城鄉文化的巨大落差和最初走進都市人對于鄉土文化的堅守。
薛翠淵:在這些中篇小說中,我比較關注的是《父親的棺材樹》。整篇小說結構十分緊湊,從樹出發,又不局限于樹,將塔爾坪一角的歷史和人事展現在了我們眼前。其中有童年的追憶、傳統文明的被破壞、老父親樸素的生命哲學等。小說筆觸十分細膩,砍樹前父親和樹整整嘮叨了一天一夜,他怕樹疼,他把斧子磨鋒利。柏木棺材打成后,整個院落都飄著大茴燜肉的香味,還有蝴蝶會繞著棺材飛,這些細節讓人感覺這口棺材是樹的精靈的化身。小說描寫了父親躺在棺材里的情景,在他看來棺材是人的歸宿,躺在里面安詳、踏實,沒有恐懼、孤獨,他在棺材里睡覺的時候,甚至夢到了母親給他納鞋底的溫馨場景。
李祝萍:農村與城市的沖突不是一言以概之的簡單命題,作者的進城系列在創作上不是從審丑意識出發,具有散文式的清新風格,正如賈平凹老師評價的:“這樣的一種清新,在文壇上刮起的風,真正咱老家的山岡,你說它硬它也硬,說柔它也柔,反正是多種氣味,多種味道都在里邊。”他的這些中篇小說有故事更有情感,那種詩歌的韻味氤氳其間,感動著我們,激動著我們。
溫江斌:陳倉先生最早是從事詩歌創作,當轉向小說創作時,寫詩的精神汩汩地流淌其間。陳倉小說的詩性首先體現在他直接將詩歌置入于小說文本中,如《美麗而亡》的“玉蜻蜓”評彈,《墓園里的春天》的“雙碑記”詩歌,《上海十日談》里“我”為米昔寫詩等等。而且,讀這些中篇小說時大多可以體悟到作家情感的抒發,小說故事總是隨著情感而波動,情感成為結構小說的主要力量。此外,陳倉小說的詩性化更多體現在語言運用上,他多用短句、少用長句,語言簡單干凈,有一種明晰和清新的境界。
金哲羽:《羊知音》是我比較喜歡的一部小說,小說談論了在當代城市中“知音”缺失的現象,根本上是人與人之間信任的缺失,拜金、物化、追名逐利的城市病。作者用諷刺串聯情節:主人公拉二胡時不小心將弦拉斷,為了遵循祖訓,需要有人聽其九遍才能修弦;然而無人靜心欣賞,唯有一只羊成為知音;當主人公要去參加選秀節目的時候,小說又將觀眾、經理等的丑態百出描繪得淋漓盡致,夸張地暗諷了當代選秀節目的價值趨向。這是一個基本虛構的故事,但是這又能讓讀者看出故事背后的真實。荒誕中的真實,使人啞然失笑而又能發人深省,產生一種獨特的張力。特別是,景物和情節能夠相互交融是此作的重要特色,如對雪的描寫:“所以在這種不太冷的地方下雪,看到雪花之后你不會立即想到純潔。”但是后面又說:“天空還在飄著雪花,雪花少有地不再落地便化了,而是一片一片地聚積起來,把這個夜晚打扮得有點純潔的樣子了。”這種情景交融的敘事,使得人們很容易預感到情節轉變的趨向,感受到其中隱藏的韻味。
陳倉:我的小說文本看上去不像小說,也不像散文,曾有學院派學者對這種文本提出了質疑。我所有小說里面沒有曲折的情節,不是用情節推動小說的發展,完全是由于情感,情感在推動整個故事的發展。如用建筑來比喻我的小說創作,別人的小說都是經過大師設計的,用什么樣的柱子、梁椽、磚瓦,用什么樣的雕花,用什么樣的窗子,都是經過嚴格精確的設計的,我的小說其實就是一個小屋,農村人蓋小木屋,想怎么搭就怎么搭,這可能是我短處,也可能是我的長處,我現在想不清楚,還在摸索中。
四、經驗之后的突破與提升
楊劍龍:陳倉是一位詩人,他用詩人的眼光觀察世界;陳倉是一位記者,他用記者的敏銳捕捉生活;陳倉是一位流浪者,他用浪子的心態回眸故鄉。陳倉的中篇小說幾乎沒有跌宕起伏驚心動魄的故事情節,有的只是進城者的尷尬與無奈,有的只是回鄉者的凄涼與落寞。
金怡:陳倉的小說也存在某些可以繼續打磨之處,如《父親的棺材樹》以第一人稱講述故事,“我”作為局外人卻一清二楚地知道父親和大美人在房間中所發生的一切,這明顯超出了第一人稱敘述視角的范圍。還有,小說對于城市弊端的暴露和批判時,常將主人公在城市中尋求出路的途徑歸結于自己的心態,似乎主人公只要積極調整心態就可以解決問題,這似乎略顯單薄。如果小說能將思考擴展到對社會制度和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分析,應該會更具深度。此外,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導致農村經歷著巨變,原先印象中的農村早已不復存在。面對農村和城市發生的遽變,如何書寫農村和城市,是擺在作家面前新的課題。
鄭周明:我覺得陳倉部分小說對城市看法在某些方面有些極端,其實城市跟鄉村不能說誰對誰錯,誰有原罪,他們并不是一個主動選擇的結果,或者說城市必然是追求物質,鄉村可能必須要向城市學習,他們的原罪有可能背后有制度的邏輯。還有就是,除了農村的年輕人,他們想融入城市,但因為他們是打工二代,由于多種原因難以融入城市;同時像現在城市的年輕人,也感覺自己和城市的格格不入,感覺到巨大的生存壓力。這些城市年輕人和鄉村進來的年輕人,他們該如何共同面對城市的未來,這可能是陳倉小說創作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所在。
溫江斌:大部分作家在小說創作起步的階段大多會借用和化用自己的人生經驗和生活狀態,因為生活感動著他們,帶給了他們諸多思考。陳倉也不例外,這些中篇小說不少情節、情感和場景都來自生活現實,這或許是作家人生中難以忘懷之處,但由此在小說中也出現了某些情節的類型化的現象。需要警惕的是,當代一些作家在創作中將生活經驗用完之后出現了寫作“真空”“斷層”,或不能繼續走下去,或繼續原地踏步。這既需要作家通過虛構、想象等手法注意力避這方面陷阱,還要作家進一步拓寬更為豐富的生活,感悟更為廣闊的體驗,獲得更為深邃的思考。
薛翠淵:陳倉的部分小說在結構上還不夠緊湊,可以進一步完善,如《上海十日談》里有一個物象“殘缺的瓷娃娃”,“我”曾扔掉瓷娃娃,米昔撿了回來說“再斷也是維納斯”,而患有心臟病的米昔,不也是一個“殘缺的瓷娃娃”嗎?是否可以將這個物象更加豐富化,加入一些筆墨賦予它更深的內涵,使小說多一條副線。如結尾可以設置一個場景,老人屋里掛著各式各樣的瓷娃娃,只是都是殘缺的,活脫脫是米昔撿回來的那個瓷娃娃的翻版,一陣山風吹來,瓷娃娃晃動的聲音,仿佛是米昔的微笑……,等等。
陳倉:我的文學底子很薄,之前寫小說幾乎沒有技巧,后來逐漸有意識了。剛才聽你所說,《上海十日談》按照這樣改就很好。另外,其實《空麻雀》后面是個敗筆,我當時是把自己當成一個社會學家,想解決這樣一個問題,既然不是農村的問題,也不是城市的問題,要回到農村怎么解決這個問題,讓這些人回到農村,具備什么樣的條件,企圖在最后尋找一個解決的辦法,是很蒼白的。寫作是很痛苦的,如何突破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如果創作一篇一篇全在原地爬坡,只是故事變了一下,人物變了一下,情感還是那個情感,眼界還是那個眼界,那可能就出問題了。今天的研討會會打開我的眼界,你們說的某一句話可能給我啟迪,就把作家的眼界打開了。
楊劍龍:我想一個作家,不要想用你的文學作品解決問題,一個作家把問題提出來就夠了,如果你要去解決問題,那是哲學家、社會學家的事。你要寫得含蓄一點,豐厚一點那就夠了。
有學者認為:新世紀十年,中篇小說是成就最大的文體,它可謂代表了白話小說誕生以來的最高藝術成就,我是深以為然的。在新世紀的中篇小說創作中,陳倉是有貢獻的,他為新世紀的中篇小說創作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陳倉以其經歷過的思考過的生活編織故事,自自然然、樸樸實實、瑣瑣碎碎,卻在絮絮叨叨的講述中動人心魄,撥動人們內心那根親情的弦,彈撥出撩人心境的凄楚與悲哀,那種進城父親的不安與尷尬,那種背著靈魂去逛街的離奇與忐忑,那種故鄉正在消失的凄切與悲涼,都使陳倉的中篇小說呈現出一種沉郁悲慨的風格,祝愿陳倉先生寫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