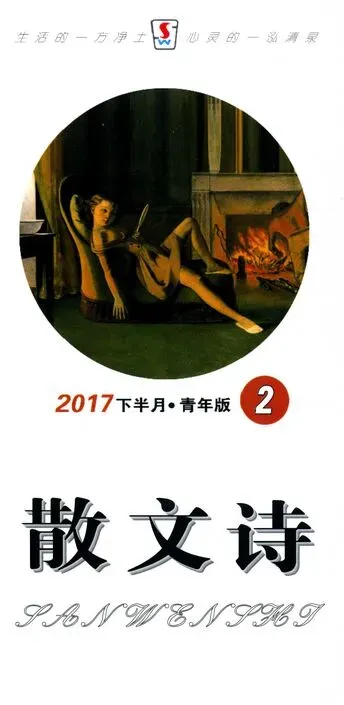掬曲留芳
湖南/彭如林
掬曲留芳
湖南/彭如林
那日去看舞劇,很幽美而純凈的一出戲,有清麗的女子捧著藍白相間的青花瓷曼妙而出,長裙的下擺搖曳不止。偶爾勾一勾腳,有微微的弧線掀起,低空劃過,極盡了旖旎之姿。全場一片安靜,只剩下了對臺上的無限遐想。后來,忽然響起了越劇的唱戲聲,伴舞而吟,聲腔細碎而輕微,卻勾勒出了那般細膩柔美而清澈的意境。
再后來,我走了神,瞇了眼睛,只聽著唱戲聲,憶起了昆曲,猶記得其空靈、幽靜和憂傷。
昆曲不似京劇、漢戲的慨然,獨有一分弱弱的氣質,恰似女子的溫柔,如桂花的芬芳,是那樣細細飄散開來的悠遠暗香,尋香而去,又沉醉倒在了旅途之中。
也許是我生性敏感而致,又覺得昆曲中彌漫著一股霧一般的愁緒,層層疊嶂,撥散不去,總也看不真切,卻覺得更有一分禪意。讓人想起幾千年前,廬山上青翠欲滴的松柏、紫爐中裊裊升起的白煙、諸峰上六教修煉時的崇敬之心。乃若“禪房花木深,曲徑通幽處”中緩緩鋪敘而來的意境。
對昆曲最深的印象,便是在陰暗朦朧的書房里,窗紙暈黃,室內簡潔。有明清時期酸枝木家具的年代感,微微霉濕的氣味。偶有一線昏黃的陽光透過細薄的窗紙射進屋內,空氣中浮動的點點塵埃清晰可見。暗紅窗格上鏤刻的雕花紋理,一筆一畫,栩栩如生。一人坐在太師椅上,另一人靠著臥榻。他們說話聲細弱而悠長。而后,又聽得一人配著樂聲,低低地唱起來,傳到屋外走廊處,好似在安詳平和的宅子里點上一點才子佳人的風流倜儻,只覺得靜世安好。
古宅子里的唱戲聲和臺面上的唱戲聲,總是不同的。一個婉轉動人,嫵媚清秀,還夾雜著壓抑下的深沉;一個皓齒明眸,流盼生輝,恍若日月。靜坐而聽,便似領略到原馳蠟象的北國風光,間或是南國屋檐邊的晶瑩水珠、青石板鋪成的幽深小巷,值得細細品味。
偶有盼目宜笑的花旦和清俊英挺的小生對唱,臺上本無任何道具,卻覺得一個在樓上緩緩訴來,一個在廊下深情安撫,眉目傳情,動人心魄,只聽得一片咿咿呀呀,不明所以,卻早已淚流滿面了,人也籠罩在一層安靜而憂愁的氛圍中。恍如中國畫上的墨跡,安靜而不張揚,一點一線的灰白和墨黑,渲染出了幾千年中國人骨子里的高潔品質和雅致情懷,“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或許就是這樣細細勾來的意境了。
聽昆曲,不要求知道細致情節,只是吃著傳統點心,飲著白瓷杯中泛紅的普洱,體味那樣深厚沉重的愛恨情仇、家破人亡,抑或是微微的欣喜,便也知足了。
像是沒翻過,我不確信,翻開內頁,見有當時讀時做的標記,在第245頁的“主要參考書(篇)目”關于引用沈醉的資料邊上,我記下了“曾在陽光舊書店見其回憶錄,惜時不知其人,未買。”如果不翻書,是怎么也記不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