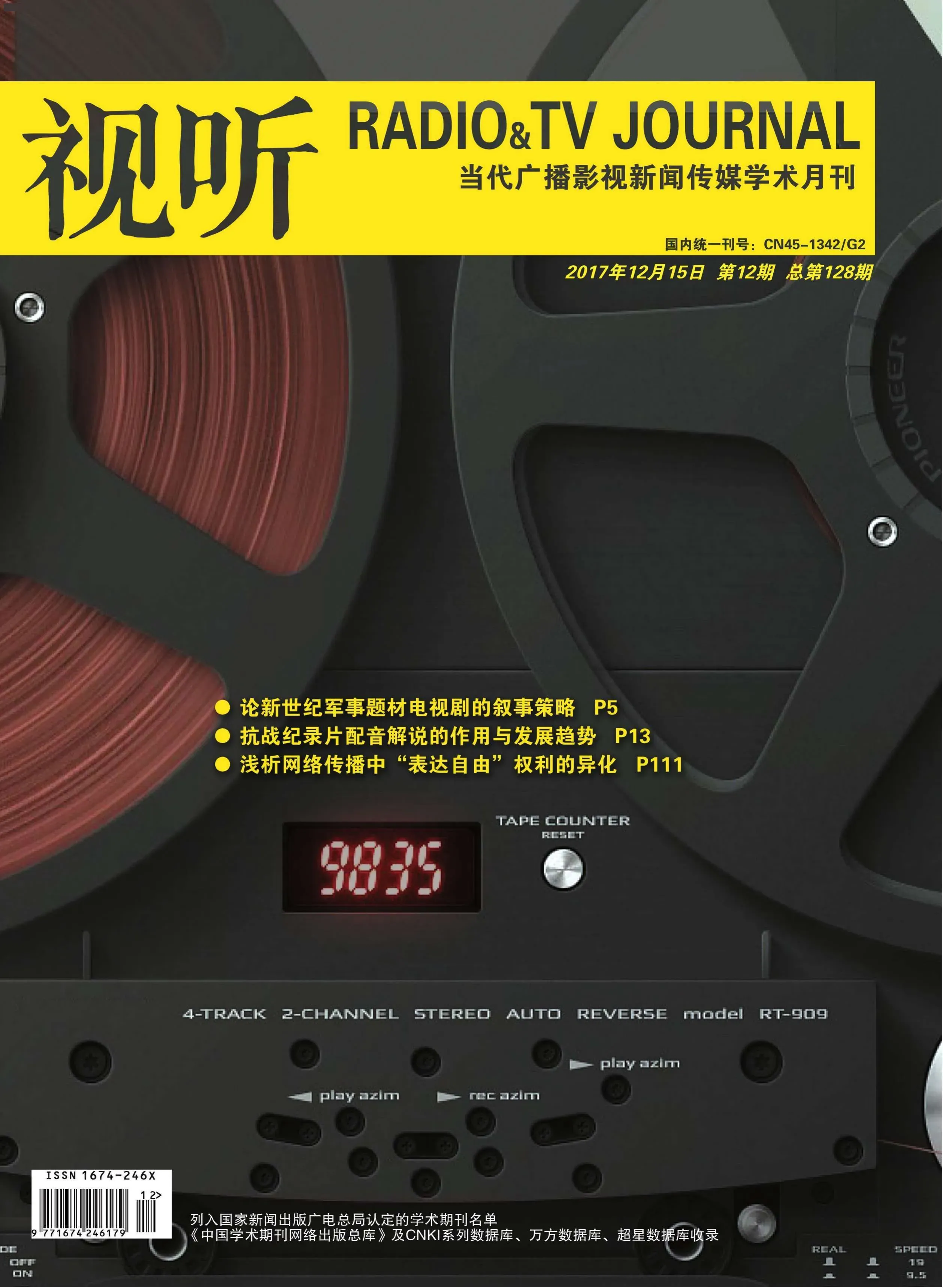唐彩鳳?唐小雁?
——徐童紀錄片中的女性
□ 顧德寶
唐彩鳳?唐小雁?
——徐童紀錄片中的女性
□ 顧德寶
女性以其在現實生活各個領域的身份、地位和文化符碼,常常成為獨立電影的拍攝對象。在徐童的獨立紀錄片中,女性不僅僅是作為弱勢群體的客觀存在映照現實生活,而且是徐童有意或無意中自我身份建構的工具,同時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還是當下整個中國獨立紀錄片創作和研究的隱喻——所以說,唐彩鳳/唐小雁是現實生活中的一個人,是徐童獨立紀錄片中的聲畫,也是一種美學意象。
女性;徐童;客觀真實;身份建構
徐童選擇了扛起攝像機,確立了他作為當代中國最具代表性獨立紀錄片導演之一的身份。從《流浪北京:最后的夢想者》到《彼岸》,從《四海為家》到《江湖》……中國獨立紀錄片在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浪潮催發的先鋒藝術創作氛圍中樹立起了旗幟。經歷了萌芽、發展和頹靡,中國獨立紀錄片的創作和傳播以及理論研究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2008年,《麥收》的出現引起了中國獨立紀錄片界不小的波瀾,藝術與倫理、敘事與紀實等問題又重新引起了業界內外的關注。最終,在各方力量的作用下,幾經風波,徐童在微博上倡議“不觀看、不討論、不傳播”。2009年,徐童的《算命》獲得云之南紀錄影像展觀眾最喜愛影片獎、香港華語紀錄片節長片組亞軍、第6屆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年度十佳紀錄片等獎項,并入選國內外諸多影展,獲得好評;2011年《老唐頭》入選第35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人道獎紀錄片競賽單元,獲得第15屆釜山國際電影節亞洲基金,獲得第16屆上海電視節MIDA導演計劃“優勝提案”。因為唐小雁的闖入,徐童的獨立紀錄片創作更上一層樓。從在《算命》中前三分之一部分露了幾次臉到成為《老唐頭》的女主角,并在第六屆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開幕式上獲得“真實人物獎”,唐小雁成為徐童的游民三部曲中獨特的女性意象。
女性以其在現實生活各個領域的身份、地位和文化符碼,常常成為獨立電影的拍攝對象,比如《遠在北京的家》《媒婆》《回到鳳凰橋》《自畫像和三個女人》。新中國成立后,頂起半邊天的女性與其說是自由獨立的女性,不如稱其為改造后的男性的影子;改革開放后,自由平等的氣氛下女性再次成為受害者和犧牲品。在徐童的獨立紀錄片中,女性不僅僅是作為弱勢群體的客觀存在映照現實生活,而且是徐童有意或無意中自我身份建構的工具,同時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還是當下整個中國獨立紀錄片創作和研究的隱喻——所以說,唐彩鳳/唐小雁是現實生活中的一個人、是徐童獨立紀錄片中的聲畫,也是一種美學意象。
一、客觀現實的映照
她是黑龍江人,16歲高中還沒畢業就跟幾個姐們兒坐30多個小時的火車到北京闖蕩,20年間倒過建材,開過歌廳,還搞過傳銷……徐童拍攝《算命》期間長期蹲守在老厲家,唐小雁去算命先生老厲(厲百程)的家里算愛情運——就這樣徐童和唐小雁結識了。老厲說她是“孤單命”,唐小雁原名唐彩鳳,小雁這個名字就是老厲為了給她改運起的。跟徐童認識兩個月后,徐童接到了求救電話。“唐小雁被仇人點了炮,店里的小妹給抓了現行;小丫頭扛不住幾電棍,當場把小雁撂了。”徐童將車抵押,把唐小雁給撈出來了,就此,二人結成了鐵哥們。唐小雁“混”在社會上,沒有文化,沒有學歷,沒有穩定的工作,沒有丈夫沒有孩子,沒有可以依靠的溫暖和諧的家庭……別說新時代女性主義者所號召的地位權利,就連普通的生存境遇下的待遇都未曾擁有。
在社會、家庭、個人等多個層面上,唐小雁作為一個極端的形象反映了我們生活中女性的客觀現實。眾所周知,紀錄片以真實生活為創作素材,以真人、真事、真情、真景為表現對象,運用各種紀實性的創作手法來達到真實性的藝術訴求。更何況,獨立紀錄片在真實客觀地反映社會現實的訴求上,又有自己的獨特的偏好。徐童在題材和拍攝對象的選擇上,首先順承了之前《麥收》的創作取向,將鏡頭對準了妓女等生活在社會邊緣的小人物。更重要的是,橫向上深刻反映了社會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對女性造成的影響,市場經濟的繁盛打破了鄉鎮農耕經濟的底盤,女性的身份和地位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唐小雁們從鄉村來到北京等發達城市,從農民變成了盲流,處在了政治經濟文化的最邊緣。還有,縱向上叩問了幾千年來的男性主導下的社會中女性亙古不變的低矮的身份和卑微的地位,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并沒有從男性的胯下將女性解放出來,妓女這個職業已經存在了千百年,縱有法律的維護和保障,唐小雁作為受害者卻成了被制裁和懲罰的對象。
唐小雁第一次亮相是作為化名出現在《算命》中,唐彩鳳是唐小雁的本名,是她從看守所保釋出來后在相關文件上簽字畫押用的名字,即是她戶口本、身份證上的名字。姓唐自然是因為她的父親老唐頭姓唐,這是我們生活中司空見慣的歷史傳承和男權文化的印記。“小雁”是因為被流氓騷擾、感情不順而找老厲給起的名字,這是受到來自男人的傷害后尋求保護的護身符。從唐彩鳳到唐小雁,她的生命歷程微縮了整個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歷史的發展變化,并見證和紀錄了這一切。有學者指出,女性主義已經從傳統女性主義轉向了后現代女性主義。李銀河在《后現代女權主義思想》中指出,后現代女性主義關注女性的多重身份及女性認同的多元化。徐童從唐小雁身上不僅發現了作為受害者的女性的一面,也看到了作為幸存者和繼承者的可以發揚光大的女性的一面。《算命》和《老唐頭》中的唐小雁的生命歷程是苦澀的,也是飽含能量的,徐童發掘了唐小雁身上現代女性的多重身份和多元價值,不能將這一切貶低為隱私的窺探和道德的評價。

二、建構身份的工具
從中國傳媒大學電視系攝影專業的學生到廣告、電視劇、電視節目、平面設計的創作者,從小公司老板到繪畫家、攝影師到小說作者,再到獨立紀錄片導演,徐童的成長和轉變與其自身經歷有著密切關系。法國著名藝術史學家丹納指出:“要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必須正確地設想他們所處的時代的精神和風俗概況。”伴隨著經濟政治的轉變,文化的風向標也轉向了,滲透并體現在徐童獨立紀錄片創作的題材和拍攝對象的選擇,進而揭示了深層次的審美心理和精神文化的原因。徐童所經歷的時代,身份的轉換和變化帶來新生活的轉機和新方向的期許,同時也造成了自我身份認同的彷徨和焦慮。在這一點上,毋庸置疑,徐童和唐小雁互相映襯。
作為拍攝者的徐童講述與被攝對象唐小雁的關系時說:“很多時候,是她在控制節奏,她突然想表達對生活的看法,想利用影像傳達自己的東西,那么我們就拍。我覺得這已經是一種合作關系,這種合作關系甚至是不平等的,因為她成了編劇,也是故事脈絡的導向,我們之間已經不是導演和劇中人那么簡單的關系,而是在共同創造一個作品,而且創造的過程以她為主。”“唐彩鳳”是她十六歲背井離鄉前在家鄉、在家人面前,讀書上學時作為女兒、妹妹、學生的名字和身份,“唐小雁”是她作為游民身份的名字——二者之間的轉換正是通過徐童的攝影機被鐫刻在歷史上。現實生活中以及徐童作品中唐小雁的身份的變更和確立,與徐童自身身份的構建暗合。徐童與唐小雁的關系不僅是生活中的哥兒們以及創作中的合作關系,還包括實現《算命》《老唐頭》創作的“利用”關系,這幾種關系以獨立紀錄片為媒介共同構建了現實生活和藝術創作中的徐童的身份。
布魯納提出,敘事是人類除邏輯之外的另一種重要的認知方式。人們的生活故事是構建自我身份的重要敘事,人物的身份構建都是在敘事中完成的。徐童拍攝《算命》《老唐頭》《挖眼睛》,首先這種創作過程就構成了徐童的人生經歷——這是構建徐童身份的基石,自我的了解、他人的了解、人格的形成便是在“故事”中完成的。徐童作為導演、扛攝影機的人,其本身的創作過程和人生經歷合二為一,自我的構建已經無形之中融合進了所創作的獨立紀錄片之中。同時,徐童的作為一個個人的獨立紀錄片創作,也折射出了整個獨立紀錄片創作群體的樣貌。通過獲獎、影展等形式,徐童的獨立紀錄片導演的身份被肯定和加固。
三、獨立創作的隱喻
經過國家精英教育的徐童被裹挾進大眾文化的洪流,理想主義與消費主義相撞,嘗試后的失敗、失敗后的嘗試以及再次失敗,剩下的僅有無所依附的理想和英雄夢。行走在邊緣的徐童選擇了攝像機作為武器守衛自己的理想和英雄夢,紀實和獨立成為其在公共文化空間發出自己聲音的傳聲筒,將獨立紀錄片作為一種語言發出自己的嘶吼。身份的游移和認同的缺乏讓“被母親的遺棄”的徐童產生了自我身份構建的欲望,在他掌握了獨立紀錄片這門語言時,“語言掏空現實,使之成為欲望”。主體的最終形成,是以語言中第一人稱代詞——“我”的出現為標志。因為主體不等于自我而是自我形成過程中構建起來的產物,所以徐童作為獨立紀錄片導演的身份建構離不開外界力量的作用。
唐小雁因為“參演”《算命》《老唐頭》成為了“明星”晉升到了精英分子的隊列:領獎、演講、喝咖啡、聊電影……唐小雁知道了上層人士是怎么看待游民的,然后回到原來生活的空間,將上層社會的生活圖景分享給游民,她能自如地穿梭在兩個不同空間和人群之間。由此,她只能是唐小雁而不再是唐彩鳳,唐小雁已經具備了多面性。徐童常常出現在其紀錄片的鏡頭中,在《老唐頭》中尤為突出,暴露出了他作為拍攝者的人為動機——他要融入被攝對象的生活中,變得不那么客觀真實。在聲音上,徐童也常常“露出馬腳”,例如《算命》中徐童勸小雁少喝點酒、問老厲問題……徐童除了在畫面和聲音上留下了自己的影子,在剪輯處理上,徐童的手法更加明顯。《算命》章回體式敘事的字幕,《老唐頭》打亂真實時空的剪輯處理等如此敘事上的安排,深深地刻上了徐童的烙印。徐童說,紀錄片是建構出來的真實,是真實的虛構。“唐小雁”最初以化名的狀態出現在我們的視野,最后在徐童的創作中獲得了生命——徐童創造了唐小雁。除了顯而易見的形式和手法上的著力處理,徐童所要獲得的更多的則是內容和內涵上的訴求,“這輩子最大的遺憾就是想成為他們,卻又永遠成為不了他們。”徐童需要通過《算命》和《老唐頭》發現自我,從其作品中的“我”的指認來實現身份的構建。拉康說:“藝術并非是分享內心的和諧,而是分享欲望與匱乏,并非爭奪欲望,而是互相維持對幻想的拋棄。”同為藝術,如果電影是用來暫時滿足欲望的夢境,那么紀錄片尤其是獨立紀錄片則是“幻想”。幻想不是需要的滿足,而是未滿足的欲望,并維持之。徐童的作者的個性化書寫——未完成的自我的構建!
1.呂新雨.記錄中國——當代中國新紀錄運動[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2.宋素麗.自我的裂變——敘事心理學視野中的中國紀錄片研究(1978-2008)[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
(作者系福州外語外貿學院影視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