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jiān)果與駝鈴
秦川
《紅人》不是把花展示給世人看,它給人看的是果。它結(jié)出的果,不是水蜜桃,不是脆香梨,是堅(jiān)果,堅(jiān)硬、粗糙,然而實(shí)在。
《紅人》的人物出場(chǎng),猶如是在一片廣袤的沙漠上,遠(yuǎn)遠(yuǎn)地從地平線的一端,出現(xiàn)了一個(gè)點(diǎn),蒼青的,模糊的,蠕動(dòng)著,擴(kuò)散著。先是吳阿興、徐菊娣,然后是李洪生、小辣椒、楊書(shū)記、顧明遠(yuǎn)、王炳金,再有吳人杰、李國(guó)祥、孫雪娥、徐建秀——聚點(diǎn)成線,成陣,成駝隊(duì),隨著一點(diǎn)悠揚(yáng)的駝鈴聲,在粗礪、堅(jiān)硬的朔風(fēng)里,嗚咽出一種蒼涼、一點(diǎn)慘烈。寫主要人物,是先有輪廓,幾筆簡(jiǎn)單的勾勒,然后有點(diǎn)染而成的面目,慢慢近了,面目清晰了,再精描細(xì)刻,眉眼就鮮活了,身心也靈動(dòng)了。寫吳阿興,出場(chǎng)時(shí)“他的腳陷在稻田里,人顯得又矮又小的,很寒磣。‘典型的鄉(xiāng)巴佬楊書(shū)記望一眼,驀地在心里就下了這個(gè)評(píng)語(yǔ)。他好像已記不起這個(gè)曾經(jīng)在公社文藝匯演中扮演過(guò)《紅燈記》中鳩山的這個(gè)人了,他想讓人家走,然而,在他眨眼的一瞬間,他眼前這個(gè)吳阿興突然讓他想起了田書(shū)記對(duì)提拔農(nóng)村干部的要求來(lái)了:矮一點(diǎn)農(nóng)民一點(diǎn)實(shí)在一點(diǎn)”遠(yuǎn)處的吳阿興是個(gè)略具面目、貌似老實(shí)的農(nóng)民。然后,作者將他放到政治的風(fēng)浪中,將他安置于一個(gè)特殊的歷史時(shí)期(20世紀(jì)70年代)搞大寨田的歷史事件中,讓他沉浮,讓他俯仰,讓人物慢慢由遠(yuǎn)而近,走向舞臺(tái)正中,在人們的眼皮底下做盡喜怒哀樂(lè),盡顯人生百態(tài)。
一個(gè)不失農(nóng)民本色的農(nóng)村基層干部形象,就這樣由模糊而清晰,由淺淡而濃厚,而終于筆立于讀者眼前:在人事興廢上的融通與權(quán)變、在劈山造田事件上讓大家填飽肚子的一根筋、在權(quán)力爭(zhēng)斗中的農(nóng)民式的善變與狡黠,在民兵營(yíng)長(zhǎng)遇難后親自從山上將尸體背回村里的篤誠(chéng),農(nóng)民的小奸小詐、小損小壞與困難當(dāng)頭、當(dāng)仁不讓的大無(wú)私、大質(zhì)樸渾然交織成一個(gè)真實(shí)、立體、可感、可觸的人物形象,使得這個(gè)名為“紅人”的人物身上可信地透著卑微,又于卑微中彰顯著不那么響亮的理想色彩,仿佛無(wú)邊沙漠中的一點(diǎn)駝鈴,斷斷續(xù)續(xù),若有若無(wú),終究跳躍著生的色彩,閃爍著靈的光輝。
然吳阿興當(dāng)“官”是有其生存悖論作引,付出自己的代價(jià)會(huì)是一種必然,且他個(gè)性很難在爾虞我詐的官場(chǎng)真正得志,他與上級(jí)永遠(yuǎn)是隔著一道鋼筋水泥墻的,盡管上級(jí)會(huì)用虛偽的表象作掩飾,所以當(dāng)他認(rèn)清楚這一點(diǎn),他的整個(gè)身心就被割裂了,因之在屢屢陷入人生的困頓而終于發(fā)瘋。作者擁有細(xì)膩、溫情、善良與愛(ài)的呵護(hù)、關(guān)照和呼應(yīng)。每當(dāng)我讀到他這我們安排的小說(shuō)結(jié)尾:“室外陽(yáng)光帶著一片暖意,這是立冬后出現(xiàn)的頭一個(gè)晴朗的好天。這樣的好天,鉆出土壤的麥苗,就會(huì)急著自搖枝葉往高放綠,不多久,江南這一片透明的原野,就會(huì)變得跟草原一樣美麗和漂亮。”這輝映成趣意境雋永的語(yǔ)詞充滿著憧憬,行文之外仍然縈繞著駝鈴的梵音,它會(huì)成為生命永恒的樂(lè)章,就像我面對(duì)春天里的第一朵花,這似錦的地方,讓我感到心曠神怡。每次讀,每次都讓我很感動(dòng)。
也許,只有他才能夠細(xì)致入微地感覺(jué)到這悲憫之中存在的美。《紅人》的本質(zhì)所鉆探和揭示的遠(yuǎn)不只是這些表象的令人觸目驚心的題材和畫(huà)面,對(duì)當(dāng)代新典型的中樞神經(jīng)還是有敲山震虎作用的,小說(shuō)可以當(dāng)作一件提案的附帶,可以說(shuō),這枚堅(jiān)果不是普通的堅(jiān)果,是山核桃,堅(jiān)硬的外殼經(jīng)過(guò)一番捶打后,是富于營(yíng)養(yǎng)的果肉。在敘事的視角上,作者揮舞著一支出入自由、仿佛跳著踢踏舞的如意筆,很快就由開(kāi)篇的旁觀者的視點(diǎn)滑入了全知視點(diǎn),一會(huì)兒鉆入“小辣椒”的內(nèi)心,一會(huì)兒深入?yún)前⑴d的內(nèi)心,一會(huì)兒又刻畫(huà)徐菊娣的內(nèi)心,敘事者變成了一個(gè)全知全能的聲音,連吳人杰的夢(mèng)都呈現(xiàn)在讀者眼前。同時(shí),作者的主觀意識(shí)也借著這個(gè)抽象的、全知全能的聲音泄露出來(lái):“人犯賤就犯在對(duì)某人抱有幻想。”“人的成長(zhǎng)有時(shí)僅在一個(gè)節(jié)骨眼上,有悖常規(guī)的荒謬的卑賤的虛空的難以言喻的,從這中間悟一悟,人就長(zhǎng)出了一節(jié)。”然后,這種過(guò)于自由的轉(zhuǎn)換有時(shí)給讀者的閱讀也會(huì)帶來(lái)一絲遺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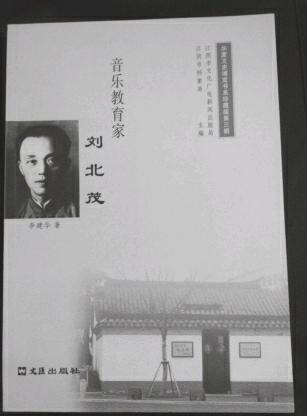
小說(shuō)開(kāi)頭描繪了一幅充滿詩(shī)情畫(huà)意的勞動(dòng)畫(huà)面,是旁觀者愛(ài)悅的眼光:“秧田基本栽完了,遠(yuǎn)遠(yuǎn)近近的田野,仿佛是丹青洇濕出的一幅意筆風(fēng)景畫(huà)……”很快,作者頓然滑入了全知全能視角:“每個(gè)人都很欣慰,為自己充當(dāng)大地畫(huà)家而自我感動(dòng)……”這種全知視角恰恰違背了審美的真實(shí),好比作者對(duì)著窗玻璃哈了一口氣,讀者看到的是窗玻璃上覆了朦朧的一層水霧,熱度卻有了。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