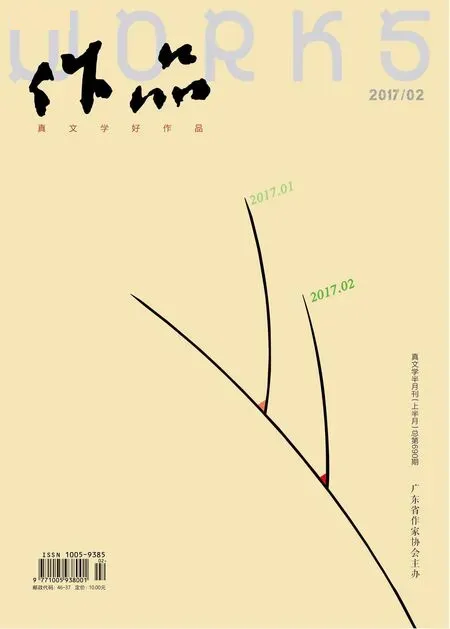吃相
文/周潔茹
吃相
文/周潔茹
周潔茹女,1976年生于江蘇常州,曾于《人民文學》 《作品》 《收獲》 《花城》 《鐘山》 《十月》等刊發表小說。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居香港。
1
車禍以后,陳小姐再也沒有來過上海。
所以我的活動在上海,我以為陳小姐是不會來的了,我知道那次車禍。
陳小姐平時都是坐在前排,就那天,去上海的那一天,她坐到了后排,她老公說的,你累了,睡一會兒,到了上海我再叫你。
陳小姐醒過來的時候滿臉是血,一根鋼筋,車頭插到車尾,座位上全是玻璃碴子和血,分不清楚是自己的還是老公的。
陳小姐喊老公的名字,沒有人應。陳小姐一眼看到自己的古馳包包,一點都沒有壞,陳小姐抖著手,摸到那只包,打出了救命的電話。
七年以后,陳小姐開著奔馳跟我講,幸虧是個美國車,要是個日本車,人就沒了。
我看著陳小姐的側面,陳小姐的側面看不到傷口,那個傷口在頭頂的另一側,頭發遮住了。我想起等待救護車的時刻,她和她老公,血淋淋的兩個人,抱在一起痛哭。一同經歷了生死的男女,他們心里面想的一定是那一句,這一輩子,我們再也不分開了。
陳小姐離婚的時候我不在,幸好我不在,一切最壞的情形。
2
七年以后了,我再見到陳小姐,陳小姐請我吃早飯。
算命師傅太不準了。我說,還說你旺夫,以后越來越好。
準。陳小姐說,就是太準了。
我是旺夫。陳小姐說,他生意越來越大。
生離死別。陳小姐說,算命師傅說的是,旺夫,但是死離生別。生離,或者死別。
那場車禍,我說。
對。陳小姐說,那場車禍,我沒死,他沒死,沒能死別,只好生離。
唉。我說,還不如死別。
是嗎?陳小姐說。
離個婚不就跟死過一次似的,我說。
你離過?陳小姐說。
跟死一樣嗎?我說。
不如死,陳小姐說。
我說奔馳是哪國的車?
陳小姐白了我一眼。
我說為什么是奔馳,那誰說的,騎自行車哭,坐奔馳笑?
陳小姐又白了我一眼,說,那是寶馬,那是寶馬好吧,寧愿坐在寶馬里哭不要坐在自行車上笑的寶馬。
我說好吧我們去吃早飯吧。陳小姐的車開出去了一段,說,土豪才開寶馬。
車停在一片仿古建筑的大門口,一個拱門,像是一個牌坊。
可以停的嗎?我問。
可以,陳小姐堅定地答。
真的可以嗎真的嗎?我又問。
可以可以可以。陳小姐說,你不要煩了好吧,什么都是可以的。
我們下了車,經過了一個名人故居,但是因為太早,門關著,我也沒有能夠進去看一眼,可是看了一眼也不會怎樣,名人都不是這里的人,他只是死在這里,這里的人對死在這里的人格外敬重,雕了像又故了居,這里的人卻對生在這里的人蔑視,很多人就跑到外面去了,死在別處。
我倆經過了名人故居,穿過了一條小巷,來到一扇木門前面。陳小姐推開門,我瞬間落到古代。一個古代院子,還有桂花樹和蓮花缸,我站在門口,不知道怎么辦才好。
進去啊進去啊,陳小姐說。
我跨進門檻,連門檻都是古代的。
坐啊坐啊,陳小姐說。
院子中央一個古代方桌,四張小板凳,我在小板凳上面坐下,那個時刻,我確實覺得板凳比沙發舒服多了。
四面八方就走出來很多人,全是年輕的男人,每一個都長得一模一樣。他們在小方桌上放下了各種各樣的吃食,又散落到院子的四面八方。
一起啊一起啊,陳小姐說。
好啊好啊,他們溫和地答。
然后就剩下陳小姐和我,搖著扇子,開始吃早飯。
你買的?我說。
買不起啊。陳小姐說,而且人也不賣啊。
我是說早飯,我說。
我可不會買。陳小姐說,他買的。
陳小姐一個眼神飛過去,我就看到一道彩虹。
實際上是,蓮花缸的那一邊,有一個正在給花花草草澆水的男人。早晨清淡的太陽光,水簾之下,就出現了一道彩虹。這個男人還穿著古代的衣服。
我可以把這個故事往架空深虐的方向講下去。我跟陳小姐在深山老林迷路,絕望得快要死了的時候,路盡頭現出一個豪宅,一個仆人拎著燈站在門口迎接,我們入到豪宅里面,真是太金碧輝煌了,連仆人們穿的衣服都是繡著花,花樣都不帶重的,我們被主人盛情款待,這位主人長得,已經無法用語言可以形容了,根本就不是地球人好吧。好吃的好看的源源不斷地端上來,再加上主人那個逆天顏值,陳小姐已經被他完全地迷住了,她一直一直地望著他,嫵媚眼神飛過去,說,彩虹。我當即驚醒,拉住陳小姐的手跳起來,我們往大門口跑,主人和仆人,一堆人在后面追,我們剛剛跑出大門,后面的豪宅轟然倒塌。我定睛一看,竟是一個巨大螞蟻窩,無數密密麻麻螞蟻舉著比自己身體還要大很多的食物,洞里洞外奔走勞碌,川流不息。再回頭看陳小姐,她已經癱軟在地,嘴里喃喃,彩虹,彩虹……
好吃嗎?陳小姐說。
我回過神來,陳小姐正舉著一塊糍粑糕。
好吃,我說。
彩虹已經不見了。穿古代衣服的男人已經澆好了花草,沒有了水,自然沒有彩虹。但是他也不走過來,他沖著我們笑了一笑,遠遠地。
他買的?我對陳小姐說,他怎么不過來吃。
他就過來了,帶著笑說,你們吃你們吃。
都是在不同的店里買的。陳小姐說,他知道哪兒的店做什么好。
他羞澀地一笑,走了。
他結婚了沒有?我說。
啊?陳小姐說。
我說他結婚了沒有。
結了,陳小姐說。
哦,我說。
3
陳小姐的奔馳幾乎停不下來,串串店實在太小了,但是她又必須要停下來,我說的,我們去吃串串吧,我以后都吃不到了。
我們就去吃串串了。
橋下面的小店,一條窄街,陳小姐的車要開過去,對面的車就開不過來。對面的車都讓她了,一聲喇叭都沒有,而且我分明地看見對面車里的男人還對她笑了一下。
你多迷人。我說,他們都讓你。
他們讓的不是我,是我的車,陳小姐冷靜地說。
我們坐在串串店,陳小姐熟練地點了一鍋串串,各種各樣的蔬菜串起來,煮熟,浸在紅油里。這種模式的食物總是令我驚嘆。
你知道嗎。離婚以后我就不能吃東西了,什么都不能吃,硬吃,就會嘔。你理解吧,陳小姐說。
理解。我點頭,我有時候吃塊餅干都會嘔,原來里面有花生,根本看不出來嘛,但是我的身體會把它吐出來,因為我對花生過敏嘛,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的身體會幫我們做決定。
我什么都不能吃。陳小姐說,我知道我快要死了。
你的身體要你死,我說。
陳小姐白了我一眼。我不想死,陳小姐說。
我喝營養液,吐掉了大部分,我還是可以活下來。陳小姐說,我爸爸死了。
我看著她。
我爸爸在我離婚的期間死了,陳小姐說。
我說對不起。
陳小姐說我也只好去死了。
我有一天傍晚出來游晃,我也許掉到河里死了,也許被車撞死了,我不知道,反正我也不在乎死不死的。
我晃來晃去,我就晃到他那兒去了。
我只是看見一條巷子,雪白的墻,我就走進巷子里面去了,然后我看見一扇木門,我知道是私人家的門,但我推開了門,我甚至沒有先敲一敲,我就直接推開了門。
我就看見了一個院子,就像你第一次見到那個院子一樣,我呆了一下,古代的房子和家具,里面的人,穿著古代的衣服,我知道我死了,我穿越了,我終于解脫了。
有什么可以幫到你的嗎?他說。
這是他的第一句話,他向我走過來,帶著笑。
我說這是哪兒?
他說進來喝一杯茶吧。帶著笑。
你就進去喝茶了?我說,你都不認識他的,你倒不怕。
我還有什么可怕的,陳小姐說。
我還有什么可失去的,陳小姐又說。
我喝了一杯茶,配茶的果子是一塊綠豆糕,是的,我記得太清楚了,綠豆糕,碧綠的亮,浸透了油紙。那是我離婚以后吃的第一口食物。
你活下來了,我說。
我活下來了,陳小姐說。
為了讓我活下來,他帶著我去了很多地方。有時候為了吃一口蔥油餅,我們會大清早就出發,開車開七八個小時,去到一個山里。
我羨慕地看著她。這家串串店也是他帶你來的?
陳小姐搖頭。沒有,陳小姐說。
我只是看到他在朋友圈貼出來這個店,我知道他會來這里,可是他從來沒有帶過我來。
可是很好吃啊。
可是就在他家家門口,他也許會帶他太太來,陳小姐說。
好吧,我說。
你還想吃什么?陳小姐說,以后都吃不到的。
我什么都想吃。我說,我什么都吃不到。
你在談戀愛吧?陳小姐說。
我說我們這個年紀的男人們都結了婚了吧,我們還有戀愛可以談?
結了好幾回了,陳小姐說。
我想吃燒烤。我說,非常想。
于是第二天傍晚,天還沒黑,陳小姐就載著我來到運河邊上。
特別熱門的燒烤店。陳小姐說,得趁著天還亮著就來占位。
車停在燒烤店的對面,我們下了車,陳小姐踩了一雙古馳高跟鞋,那雙鞋行走在一地的煙蒂和竹簽上面。
馬路邊上擺著四張塑料桌子,每一張的款式和顏色都不同,椅子也是各種各樣的,而且上面都坐滿了人,所有的椅子都在搖晃。
還是來晚了,陳小姐說,我們等等吧。
等也沒位,一個穿著圍裙的人說。
為什么?陳小姐說。
你們前面排著二十號人呢。圍裙說,等排到你們什么都沒有了。
我們可以等,陳小姐堅定地說。
圍裙手一指,那兒不給停車,會貼條的。
貼。陳小姐說,讓他們貼。
反正沒位,圍裙說。
我望了一眼桌子,每一張桌子上面都是空的。
我是老板。圍裙又說。
陳小姐帶著我回到車里,她的鞋底肯定沾滿了各種各樣地上的東西。
你就這么想吃燒烤嗎?陳小姐說。
也不是那么想吧。我說,我又沒有吃過別的。
我們去另外一家。陳小姐說,網上說郊區那邊有一家很出名的。
他沒帶你吃過燒烤?我說,你還在網上找?
沒,陳小姐說。高跟鞋踩下油門,我們出了城。
一個小時以后,我們迷路了。
我要回家,我說。
網上都是假的。陳小姐說,鄉下這一片黑燈瞎火,哪有什么燒烤。
我要回家,我說。
陳小姐送我回家。
我家樓下居然有一間燒烤店,凌晨兩點,生意還很興隆。
哎。陳小姐說,這家網上也有的,有名的。
我們就坐在了我家樓下,開始吃燒烤。
他為什么不帶你吃燒烤?我說。
他說孩子也喜歡燒烤,可是太太說臟,于是全家都不吃。
好像是不太干凈。我說,聽說韭菜從來不洗。
那你為什么還要吃?陳小姐說。
我說我去了一下建水啊,我在建水吃燒烤啊,然后我收到了一枝花。
陳小姐說你吃燒烤然后收到一枝花?
我說是啊,我們這個年紀,吃著吃著燒烤還有人送你一枝花。
陳小姐說燒烤好吃嗎?
不知道啊,我說。
玫瑰花,我又說。
4
我的活動在上海,我還以為陳小姐是不會來的了,我知道那次車禍。
可是陳小姐來了,還有他,他穿著現代的衣服,我差一點就認不出來他了。
我馬上就原諒了他們的遲到。你們對我真是太好了,我說。
他說上海這邊有個素菜館特別好,我就想來試下菜。陳小姐說,正好你也有活動,我們就彎過來一下看看你。
好了,我們走了。陳小姐說。
再坐會嘛,我說。
不了。陳小姐說,要不來不及趕回去了。
誰開的車?我說。
開什么車?陳小姐說,為什么開車?我們坐火車。
后來陳小姐帶著我在一間大酒店的日料店吃個不停的時候,我根本就想不到這個女人得過厭食癥。
是不是還能吃就代表著還能愛啊,我說。
陳小姐白了我一眼。
這家日本館子也是他帶你來的?
以前就常來。陳小姐說,跟我前面那個老公。
我不說話。
這種大家都知道的最好的日料館,陳小姐說,我們吃了不少。
我埋頭吃漬物炸物燒物,最好的日料館,真沒吃出好來,價錢肯定好。
我前面那個老公有錢嘛,陳小姐突然笑了一聲,我旺夫。
陳小姐的笑聲有點大,我看了一眼柜臺后面的壽司師傅,師傅眼眉都沒有抬一下。
他帶我去的,都是別人不知道的館子,別人也進不去。陳小姐說。
然后他們就帶著我去了一次那種,別人不知道,也進不去的館子。
其實也就是在古代院子附近的一條巷子里面,但是如果不是他們帶著我,我肯定是找不到的。
老板立在門口,也是漢服。我現在知道了,他們穿的不是古代衣服,是漢服,這種衣服肯定是比唐裝舒服,也藏得住肚子。
你也買一件穿,陳小姐說。
我還不至于吧,我說。
陳小姐白了我一眼,陳小姐穿了一件漢服。實際上她已經訂制了好幾件漢服,一個女人,又能吃,又能穿,真的可以活下去了。
老板跟我們點了點頭,我們就自己入到屋里去了。一張圓桌,大概可以坐七八個人,但是只坐了陳小姐跟我。他大概在外頭跟老板說話。
我也是才來第二次。陳小姐說,他說得帶你來這兒,這兒好,他喜歡你。
他喜歡你,我糾正她。
我又不認識他。我說,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進來了,一手一碗元麥糊粥,亮到透明的粥,確實好。
先喝點元麥糊粥。他說,這么熱的天。笑著的臉。
如果我會寫吃的就好了,好菜好肉煮成一鍋好湯,一碗米飯,再加一個生蛋,扣入湯鍋,吃得肚圓。可是我不會,菜真的是來了不少,可是我也不是很記得的了。
只是一盆石灰燉蛋和一窩雞湯,他站了起來,給陳小姐盛了燉蛋,又細細澆了一勺雞湯在上面。
這么吃才好吃,他說。
我就說了,我也不知道我為什么要說話。我說陳小姐你以前那個老公就從來沒有給你夾過一次菜。
陳小姐突然哭了。
5
然后就是中秋了,陳小姐說在院子里聚一聚,我帶上我的朋友,你帶上你的朋友。我說我還有什么朋友呢?我走了這么多年,我還有什么朋友。
穿漢服。陳小姐說,大家都要穿漢服。
我說我不去了,我沒空,真的。
我送給你一件漢服!陳小姐咬著牙說。
我被安排站在巷子口迎接,穿著漢服,我的裙子拖著地。
我是不是說過漢服比較舒服,但是系帶在胸的上面,簡直就是勒著胸口的衣服,我有點上不來氣。
你的朋友還沒來?陳小姐站在我身后。她穿了一件青色的高腰襦裙,手里一把圓扇。
我的朋友就來了,還帶著另外兩個人,我說的,多帶人,有誰帶誰,有吃的。
我的朋友就帶了他的同事,真的是把能帶的都帶了。
前男友啊?陳小姐搖著扇子說。
是啊。我的朋友說,七年前的。
結婚了嗎?陳小姐說。
結了,我說。
進來坐啊進來坐啊,陳小姐說。
月亮圓起來的時候,陳小姐跳了一支舞。我說的是,她真的跳了一支舞。月亮下面,古代的衣服。我都要哭了。
他跟我的朋友們坐在一起,四個男人,一桌。我知道陳小姐那支舞是跳給他的,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
陳小姐跳完舞,汗如雨下。
我去換件衣服,她喘著氣跟我說。
我也要去換。我說,我呼吸不上來,我都要昏過去了。
你又不吃飯了?我的朋友突然說。
我吃啊,我說。你怎么知道我不吃飯。
剛才你就沒吃。他說,你什么都沒吃。
我等會兒吃,我說。
前年那誰去你那兒旅游,你請她吃了個飯,我的朋友說。
是啊,我說。
去年那誰去你那兒旅游,你也請她吃了個飯,我的朋友說。
誰來我都請吃飯,你來我也請,我說。
可是她們回來都跟我們講,你請她們吃飯,可是你不吃飯。我的朋友說,她們說你是真的,根本就不需要吃飯。
我是神嗎?我說,我不吃飯我能活到現在嗎?
你說吃一口飯變成了非常艱難的一件事情,你說怎么辦吃不出來味道,所有的東西都沒有味道怎么辦太沒有辦法了,她們就說當橡皮吃吧不吃會死的,我的朋友說。當著另外三個男人的面。
我都要氣得炸了。
我說以后誰來我都不請他吃飯了。
你得用不吃飯會死的這個念頭來讓自己吃飯,我的朋友說。
我說你誰啊。
這有什么稀奇的。陳小姐突然說,我們都不吃飯。
不餓,陳小姐說。
另外三個男人不說話。
6
我走之前陳小姐說請我吃宵夜,運河邊上。我說我太不好意思了,我回來的那一天你就請我吃早飯。
陳小姐說你以后都吃不到了。
趁現在還能吃就吃點吧,陳小姐說。
好吧,我說。
帶上前男友。陳小姐說,七年前的。
為什么?我說。
因為這次我會帶他。陳小姐說,他從來不在晚上出來的,過了七點,微信都不回,但是這一次,他會出來。
其實就是在熱門燒烤店的隔壁,竟然有個茶館,老板把門關了,露天院子里,擺了一張長桌子。桌上全是酒,還有一盤烤串。
陳小姐說的,要吃那家的烤串,我就走過去買了拿過來。老板戴著眼鏡,穿著長衫,說話說得很慢。
我說你買得到的啊你不用排隊的嗎?
戴眼鏡的老板說不用不用,我們是鄰居嘛。
陳小姐喝醉以后,我只好拜托他送她回去,我實在弄不動她了,她靠在一堵墻上,誰都不能把她從墻上面移下來。
我跟他一起把她弄到車里,她的手抓著我的手不放。
你送我,陳小姐說。
我不會開車啊,我說。
我不要他。陳小姐說,我只要你。
你要我沒用啊。我說,我不會開車。
我不要他,陳小姐又說。
我說我也喝了酒了,你堅持要我咱倆都得撞死了。
陳小姐不松手。
他坐在方向盤的后面,對我說,我送她,你放心。
陳小姐還是抓著我的手,反復地反復地說,我不要他我不要他,不要把我交給他。
我看不出來陳小姐的臉是笑還是哭,我只好說他只是送一下你,他的車還在這兒,他還得回來開他自己的車。
陳小姐放了手,我關上了車門。
安全帶系上。我的朋友跟在我的后面說。
于是我從車窗的外面伸了我的脖子進去,給陳小姐系安全帶。
陳小姐一把扣住我的脖子。
現在好了,我的整個上半身都在車里面了。
你是故意的吧。陳小姐湊著我的耳朵一字一句,他結了婚了啊。
我是故意的。我說,結了婚又怎么樣。
我們又不是在古代。陳小姐咬牙切齒,即使他能再有個妾我也不做。
你又不是沒做過大婆。我說,有意思嗎?
7
陳小姐的車開遠了以后,我跟我的朋友說,我們也走吧,明天一早我還要趕飛機。
我的朋友說,我們往燒烤店那邊走走,我再給你買一盒烤串。
我說我不想吃。
我的朋友說,我也認得燒烤店的老板的,不用排的,馬上就能吃到,難得有你想吃的東西。
我說我不想吃。
電話響,我接了電話。陳小姐說她到家了,現在床上,他給她蓋了被子就走了。
我說還有呢?
陳小姐說沒有了,他走了。
我說還有吧。
陳小姐說好吧,他終于親了我一下,在我的臉頰上,他說好好過。
我說好吧。
你肯定是不回來的了,我認得了一個女孩,就同她結了婚,我的朋友說。
結婚好啊。我關了電話,說,好好過。
可是我也舍不得你。我的朋友說,我也想要你。
我看著他。
要是在古代多好,他說。
(責編: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