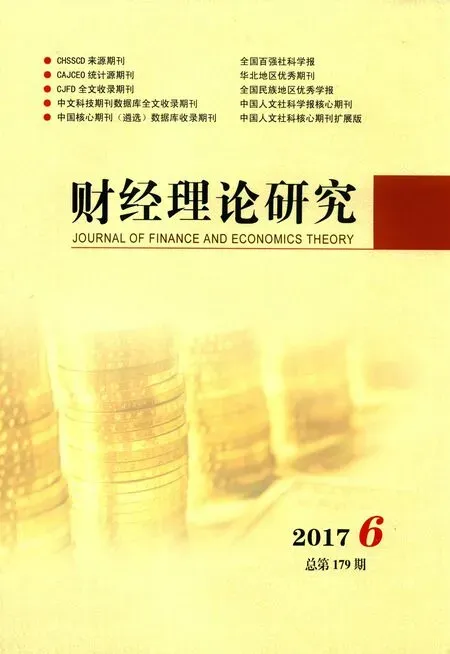我國土地財政的原因及轉(zhuǎn)型路徑分析
經(jīng)庭如,姚 悅
(安徽財經(jīng)大學 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安徽 蚌埠 233000)
我國土地財政的原因及轉(zhuǎn)型路徑分析
經(jīng)庭如,姚 悅
(安徽財經(jīng)大學 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安徽 蚌埠 233000)
由于土地征地制度形成的政府土地管制與壟斷,土地財政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逐漸上升。雖然土地財政為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建設(shè)城市基礎(chǔ)公共設(shè)施、彌補財政缺口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杠桿作用,中國住房化、城鎮(zhèn)化的快速發(fā)展也離不開土地財政,但是隨著土地財政帶來土地性質(zhì)的改變、政府金融風險的加劇、GPD考核機制的扭曲等等問題以及隨著土地成本日漸上升和征收制度的日漸規(guī)范,土地財政逐漸走向了“后土地財政時代”。以此提出相應(yīng)的轉(zhuǎn)型路徑:首先應(yīng)改進農(nóng)地征用機制,完善行政考核體系;其次分地區(qū)差異化進行土地年租制;最后穩(wěn)步推進房地產(chǎn)稅。
土地財政;分稅制改革;土地年租制;房地產(chǎn)稅
一、引言
2017年2月28日中央財經(jīng)領(lǐng)導(dǎo)小組第十五次會議上正式強調(diào)“房子是用來住得,不是用來炒的”,于是一場針對土地、房地產(chǎn)的改革被賦予了新的意義。4月1日,承擔著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經(jīng)濟密集地區(qū)、優(yōu)化開發(fā)新模式、調(diào)整優(yōu)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間結(jié)構(gòu)的河北雄安新區(qū)正式設(shè)立。5月9日,河北省國土資源廳強調(diào)雄安新區(qū)要一改往日傳統(tǒng)的土地財政路線,嚴格控制房地產(chǎn)市場,積極開創(chuàng)新的土地開發(fā)模式。6月1日,財政部、國土資源部聯(lián)合發(fā)布《地方政府土地儲備專項債券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辦法》中指出土地專項債券要從土地儲備和當?shù)卣Y金周轉(zhuǎn)實際使用情況出發(fā),依據(jù)當?shù)卣椖康耐恋厝谫Y需求,土地收入對應(yīng)納入政府性基金預(yù)算管理中。《辦法》強調(diào)此項專項債券必須嚴格保證當?shù)卣蟹€(wěn)定且充足的預(yù)期償債資金來源以及能夠平衡收益和融資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對于《辦法》的實施,國內(nèi)不少學者都認為發(fā)行土地儲備專項債券有利于規(guī)范地方債務(wù)同時可以打破土地財政的局限,為其轉(zhuǎn)型帶來新的途徑。新的改革必然帶來新的面貌,但值得深思的是,為什么曾被賦予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發(fā)動機”和“加速器”的土地財政,近幾年會飽受爭議?
二、“土地財政”的內(nèi)涵
首先,“土地財政”并不是一個正式的學術(shù)概念,而是在我國土地出讓帶來大量政府利潤的基礎(chǔ)上,對土地帶來的經(jīng)濟收入總結(jié)出的一種經(jīng)濟現(xiàn)象[1]。其次,“土地財政”的內(nèi)涵一般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政府通過出讓當?shù)赝恋厥褂脵?quán)獲取的土地出讓金;二是政府對土地和房屋征收的土地增值稅、土地使用稅、房產(chǎn)稅、契稅等直接稅收收入以及建筑業(yè)和房地產(chǎn)業(yè)相關(guān)的間接稅如營業(yè)稅;三是政府依靠土地為信用憑證的融資性收入。近十多年來,土地與政府的利益鏈成為眾多學者研究的熱點,甚至一度被認為是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從稅收的角度來說,“土地財政”就是地方政府利用稅收的無償性、強制性來滿足政府財政需要的一種法律手段;從土地出讓金角度來說,“土地財政”就是地方政府以土地使用權(quán)作為租賃品租給土地使用者,一次性收取租賃費用作為擴充自身財政空間的一種商品行為;以土地融資的角度來說,“土地財政”是地方政府以土地資源作為信用工具將政府資金進行資本運轉(zhuǎn)并獲得預(yù)算外收入,增加可支配財政資源,增強土地支配能力的一種融資行為。最后,究其本質(zhì),“土地財政”本身就是在中國經(jīng)濟轉(zhuǎn)型時期,以政府為主體圍繞土地所進行的一種財政收支活動和利益分配關(guān)系[2]。
三、“土地財政”的成因
關(guān)于“土地財政”的成因,國內(nèi)學者大多有以下三種共識:
一是“財政壓力說”,即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造成的地方財權(quán)與事權(quán)不匹配,地方政府收入小于支出的現(xiàn)象日漸嚴重,加重了地方財政壓力,迫使地方政府“以地生財”。盧洪友(2011)[3]通過分析2005-2007年中國地市一級數(shù)據(jù),以土地出讓金收入作為衡量土地財政行為的指標,以城市人均道路面積和城市擁有的公共汽車數(shù)來衡量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以城市教師數(shù)和在校學生數(shù)作為衡量教育的指標,以擁有的床位數(shù)和醫(yī)生數(shù)作為衡量醫(yī)療水平指標,用人均擁有綠地面積和綠地覆蓋率來衡量城市環(huán)境。通過實證發(fā)現(xiàn)中國地市財政分權(quán)與政府出讓土地模式呈現(xiàn)正向關(guān)系,且結(jié)果通過顯著性和穩(wěn)健性。另外,盧洪友認為政府采取出讓土地獲取收入的方式實則是一種無奈之舉。王克強(2012)[4]運用動態(tài)效應(yīng)和閾值分析認為事權(quán)與財權(quán)的不平衡會導(dǎo)致地方土地財政的增長,且當財權(quán)事權(quán)不平衡的程度越高,地方財政壓力越大,土地收入規(guī)模也越大,但是實證中并未解釋為什么對發(fā)達地區(qū)增加補助也并不能減少土地財政規(guī)模的原因。雷瀟雨(2014)[5]認為分稅制改革極大地改變了地方政府的財政行為,隨著財權(quán)上移,各種預(yù)算外收入成為解決地方財政的主要來源,由于土地帶來的利潤直接且迅速,當?shù)卣终莆罩型恋爻鲎尳穑酥?土地帶來的附加利益使得地方政府越來越依賴土地財政,因此認為分稅制改革帶來的收支緊缺才是一切的開始。錢忠好、牟燕(2017)[6]認為現(xiàn)行土地財政來源于財政分權(quán),導(dǎo)致各級地方政府紛紛采用“低價征地,高價賣地”來快速獲取相應(yīng)的收入和稅費,從而也造成了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
二是由于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考核制度,官員的晉升制度誘使地方政府官員“以地升官”。李勇剛(2013)[7]以1999-2010年31個省市數(shù)據(jù)構(gòu)建面板聯(lián)立模型,實證分析認為政府的激勵機制對土地財政具有雙向推動作用,激勵機制造成政府需要更多的財政資金發(fā)展公共建設(shè),而出讓土地有利于政府吸引更多的投資者進行土地投資。另外,晉升激勵具有明顯的地方性差異,其中中西部明顯大于東部地區(qū)。范子英(2015)[8]以財政壓力的變化新角度來實證分析財政壓力的變化與政府土地出讓行為的變化,通過實證分析認為分稅制改革事實上并沒有增加地方財政壓力,地方通過出讓土地所獲取的財政收入也沒有直接用于彌補財政收支缺口,因此,認為土地財政其實是一種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楊其靜(2016)[9]通過整理2007-2011年中國土地市場上每宗工業(yè)用地出讓結(jié)果信息分析得出地方晉升競爭是導(dǎo)致土地財政的主要原因,城市土地投資的規(guī)模與市委任職期限呈倒U型,且經(jīng)濟實力相近的城市之間會出現(xiàn)土地競爭的模仿。王梅婷(2017)[10]通過分析2008-2013年262個地級市的土地出讓行為和官員晉升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雖然財政分權(quán)和晉升機制都會影響土地出讓行為,但是晉升機制的顯著程度遠遠大于財政分權(quán),另外發(fā)現(xiàn)當?shù)卣巴恋囟愂占睢毙袨檫h遠大于“土地財政激勵”行為。
三是我國自身的土地制度,即現(xiàn)有土地的征收制度和壟斷,從而刺激地方政府“以地控權(quán)”。陶然(2010)[11]通過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實際中政府常常擁有“公共利益”之外的用地權(quán),在批準工業(yè)用地和商業(yè)開發(fā)的部分項目上政府擁有絕對的控制權(quán),壟斷著土地一級市場才是土地財政迅速暴漲的原因。另外政府對土地的收益并不是依賴采用低價出讓土地的方式而是招商引資后的相關(guān)稅費。錢忠好(2015)[12]分析將中國農(nóng)村土地非農(nóng)化的唯一途徑就是政府征收或征用,變?yōu)閲型恋睾蟛拍茉谕恋厥袌霭l(fā)揮土地價值。計算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在中國不斷加大征地制度改革力度的同時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卻下降了10個百分點。另外,他認為政府采取土地財政是財政體制和政績考核下的理性選擇,因為征收制度為其創(chuàng)造了所有可能。鄧蓉(2017)[13]通過對西部某試點縣近三年的財政收支、土地要素和征地制度的討論,認為現(xiàn)行的征地制度對縣域等不發(fā)達地區(qū)的土地財政影響更為明顯,征地制度與縣域地方財政的矛盾突出使得土地出讓金等快捷直接的收入成為縣域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而縣域政府手中對土地的絕對權(quán)也成為最優(yōu)先的方式。王慶鵬(2017)[14]認為我國土地征收制度的監(jiān)管和查處力度不夠,根據(jù)國辦發(fā)50號文件,對于地方政府土地違法行為僅僅是采用提出糾正整改意見,而不是直接查處,無形中助長了地方政府權(quán)力的濫用,為了獲得更多的財政收益,依賴土地融資的動機就越強烈。
綜上所述,土地財政的成因主要有分稅制、晉升激勵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等,但經(jīng)濟發(fā)展問題的復(fù)雜性不僅來自于多元化的影響因素和其中緊密的關(guān)聯(lián)性,更是來自于真實經(jīng)濟情況的差異性和現(xiàn)實性,筆者并不認為上述三個原因是獨立分開的。
四、“土地財政”的現(xiàn)狀
(一)土地出讓金收入高速增長
根據(jù)前人學者的經(jīng)驗,我國常常以預(yù)算內(nèi)財政缺口指標衡量土地財政,即(預(yù)算內(nèi)支出-預(yù)算內(nèi)收入)/預(yù)算內(nèi)收入,預(yù)算缺口指標為負,即預(yù)算內(nèi)收入大于預(yù)算內(nèi)支出,反之為正即預(yù)算內(nèi)支出大于預(yù)算內(nèi)收入。我國分稅制改革開始于1994年,因此選取數(shù)據(jù)從分稅制改革后,如圖1所示:1993年我國地方財政缺口為-0.02,即此時預(yù)算內(nèi)收入大于預(yù)算內(nèi)支出,此時的土地財政收入為557.8億元。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地方財政缺口迅速上升到0.75,即預(yù)算內(nèi)支出大于預(yù)算內(nèi)收入,短短一年,地方財政壓力上升38.5%,土地出讓收入639億元,占同年地方收入28%,同比去年上升12%。對比圖1圖2可知,雖然地方財政壓力在1994年到1997年持續(xù)下降,但此時土地出讓金收入呈現(xiàn)逐年遞減的形式,也就是說至少在1994-1997年之間地方財政壓力并沒有產(chǎn)生明顯的土地財政行為。直到1998年我國開始實施住房制改革,地方財政壓力基本呈現(xiàn)一個上升趨勢,并在2002年達到第一個峰值,之后的四年,地方財政壓力逐漸放緩,直至受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地方財政壓力逐漸上升在2009年達到第二個峰值,隨之持續(xù)下降,直到2014年以后,中國進入新常態(tài)發(fā)展階段,新的財政壓力再次出現(xiàn)。土地出讓金從1998年后開始有明顯的上升趨勢,此后土地出讓金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比重即土地財政依賴值也在逐年遞增,最高曾超過地方預(yù)算收入的50%,達到68%,成為名副其實的地方“第二財政”。期間國家曾于2005年調(diào)控房地產(chǎn)市場,因此土地出讓金有明顯下降趨勢,但2006年后迅速反彈達到第一個峰值,2010年達到第二個峰值,隨之2013年達到近二十年最大峰值。雖然土地財政行為和地方財政壓力在時間上大部分相符合,但從圖1可知,排除國家調(diào)控房地產(chǎn)熱和金融危機兩個特殊時點,2003-2007年、2010-2014年地方財政缺口明顯下降的同時,土地出讓金收入并沒有因此下降,因此1994年分稅制改革所造成的地方財政壓力可以解釋部分土地財政的原因,但不能完全解釋土地財政的原因。

圖1 1993-2016年地方土地出讓金與財政缺口趨勢圖數(shù)據(jù)來源:中國國土資源部、中國統(tǒng)計年鑒.

圖2 1993-2016年地方土地出讓金收入與土地財政依賴趨勢圖數(shù)據(jù)來源:中國國土資源部、中國統(tǒng)計年鑒.
(二)土地相關(guān)稅收明顯增加
構(gòu)成土地財政收入的直接稅種有土地增值稅、耕地占用稅、房產(chǎn)稅、契稅、城鎮(zhèn)土地使用稅五種直接稅和房地產(chǎn)業(yè)與建筑業(yè)的間接稅如營業(yè)稅。關(guān)于五種直接稅,由圖3可知,土地相關(guān)的五種直接稅收收入逐年上升,占地方財政比重也呈現(xiàn)統(tǒng)一的上升趨勢。近年來,契稅和土地增值稅占土地稅收收入的比重越來越大,從1999-2016年分別增長3.23%和4.82%,而房產(chǎn)稅則從1999年的3.3%下降到2016年的2.55%。十七年里,五種與土地相關(guān)的稅收總和從1999年只占地方財政收入的6.8%上升至2016年占地方預(yù)算內(nèi)收入的17.23%,稅收總和在十七年里增長了39倍。究其原因,可以理解為政府通過低價出讓土地所帶來的招商引資,以另外一種滯后的土地利潤形式反映出來。另外,圖3中2007年有明顯特殊性,查閱相關(guān)資料后得知,2007年我國曾發(fā)布國稅函(2007)544號文件,文件中強調(diào)將土地增值稅作為重點稅源戶進行監(jiān)控調(diào)查以此規(guī)范房地產(chǎn)市場。關(guān)于間接與土地有關(guān)的稅費,截至2016年,有關(guān)房地產(chǎn)業(yè)和建筑業(yè)稅收收入約占地方預(yù)算收入的40%[15]。隨著營改增的完善,有關(guān)這兩部分的稅收必然會有新的調(diào)整。
(三)土地出讓行為日漸規(guī)范
1994年我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chǎn)管理法》,正式明確可以采取拍賣、招標和雙方協(xié)議的形式來出讓土地使用權(quán),法律為土地使用權(quán)的合法性提供了保障。由圖4可知,我國從2000-2016年,以招掛拍的形式出讓土地基本上呈現(xiàn)一種高速增長的態(tài)勢,尤其在2008年之后,土地出讓面積急速上升,政府依靠招拍掛行使土地使用權(quán)的比重也逐年上升,從而獲取大量的土地出讓金收入來擴充財政收入。一方面法律賦予了政府行使的權(quán)力但另一方面也助長了政府濫用土地的可能性。按照協(xié)議出讓土地的行為滋生了大量“尋租”、“暗箱操作”等各種非法占用、轉(zhuǎn)讓、出租、抵押和準變土地用途的行為。由圖5可知,2000年政府違法用地行為達到18.5萬件,取得罰沒收入8.6億元。之后的兩年雖然明顯下降,但2003年再度急速上升17.8萬件,取得罰沒收入12.2億元。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政府違法建設(shè)用地的行為呈明顯上升趨勢,截至2016年,共取得罰沒收入325.13億元。值得欣慰的是,國家對于土地的重視程度越來越明顯,查處力度越來越大。近幾年先后頒布《國土資源行政處罰辦法》、《節(jié)約集約利用土地規(guī)定》、《土地利用計劃管理辦法》等多部切實有效的法律法規(guī)來規(guī)范地方政府對土地的使用權(quán)利。2016年,查處違法案件7.4萬件,同比下降16.85%,其中關(guān)于行政征收違法行為只有9.9%。

圖4 2000-2016年土地出讓面積、招拍掛面積、招拍掛/出讓面積趨勢圖數(shù)據(jù)來源:中國國土資源部.

圖5 2000-2016年土地罰沒收入與違法案件趨勢圖數(shù)據(jù)來源:中國國土資源部.
五、“土地財政”帶來的影響
任何經(jīng)濟問題的存在都有其歷史價值,“土地財政”在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過程中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必然有其歷史貢獻,同樣,也必然有其歷史階段性。因此本文從正反兩個方面客觀討論“土地財政”帶來的影響。
(一)土地財政帶來的積極影響
1.土地財政帶來了巨大的融資力
土地財政中地方政府采取高地價出售經(jīng)營性用地,低地價出售工業(yè)用地,通過招拍掛甚至低價尋租的方式來吸引外商,漸漸形成了“經(jīng)營城市+招商引資”的城市發(fā)展模式。必須承認,土地財政曾經(jīng)的融資能力為地方政府切實地彌補了大部分財政缺口。雖然土地財政被詬病已久,但是依賴土地財政獲得的融資性收入切切實實地以城市基礎(chǔ)公共建設(shè)、醫(yī)療衛(wèi)生等存量資產(chǎn)存在并繼續(xù)為現(xiàn)今政府使用著。更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對于地方產(chǎn)業(yè)建設(shè)的扶持從最初的免稅、減稅到現(xiàn)今直接融資和優(yōu)惠,所依賴的大部分建設(shè)資金都是來源于土地的融資收益和稅收收入,其中有一部分稅收收入也是建立在當?shù)赜凶銐蚨嗟钠髽I(yè)和保證企業(yè)有充足利潤的基礎(chǔ)上,而吸引這些企業(yè)來地方發(fā)展的原因,土地的經(jīng)濟性起了決定性作用。回顧地方發(fā)展,土地所帶來的融資性比所有廉價的勞動力都來得直接而長遠,根據(jù)杜雪君[15]的實證分析,土地財政的收益提升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對固定資產(chǎn)投資和經(jīng)濟建設(shè)起到了不可否認的正向作用。而辛波[16]也證明了雖然GDP不是土地財政收入的格蘭杰成因,但土地財政收入?yún)s是GDP的格蘭杰結(jié)果。
2.稅收的高速增長
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強調(diào)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chǔ)和重要支柱,而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對比其他稅收的征收形式,出售土地所帶來的外溢損失小、交易成本低且邊際效益高,最重要的是利益程度遠遠高于其他稅收收入。根據(jù)圖5可知,近十幾年來,依靠土地財政所帶來的土地相關(guān)稅收都在逐年增加,土地直接的相關(guān)稅收尤其是土地增值稅,受房地產(chǎn)市場的影響,年均增長率超過50%。不僅如此,我國其他主體稅種也大幅度增加。根據(jù)2016年中國統(tǒng)計年鑒的數(shù)據(jù)顯示,2016年各項稅收總和比1999年增加了119671.42億元。其中以增值稅、企業(yè)所得稅、消費稅和營業(yè)稅為例,2016年的稅收分別比1999年增長了10.5%、12.45%、6.89%和35.56%。2016年固定資產(chǎn)投資596501億元,而來自地方項目有571337億元,占總投資的95.78%。通過土地所帶來的利潤不僅融資基礎(chǔ)設(shè)施更是使資本重新回流到公共基礎(chǔ)建設(shè)中,促進了產(chǎn)業(yè)快速成長,相應(yīng)的其他稅收也隨之上漲,因此政府依賴土地財政所帶來的后續(xù)財政收入遠遠高于了期初出售土地的價格。
(二)土地財政帶來的消極影響
1.土地變?yōu)橥顿Y品
由上述分析可知,地方政府近幾年來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程度越來越明顯,土地出讓金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也越來越大。政府對待土地的手段帶有明顯計劃經(jīng)濟的色彩,手中的權(quán)力使得房地產(chǎn)市場漸漸走向一種病態(tài)的發(fā)展。1998年開始停止住房實物分配,房價單價上漲至2000元,2004后全國平均房價開始從3000元迅速上漲,同比暴漲18.7%,2007年同比上漲16.9%,2008年同比下降1.9%,2009年同比上漲22.4%,直至2016年漲至11816元。根據(jù)數(shù)據(jù)顯示,截至2017年4月,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的房價也都在50000元以上,對比1998年房價增長了接近600%,土地成了名副其實的投資品。大量文獻證明地方政府往往可以成為推動房價上升的內(nèi)在激勵。當土地變?yōu)橥顿Y品,必然會出現(xiàn)明顯的貧富差距,經(jīng)濟條件好的投資房地產(chǎn)催升價格上漲獲得盈利繼續(xù)循環(huán)投資,沒有條件的在負擔巨額房債之后嚴重加劇經(jīng)濟負擔,貧富差距就在房價中越來越明顯。同時,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和有限性,理應(yīng)最大效率的使用,但是由于目前土地批租監(jiān)管制度仍不完善,地方追求短期經(jīng)濟利益的最大化,缺乏對土地合理科學的規(guī)劃,造成土地粗放利用和閑置。
2.加劇了金融風險的可能性
首先我們應(yīng)明確債務(wù)并不是不好的,適當合理的政府債務(wù)有利于吸引外來投資者,帶動當?shù)亟?jīng)濟發(fā)展,因此不能一味地強調(diào)避免地方債務(wù),但是要控制在一個合理科學的范圍內(nèi)。截至2016年末,我國地方債務(wù)為17.18萬億元,同比增長1.8萬億。地方政府債務(wù)率為89.2%,占全國債務(wù)60%,占GDP的比重為24%,東部地區(qū)債務(wù)規(guī)模為84954.07億元,占全國債務(wù)的47.5%,中部地區(qū)債務(wù)規(guī)模為42204.8億元,占全國債務(wù)的23.6%,西部地區(qū)債務(wù)規(guī)模為28.7%。根據(jù)第32號公告可知,地方政府債務(wù)主要集中在市級層面,國內(nèi)負有償還債務(wù)責任的地方層級差別大。經(jīng)濟不發(fā)達的省份多為省級負債比,而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多以區(qū)縣負債比為主。2016年11月,國務(wù)院發(fā)布《關(guān)于印發(fā)〈地方政府性債務(wù)風險應(yīng)急處置預(yù)案〉》,預(yù)案中強調(diào)“地方政府對其舉債的債務(wù)負有償還責任,中央實行不救助原則”。在中國城市化的高速發(fā)展中,地方政府依賴土地成為融資手段已經(jīng)成為一種常態(tài),而政府依賴土地還款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地方政府對經(jīng)營性用地的財政收入情況,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極大加劇了地方政府的金融風險最終也將上升至整個國家的金融風險。
3.破壞了GDP考核體系
官員的考核機制往往是在任職期間通過政績來進行選拔篩選,傳統(tǒng)文獻中認為地方政府官員想要在有限的收入里進行最大化的經(jīng)濟建設(shè),常常會更加依賴土地財政,通過土地獲得短期任職的效益,以此來進行公共基礎(chǔ)建設(shè)。但思考土地的經(jīng)濟性,能夠成為投資開發(fā)招商引資的土地必然有其優(yōu)良的自然資源和地理因素,而某些偏遠地區(qū)因為地勢崎嶇不平的天然劣勢,使得土地的開發(fā)利用程度低,地方政府的升遷率也相對較低。相關(guān)文獻實證顯示,城市建設(shè)和土地發(fā)展的支出往往與官員任期的前一年呈顯著正向關(guān)系,同時,土地出讓金的增加在官員任期的第一年也呈明顯同步關(guān)系。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官員的晉升機制很大程度上在于其能否在任職期間產(chǎn)生足夠的土地收入,扭曲的考核體制無形中增加了地方政府“面子工程”和腐敗問題。另外,地方政府往往更愿意選擇見效快的城市公共基礎(chǔ)建設(shè)而放棄公共教育文化和醫(yī)療的長遠建設(sh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地區(qū)發(fā)展不平衡和人文建設(shè)的缺失。
六、“土地財政”的轉(zhuǎn)型分析
隨著中國進入新常態(tài)發(fā)展階段,“改革”成了未來幾年內(nèi)的關(guān)鍵詞。盡管土地財政對我國住房化、城鎮(zhèn)化、住房商品化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杠桿作用,為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建設(shè)城市基礎(chǔ)公共設(shè)施,彌補財政缺口同樣發(fā)揮了不可否定的作用,但是隨著土地成本日漸上升和征收制度的日漸規(guī)范以及可出售的土地越來越少,土地財政逐漸走向了“后土地財政時代”[17],正如趙燕青(2014)[18]所說“融資性土地財政已經(jīng)完成了其歷史使命,土地財政的轉(zhuǎn)型已是改革發(fā)展的必經(jīng)之路”。
1.改進農(nóng)地征用機制,完善行政考核體系
土地財政本身就是圍繞著土地展開,而土地本身具有公共性。我國的基本國情就是土地實行國家所有與集體所有,農(nóng)業(yè)用地、工業(yè)用地和商業(yè)用地之間不可隨意轉(zhuǎn)換。同時我國《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規(guī)明確規(guī)定我國國有土地有地方政府具體管理,而集體土地要想進入土地市場必須由當?shù)卣日魇諡閲型恋兀簿褪钦f集體土地的產(chǎn)權(quán)如使用權(quán)、經(jīng)營權(quán)、租賃權(quán)、轉(zhuǎn)讓權(quán)等多種產(chǎn)權(quán)的形式是直接掌握在當?shù)卣氖种校由系胤脚で目己藱C制,這才是我國土地財政形成的真正原因。根據(jù)巴澤爾的產(chǎn)權(quán)公共理論分析,任何沒有被界定清楚的產(chǎn)權(quán)本質(zhì)就是公共產(chǎn)權(quán),而公共產(chǎn)權(quán)的直接歸屬者很大程度受益于政府。在我國,農(nóng)村土地的所有權(quán)歸農(nóng)村集體所有,從農(nóng)業(yè)用地到非農(nóng)業(yè)用地征的地權(quán)歸政府所有,即地方政府壟斷著城市土地供應(yīng),因此,應(yīng)明確農(nóng)地征用機制。首先應(yīng)以法律的形式正式保證農(nóng)村集體土地與國有土地享有同樣的財產(chǎn)權(quán)利,其次公開征地程序便于民眾監(jiān)督,科學制定征地補償標準,改進一次性補貼的征收方式,最后完善行政考核機制,真正落實《決定》精神,建設(shè)城鄉(xiāng)統(tǒng)一的建設(shè)用地市場,使農(nóng)村集體土地平等入市。
2.分地區(qū)差異化進行土地年租制
由于官員考核機制的扭曲,前任政府以廉價土地出讓金一次性出售土地提前透支后任政府的土地的行為已屢見不鮮。因此,可以將一次性收取的費用改成“年租制”,即每年收取一次。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和保值性,土地在未來的經(jīng)濟價值一定遠遠大于現(xiàn)在。將一次性的收入分攤到未來的幾十年,不僅可以遏制地方政府扭曲的賣地行為,從根本上改變地方政府依賴土地“寅吃卯糧”的行為,科學地約束每一屆政府的土地權(quán)利和短期化發(fā)展,更可以將土地更高效,更具有經(jīng)濟效應(yīng)的使用起來。另外,由于土地的年租制,要求地方政府更合理的使用土地,降低了未來的購房門檻,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房地產(chǎn)市場的投機熱,使得房屋可以逐步回到原有的價值和作用上。但值得注意的是,國內(nèi)眾多文獻已經(jīng)證明在我國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由于土地具有較高的商業(yè)和經(jīng)濟價值,往往更具有商業(yè)融資力,也更容易獲得房地產(chǎn)相關(guān)稅費,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程度遠遠高于經(jīng)濟不發(fā)達地區(qū)。因此,在實行土地年租制時,應(yīng)區(qū)別不同經(jīng)濟水平的城市來差異化實施,相對發(fā)達的地區(qū)嚴格控制土地出讓制度,而相對落后的地區(qū),由于地方經(jīng)濟受限,采取相對寬松且合理的年租制。
3.穩(wěn)步推進房地產(chǎn)稅
首先應(yīng)明確,十三屆三中全會中已經(jīng)將“房產(chǎn)稅”改為“房地產(chǎn)稅”,并提出“加快房地產(chǎn)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其次房地產(chǎn)稅是包含房產(chǎn)稅、土地增值稅、耕地占用稅、契稅等與土地息息相關(guān)的綜合稅種,房地產(chǎn)稅的改革將是一場有關(guān)于土地的系統(tǒng)性改革。最后參照發(fā)達國家稅制經(jīng)驗,發(fā)達國家的房產(chǎn)稅歸屬于地方政府,是地方政府主體稅種,往往占地方財政收入50%-80%。國內(nèi)眾多學者關(guān)于房地產(chǎn)稅可以成為地方主體稅種的討論已有很多。從特征來說,房地產(chǎn)稅具有穩(wěn)定、征收成本低、不易轉(zhuǎn)嫁等特性,可以穩(wěn)定地擴充地方財政收入的同時還可以完善中國稅制體系;從產(chǎn)業(yè)效應(yīng)來說,政府在獲得房地產(chǎn)稅稅收收入后可以更集中財力發(fā)展當?shù)亟?jīng)濟建設(shè),完善當?shù)毓卜?wù),將財政重心轉(zhuǎn)移到產(chǎn)業(yè)扶持和優(yōu)化投資機制;從經(jīng)濟效應(yīng)來說,房地產(chǎn)稅可以更好地引導(dǎo)房地產(chǎn)市場,改善房地產(chǎn)的投機熱,逐步實現(xiàn)“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雖然房地產(chǎn)稅可以成為地方政府長期且穩(wěn)定的稅源,但是在中國土地并非私有制的國情下,開征房地產(chǎn)稅的難度重重,切不可操之過急。首先明確房地產(chǎn)稅開征的主要目的,其次合理確定房地產(chǎn)稅的征收對象并適時推出科學的法律法規(guī),最后應(yīng)及時完善房地產(chǎn)市場監(jiān)管信息。
[1] 劉尚希.正確認識“土地財政”[EB/OL].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diaochayanjiu/201505/t20150501_1226052.html,2015-5-1.
[2] 王玉波.土地財政的成因與效應(yīng)及改革研究綜述[J].經(jīng)濟問題探索,2013,(2):150-155.
[3] 盧洪友,袁光平,陳思霞,等.土地財政根源:“競爭沖動”還是“無奈之舉”?——來自中國地市的經(jīng)驗證據(jù)[J].經(jīng)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1):88-98.
[4] 王克強,胡海生,劉紅梅.中國地方土地財政收入增長影響因素實證研究——基于1995-2008年中國省際面板數(shù)據(jù)的分析[J].財經(jīng)研究,2012,(4):113-123.
[5] 雷瀟雨,龔六堂.基于土地出讓的工業(yè)化與城鎮(zhèn)化[J].管理世界,2014,(9):29-41.
[6] 錢忠好,牟燕.中國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市場化改革為何舉步維艱——基于地方政府土地財政依賴視角的分析[J]. 農(nóng)業(yè)技術(shù)經(jīng)濟,2017,(1):18-27.
[7] 李勇剛,高波,許春招.晉升激勵、土地財政與經(jīng)濟增長的區(qū)域差異——基于面板數(shù)據(jù)聯(lián)立方程的估計[J].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研究,2013,(1):100-110.
[8] 范子英.土地財政的根源:財政壓力還是投資沖動[J].黨政視野,2016,(2):58-58.
[9] 楊其靜,彭艷瓊.晉升競爭與工業(yè)用地出讓——基于2007~2011年中國城市面板數(shù)據(jù)的分析[J].社會科學文摘,2016,(1):5-17.
[10] 王梅婷,張清勇.財政分權(quán)、晉升激勵與差異化土地出讓——基于地級市面板數(shù)據(jù)的實證研究[J].中央財經(jīng)大學學報,2017,(1):70-80.
[11] 陶然,汪暉.中國尚未完成之轉(zhuǎn)型中的土地制度改革:挑戰(zhàn)與出路[J]. 國際經(jīng)濟評論,2010,(2):93-123.
[12] 錢忠好,牟燕.征地制度、土地財政與中國土地市場化改革[J].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問題,2015,(8):8-12.
[13] 鄧蓉.征地制度改革對縣域財政的影響分析及其思考——以西部某試點縣為例[J].理論與改革,2017,(1):26-32.
[14] 王慶鵬,李軍.淺析現(xiàn)今土地管理之土地執(zhí)法所面臨的問題與對策[J].科學與財富,2017,(7).
[15] 杜雪君,黃忠華.以地謀發(fā)展:土地出讓與經(jīng)濟增長的實證研究[J].中國土地科學,2015,(7):40-47.
[16] 辛波,于淑俐.對土地財政與地方經(jīng)濟增長相關(guān)性的探討[J].當代財經(jīng),2010,(1):43-47.
[17] 郭家虎,崔文娟.我國土地財政的發(fā)展現(xiàn)狀、形成根源與轉(zhuǎn)型路徑[J].中共南京市委黨校學報,2016,(2):61-66.
[18] 趙燕菁.土地財政:歷史、邏輯與抉擇[J].城市發(fā)展研究,2014,(1):1-13.
[責任編輯:張曉娟]
AnalysisoftheCausesandTransformationofLandFinance
JING Ting-ru,YAO Yue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00,China)
Du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land expropriation system, government could control and monopoly land, land finance accounting for the local fiscal revenue increased gradually. The land finance had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public infrastructure, making up the financial gap for local government investmen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China housing also cannot do without the land finance, but with the land finance changed the nature of the land, the government increased financial risk, GPD assessment mechanism and so on and the distorted cost of land expropriation system is increasing and regulate land finance gradually "the end of land finance" era.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transformation path: first of all, should improve the land expropriation system, perfect the administrative evaluation system; secondly regional difference of land rent system; finally, steadily promote the real estate tax.
land finance;the tax sharing system reform;land rent system;real estate tax
2017-07-04
安徽財經(jīng)大學研究生科研創(chuàng)新基金項目(ACYC2016002)
經(jīng)庭如(1965-),男,安徽金寨人,安徽財經(jīng)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從事中國稅制改革研究.
F812.2
A
2095-5863(2017)06-005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