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畫的對話
孫克
關于中國畫的對話
孫克
馬春梅:您經歷了“中國畫改造論”提出并施行的主要階段,您怎么看待這一段歷史?
孫克:“中國畫改造論”的提法,應是康有為較早明確提出的。康有為當時作為改良派的政治活動家,從改良的角度提出這個想法的。百日維新失敗后,康有為在歐洲看到西方藝術很真實、寫實,覺得中國畫脫離現實,認為中國畫衰落得很,覺得中國畫需要改造。這種改造的思想是對照西方的狀態來看中國畫,在他的《萬木草堂藏畫目》序言中,崇宋畫,貶元畫,否清畫,他的理想是:“他日當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國人豈無英絕之士應運而興,合中西而為畫學新紀元者,其在今乎?”他的想法很明確,中國畫的出路,必須中西結合。
改造中國畫不僅僅是康有為一個或幾個人的看法,同時也是20世紀初葉激進的文化思潮,徐悲鴻先生在1918年發表的“中國畫改良論”亦同一機杼。20世紀初,大多數人都覺得中國的儒家思想、傳統文化、科學技術這些方面不行,主張西化,甚至是全盤西化。當時的知識分子都是抱著挽救危亡的愛國主義理想,很自然地形成一種一切都與富國強民有關的思潮。有人提出教育救國論,有人提出工業救國論,在當時這都很自然。美術界也是如此,木刻運動的興起,抗戰時期漫畫、宣傳畫的興起,無不與救國圖存有關。
雖然也有許多中國畫家還在繼續畫中國畫,不但齊白石、黃賓虹埋首攀登藝術高峰,更有如潘天壽、傅抱石、李苦禪、王雪濤等眾多傾心于中國畫藝術的后繼者,苦心孤詣、艱苦卓絕地努力,創造了中國畫20世紀的輝煌。但當時許多傾心革命的激進青年都覺得中國畫不能反映生活,不但在紅軍時期,就是在抗戰時期和國內戰爭時期,用中國畫形式反映現實內容的,幾乎絕無僅有,這更加令他們對中國畫的存在價值,產生懷疑。1949年蔡若虹在華北聯合大學給學生們上課時就講過,中國畫最終是要消滅的,因為這種藝術是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藝術,它不能為人民服務,不能為政治服務(據北京畫院曲則成回憶)。這種觀點雖然片面,但反映了部分人的想法。好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思想文化界對傳統文化觀念不再那么激進,國家領導人對中國畫還是挺重視的。大家的態度都發生了一些轉變,包括蔡若虹也寫文章贊美了齊白石的藝術。這是時代變化造成的不同。但是中國畫的改造仍是個問題。李可染先生在50年代的時候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文章,提出要重視改造中國畫的問題,提出要創新,要適應社會主義的政治發展形勢。幾十年來,如何改造中國畫在中國美術界一直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中西結合的命題,包括汲取西畫營養,在人物畫方面有明顯收獲,“徐蔣體系”探索開山,功不可沒。但是山水畫、花鳥畫怎么去畫新社會、社會主義呢,這都是有困難的。20世紀50年代有許多風景畫家勉強畫一些水庫建設、高壓電線乃至拖拉機,花鳥畫家畫糞筐,畫磚頭。藝術家們也是想極力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十分辛苦,現在看來不過是一個歷史過程,極少流傳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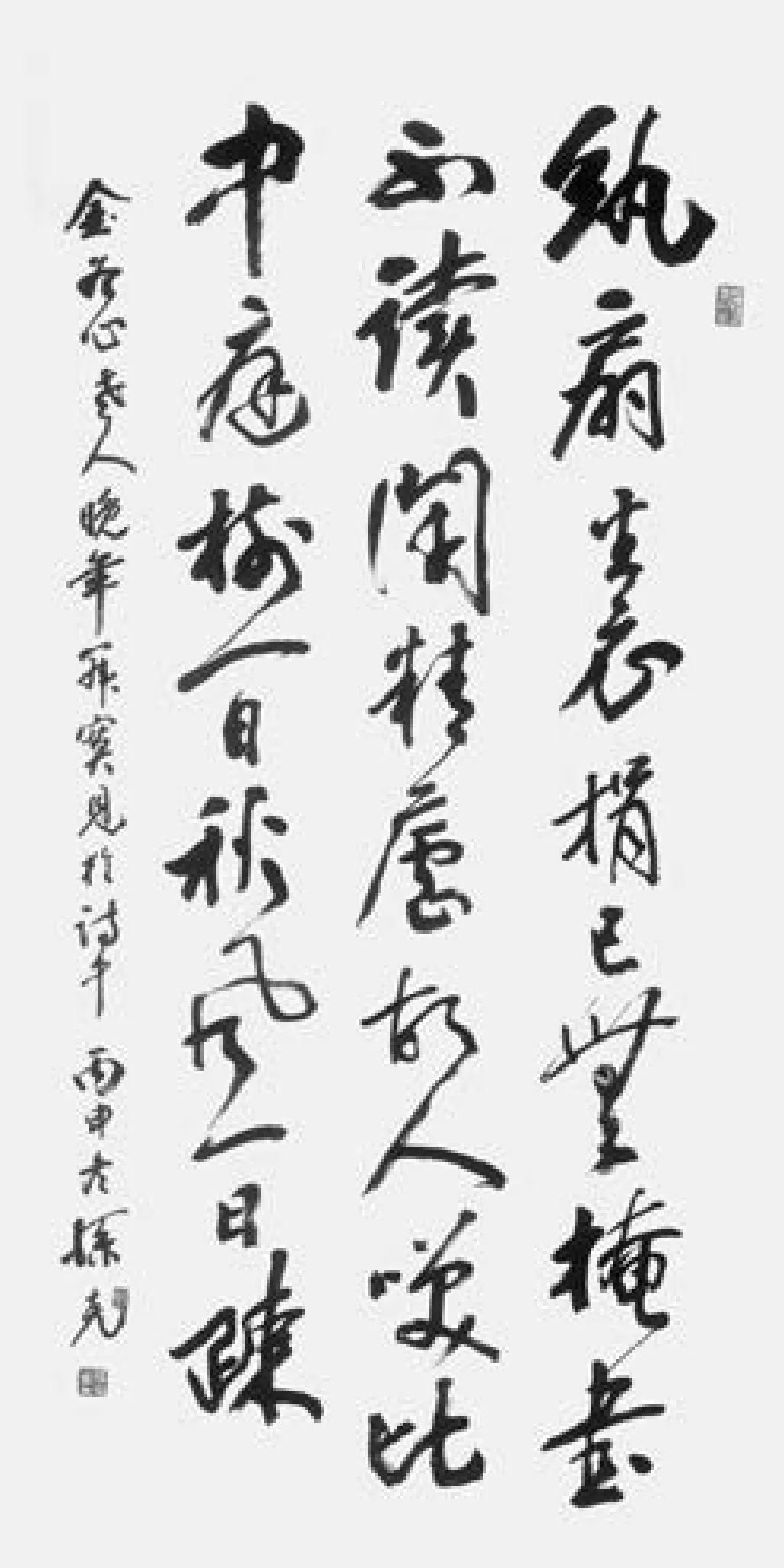
孫克 金冬心詩 136cm×68cm
馬春梅:對于中國畫,有很多觀點和提法都有其一定的歷史情境,需要重新認識和反思。全盤西化肯定是很偏頗的,但是歷史遺留問題造成的文化缺失,再重建的話確實存在比較大的困難。現在生活方式上的西化肯定是不可逆的了,這也使得一部分畫家、理論家認為中國畫的根基在改變。您覺得在中國目前的社會發展階段中,中國畫會失去它的根基嗎?您怎么看曾經震動整個中國畫壇的“窮途末日”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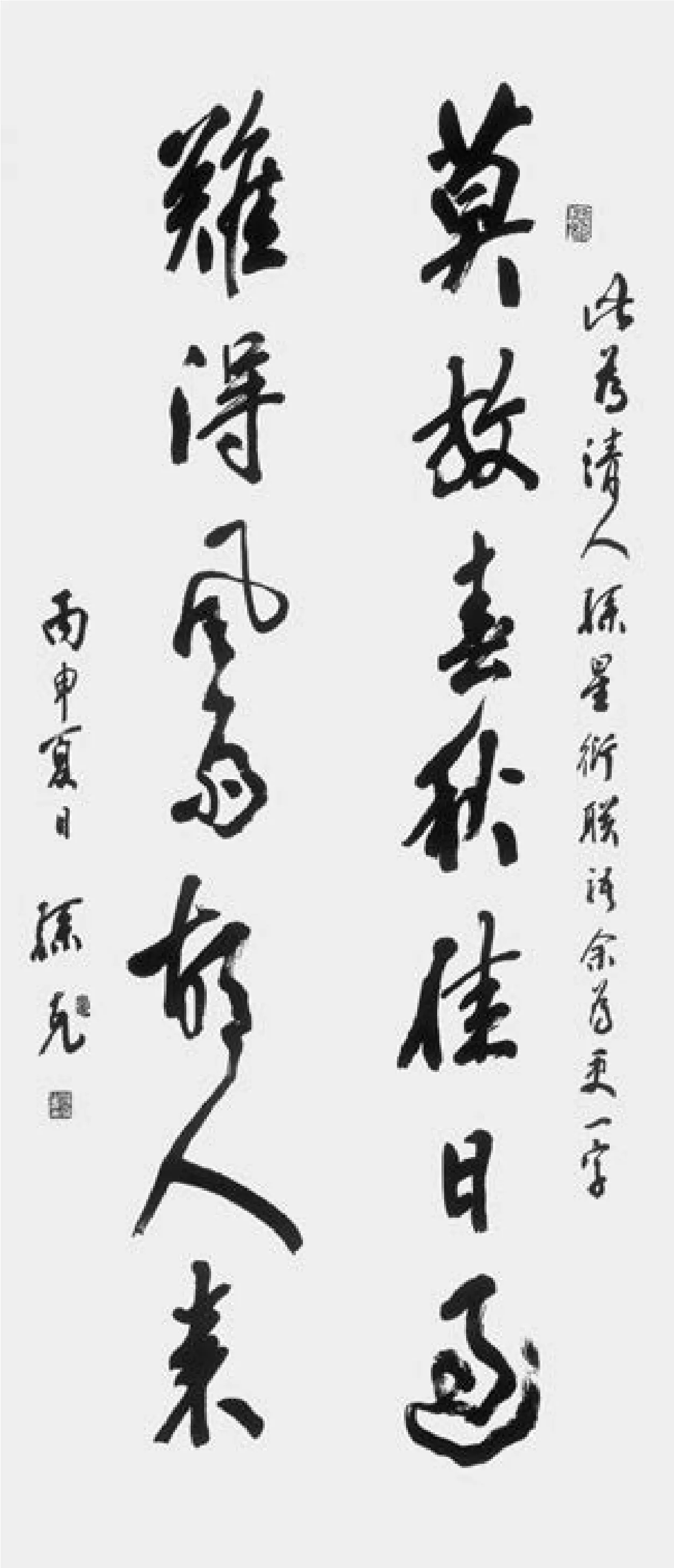
孫克 孫星衍對聯 136cm×68cm
孫克:現代社會的科學技術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必然的現象。鄧小平說過,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這種現代化的生活也是人民方便、幸福的表現,這并不能代表深層次的西化,西化主要體現在意識形態、文化思想方面的變化。中西的差異有很深刻的歷史、文化原因在內。例如,統一的方塊漢字就是其中很關鍵的一環。如果沒有統一的方塊字,中國現在就不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了。都用同一種文字,就有了文化統一的基礎,對中國的文化發展有關鍵的作用。簡單的西化是不容易做到的。不能簡單看問題。我們現在看孔子時代的書跟現在的語言有很多的相通之處。包括孔子當年說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些詞語到現在還在用。兩三千年還一直這么用,說明了中國文字的傳承性。從文字文化的精神延續到中國文化的悠久歷史,都是需要我們去認真研究、對待的一個過程。中國的自然、地理、社會狀態跟西方社會生產、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的差別,在文化、宗教、藝術上同樣有很多不同,如果單從生活方式上去衡量,我覺得這個西化的提法還是太表面。
中國畫現在的生存發展肯定不會很簡單地像某些人說的走向“窮途末日”。但是它會出現一些問題。中國畫的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一方面是中國人普遍的欣賞習慣,喜歡山水畫,喜歡花鳥畫,喜歡中國式的文人畫。另一方面,還要有一種中國傳統文化形成的欣賞力和較高的欣賞水平。現在要憂慮的也是這個問題。這一百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有了很大的困難。中國畫的改造不是想象的那么簡單,它有優點,也有缺點,對于中國畫的發展,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能夠恢復畫家對傳統文化的學習繼承。還有一個方面,就是現在的中國畫發展離不開世界文化。20世紀以后的西方繪畫變成了兩段,他們作為主流的優秀的寫實傳統被中斷了,實在是很可惜的。中國人應該把這些好的東西該借鑒的借鑒,該發展的發展,嘗試更多新的東西。傳統山水畫是臥游,看完山川以后回來畫出來的山水畫表達的是心里對山川的認識,通過山川表達自己心里頭對美的追求,表現的是筆墨、線條的美,皴擦點染的美,圖像程式的美,這實際上是一種主觀的操作和追求,跟西方人對景寫生完全不一樣。西方繪畫對自然的真實性追求和中國畫的追求不一樣。但是中國畫畫來畫去變成了師傅怎么畫學生就怎么畫,古人怎么畫我就怎么畫,把山水畫畫成死板的、沒有生命的東西了。到了20世紀,“四王”山水之所以受到批評,就是照抄照搬的人太多,失去生命力的關系。這就需要我們回過頭到自然中去體驗、去表現、去畫,這里頭就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和反差,所以要把西方繪畫的觀念吸取一些,現實的東西、大自然的美的東西能不能體現出來?能不能追求一點?有沒有這個可能性?當下的山水畫面目是很多的,大家都在探索,我們有自信,相信中國畫的前景仍然是廣闊光明的。

李可染 漓江山水甲天下 67mm×126mm 紙本 設色 1957年
馬春梅:這就牽涉我們如何將寫生與傳統融合,在多大程度上表現真實的問題了,這是中國畫改造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階段。
孫克:20世紀50年代,我第一次看到徐悲鴻先生畫的《漓江春雨》的時候,覺得他畫出了漓江在云霧當中水墨暈章的景觀,很生動,這跟傳統四王的山水很不一樣,畢竟有一個真實、新鮮、現實的東西包含在其中,很合我一個初學繪畫的青年人的胃口。又比如李可染先生。新中國成立以后他在中央美院負責教學,在教學中,他要符合中央美院注重造型、素描基本功的特點,同時要協調筆墨和造型這兩個方面,所以李可染先生就比較注重寫生。最早20世紀50年代李可染、張仃和羅銘三位先生去寫生,回來做匯報展,在北京、在中央美院很轟動,因為他們到生活現實中去寫生,帶回來一些鮮明生動的東西,當時給畫壇一個很大的震動。我覺得在寫生中,還是可染先生最成功。可染先生很智慧,基本功好,天分又高,而且他很理解中國畫的精神。他畫的頤和園、桂林,還有江南的山山水水,一方面是真實、寫實的,一方面又有筆墨,特別具有寫意性,虛實處理得特別簡練,不是見了什么畫什么。可染先生畫一棵樹,常常是圍著樹走,左看右看,選擇一個最美的角度,甚至進行加工。所以可染先生的畫比別人高明就在于它是真實的,又是精神的內在的東西。我特別佩服李先生這一點:他早年在杭州藝專學西畫,參加過前衛精神的“一八藝社”,抗戰時期畫宣傳畫,但是他到了北平之后,就去拜齊白石老人為師,又是黃賓虹藝術的忠實追蹤者。應該說筆墨精髓是可染藝術的真諦。對中國畫來講,寫生實際上是一種探索印證的過程,觀察寫生歸來進入案頭錘煉,然后再去寫生。畫家長時間關在畫室里會有靈感枯竭的感覺,要從自然、生活當中吸取一些新的東西和體驗。
但是,要想把中國畫的山水畫畫好,光靠寫生真實景觀不行,只畫山石景觀的中國畫不是好的,中國畫是能夠千錘百煉、經過時間考驗的,不會被人忘記。有些老畫家如黃賓虹,有人說黃賓虹的畫有一個不足,就是他畫的山水都是一個面貌,沒有明顯的區別,但是他與一些畫家不同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他畫的是他心中的山水。黃賓虹的畫山川渾厚,草木滋潤,極富內美,他的藝術在他身后日漸彰顯。畫家同時面臨著真實的現實和心里頭的意境創造的東西。現在畫家太多了,畫得好的人也很多,大家都自由發揮。現在的文化政策也鼓勵大家不斷去創造、追求,個人的個性得以發展。這種情況之下,如何綜合提高自己是一個問題。黃賓虹先生去世都幾十年了,又重新被大家認識,這就是藝術的一個特殊的規律。真正的珍品不會永遠埋沒,而且越陳越香,越有價值,這說明藝術不是一個簡單的事物。我希望大家記住和理解賓虹老人的話:“有筆有墨兼有章法者,大家也。有筆有墨而乏章法者,名家也。無筆無墨而徒事章法者,眾工也。”我覺得我們也有責任,應該有一種精神的創造,一個時代的藝術,能夠達到很高的水平成為時代的經典。偉大的作品都體現著人類的智慧、精神,有益于后人,為后人頂禮膜拜,就像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歷代繪畫珍品。
比如說我們在80年代發現的江西畫家黃秋園。南昌并不是文化中心,加之當時“左”的文藝環境,黃秋園的藝術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令人十分惋惜。黃秋園在筆墨技巧方面很有特點,功力非常深厚,畫面很重、很黑,晚期的作品越畫越黑,真是達到賓虹老人與可染先生提出的“層層深厚”的要求。他的作品當時沒有人懂得欣賞,那時更沒有市場,更不受地方有關部門的重視,他連美協會員都不是,但是他解決了很多的技巧、技術的問題,藝術境界也很高。1985年他的作品在北京美術館展出時很轟動,李可染先生也去看了,這也是很有影響的事。他的作品特點和李可染先生的藝術追求是有共鳴的。可染先生很重視,也很欣賞,甚至說了“國有顏回而不知,深以為恥”這樣的話。這個評價當時有人覺得有點高了,可染先生的意思是覺得慚愧,沒有早些發現這么好的畫家。這體現了可染先生虛懷若谷的氣量胸襟。在黃秋園前后還出現了一位四川成都畫家陳子莊。陳子莊更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畫家,他所達到的獨創性、生動性,還有對傳統的精神的一種繼承,藝術上做到真正的高簡淡逸,格調極高。他的藝術源于生活,根于傳統,獨樹一幟,極富個性,別開生面,很了不起。黃賓虹、黃秋園和陳子莊都是從優秀傳統中走出來的畫家,所以我覺得我們對傳統,對中國畫須要有一個再認識的過程。在不斷認識中發現有許多畫家被埋沒,或者以前不夠重視。這短短一百年回看過去,真正好的畫家陸續被“鉤沉”出來,我們還要不斷努力。

黃秋園 秋山幽居圖 117mm×113mm 紙本設色1976年 中國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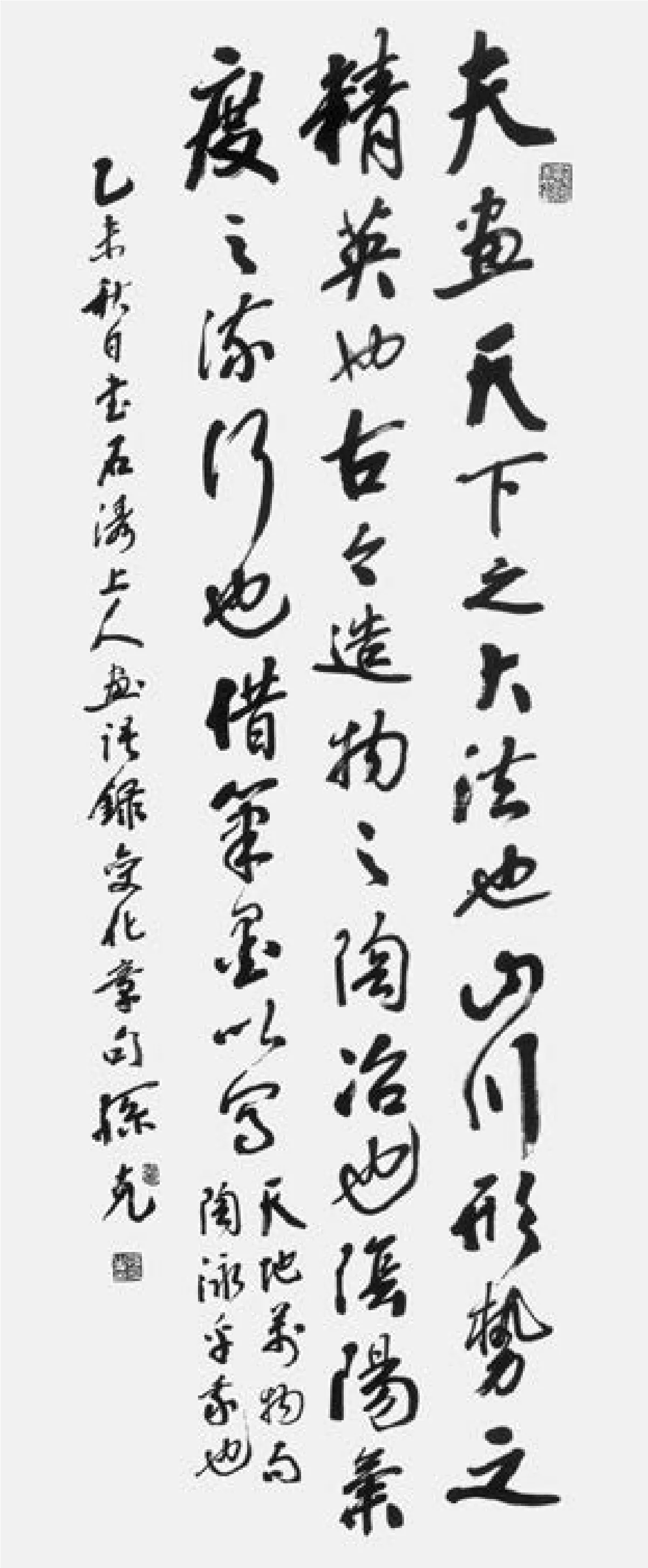
孫克 石濤畫語錄 138.5cm×48cm
馬春梅:您在北京畫院《中國畫》雜志的時候,其實也對繼承、推廣傳統文化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孫克:對。《中國畫》雜志是1957年北京中國畫院成立后開辦的。沒辦多久因為經濟條件停了多年,一直到了1982年才復刊。復刊后由潘絜茲先生做主編。我是他的助手,就跟著潘絜茲先生一直致力于對傳統的恢復和發揚(尤其重視工筆重彩畫),也比較關注現實。因為當時全國美術刊物很少,中國畫專業刊物更少,所以當時雜志的權威性、話語權比較受到讀者尊重,尤其受到畫家們的重視。潘老是畫壇前輩,德藝雙馨之譽當之無愧。我受他影響甚深,學術目光轉向當代中國畫的發展和繼承,感到改革開放的時代為文藝事業迎來春天,機會難得。80年代早期美術界思想活躍,“保守”與激進難免各趨兩端,有人發出中國畫“窮途末日”的呼聲,意在西化乃至“全盤西化”。當時的我明確選擇“保守”一途,發出中國畫正處于“方興未艾”的高調,認為對于民族文化不可妄自菲薄。當時論戰相當激烈,也十分令人激動,真的是學術之爭。對于后來有人譏我為“傳統衛道士”,我不覺難受反而感到光榮。我的人生經驗告訴我,20世紀以來,中國人自己貶損自己的文化,令自己喪失文化自信,令人痛心,維護傳統要理直氣壯。當時盡我所能做一些有益于中國畫建設的事,一是協助潘絜茲先生大力提倡發展工筆重彩畫事業,《中國畫》雜志功不可沒;二是盡力推動中國畫創作,發表精品好畫,宣傳老畫家,推出青年俊彥;三是發掘被埋沒的精英人物,如陳子莊、黃秋園、黃葉村等。黃秋園畫展是我一手策劃和推動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展出極為成功轟動,當時正值“’85思潮”高峰,“西化”呼嘯震耳之際,黃秋園畫展廳內人山人海,說明人心所向。當時有人說我們“以死人壓活人”(“文革”中常用語),三十年回首,孰是孰非,歷史會有判斷。三十多年為優秀文化傳統奔走呼號,是我認定的方向,不怕人罵,也從不后悔退縮。
馬春梅:現在好的文化陣地太缺少了,可能一方面是由于文化陣地太多,恰恰導致了權威的分散和失效,另一方面也的確是因為現在理論家、畫家扮演的角色和以前都大大不同了。
孫克:我在《中國畫》雜志的時候,沒有考慮市場的問題。只要畫家是好的,我們就發表,沒有想過利用雜志從畫家身上牟取利益。我們白天組稿、跑腿辦事,自己帶著照相設備到處去發現畫家,去拍照,去訪問。晚上還要給畫家寫文章,介紹作品。90年代藝術市場剛剛起步,書畫拍賣的第一槌是1991年開始的。藝術市場對藝術發展的推動力是很大的,繁榮是它造成的,負面的影響也是它。好處是確實推動了畫家們努力作畫,提供大量的作品給市場,國內的藝術市場、畫廊、拍賣行大量出現,進入規范,畫家創作的積極性也空前提高,也有很多的青年進入這個行列,藝術院校的國畫系大大繁榮。市場給畫家以社會地位,很多畫家成了“先富起來”的一群人。生活的改善本身不是壞事,但負面影響就是讓藝術變成對物質利益的追逐,變成各種利益的交換。以至于現在有一些畫家心態比較浮躁,作品粗制濫造,不斷重復,形同行活。齊白石老人的作品在當時也是有市場的,這些年我們看到的白石作品,只要不是贗品,幾乎每張都很精彩,絕非應酬之品。據說白石老人每天上午畫一幅,下午畫一幅,都是高質量的、很認真的,絕不因為市場需求而搞“流水作業”。讓我們想一想,浮躁最后損害的其實還是市場,損害的更是畫家自己。
馬春梅:自從20世紀80年代起,您就堅定了繼承發展中國畫的信念,這樣的文化自信是如何建立的?
孫克:談到文化自信,我個人的體會首先是要了解自家文化,懂得自家文化,并且熱愛這個文化。其次,要做到文化自信,還要了解、懂得和中華文化有深刻不同的這個西方異域文化,真正了解和懂得兩者之間的差異,乃至各自的長短。這樣才能避免盲目。
我讀小學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小學校長是一位飽學宿儒,自編了一本《經訓》小冊,摘編《論語》中做人的基本道義守則,當時懵懵懂懂,成年后感到極受教益,許多名句至今猶能背誦。班主任對我一生影響極大,他油印了魯迅的雜文還有朱自清的散文如《匆匆》給我們閱讀,他教我做人要真率,“敢哭、敢笑、敢講、敢罵”,老師播撒在我心中的一顆種子萌芽生長,影響一生。
在中央美院附中學習的幾年里,我是不折不扣的西方文化的粉絲。新中國成立初期,向蘇聯一邊倒,我們美院附中就是這樣,從教學到課余生活,幾乎蘇化了,就文化內涵思考,蘇俄文化的本源仍屬于歐洲文化范疇。就我個人來講可謂深受影響,那時年輕,對西方文化十分醉心,大約和當下許多青年一樣。從1960年以后,我開始讀中國書,讀中國文學史、詩史,讀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滄浪詩話》《人間詞話》反復閱讀,《西廂記》《聊齋志異》是我的最愛。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才逐漸地明白了、清醒了,成了不折不扣的傳統文化的“衛道士”,認真講,戴“衛道士”的帽子,我自認還不夠資格,我的學識水平也就屬于“擁躉”而已。
人生短暫,每個人只會得到他親歷的那一段歷史現實所給予的認知,但是,讀書求知卻可以使人的心胸目光燭照大千。如今我年過八旬,生活和讀書體驗令我深深感受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浩瀚無際,我們的文學藝術豐厚、精美無比,怎樣形容也不為過,它是如此大美,因此我們窮盡一生也不可能盡窺其堂奧。前人說“弱水三千,我只做一瓢飲”,而我們在幾近百年的時段里,自我輕蔑,自我菲薄,得失之間,難以估量。對于西方文化,我們歷來虔誠學習,大家常說,我們了解西方(文化),遠勝于西方對我們的了解。當然,還要知道中西文化的深刻差異,是源自自然環境及其形成的農耕的和漁獵(商業)的生產方式,更是人性、歷史形成的不同社會制度,以及文化審美追求的種種差異,皆屬于無情的客觀之制約,非個人主觀愿望可以任意嫁接移植。文化之間是可以相互借鑒學習的,多年來我們學西方獲益不少,然而,不應該成為輕蔑自己的理由。今天中央提出建立“文化自信”,我感到極其英明、正確、適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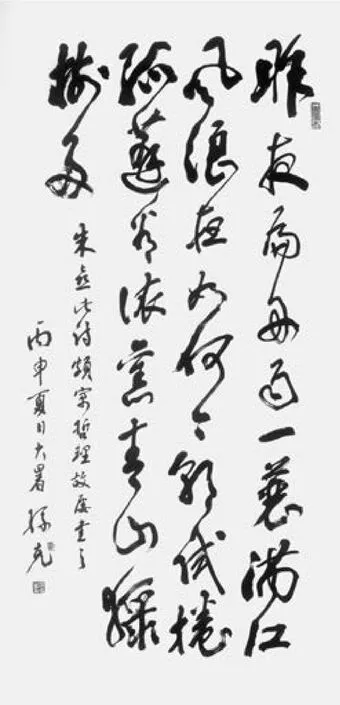
孫克 朱熹詩 136cm×68cm
馬春梅:您從事藝術理論工作,又潛心研究書法多年,能談談書法的問題嗎?

陳子莊 山水 23.5mm×30mm 紙本 設色 20世紀70年代
孫克:所謂書畫同源,書法對繪畫的影響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中國人一開始就是用軟筆寫字、畫畫,形成了用線條來表達美感,注重寫意的藝術形式。但書法的美感不一樣,大有學問。畫家要對書法下一點功夫。因為書法所包含的美學內涵涵蓋中國畫里的很多東西。但書法的復雜性在哪里?書法的文化內涵太深刻,又是一種很獨特的藝術形式。書寫首先是表達意思的,始終是一個實用的事物。書法如果寫不出一個字的話,那就不是書法了。文字內容是它的規限,不能越出這個圈子,越出這個圈子就不是書法了。所以,書法顯然是一門抽象的藝術,追求的是一種抽象的美,但是這個抽象又不是無限制的,限制它的是文字的筆畫規矩,而其審美標準又是由幾千年形成的審美法則所制約。從甲骨文時期萌芽的書法審美,經過大篆、小篆、漢隸、魏碑、草書、行書,為什么到了楷書,動作就慢下來了?甚至是永字八法中八個有名稱的筆畫就把中國的書法楷書的字體概括了,就因為書法是實用性的,楷書的字形規范實用了,它的審美標準就比較定型了,這個審美的規律也是大家通用的規律,共同的體會。但是定型不等于說書法審美就定型了,它還是在變化,不斷地發展,可是又有限制,就是它本身離不開文字,始終跟內容結合在一塊兒,它跟文字內在的文化內涵又是完全不可分的。書法是傳達感情、交流思想的一個載體,如果寫書法看不出是什么內容,就不是書法了。
我有時候就覺得書法不大像是藝術,感到它跟藝術的概念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書法又是一門藝術,它有屬于它自己的審美規律。書法正是一門特殊的、獨特的藝術,全世界只有中國人的文化里有書法這個藝術門類,我覺得這是我們中國人最大的驕傲,是祖宗給咱們的傳家之寶,是中國人獨一無二的創造。西方人有古代石頭建筑,有他們的雕塑、油畫,他們賴以驕傲。而我們有書法。書法的美,書法的獨特性,有十幾億人去欣賞、喜歡、理解,我們也應感到驕傲自豪,所以一定要愛護、要維護、要發展書法,因為我們還在使用它,他令我們得到美感享受。中國書法是經過幾千年不斷的創造積累的,我們把它繼承下來,發展下去,給后人留下美好的事物,不要在這個時代斷了代,這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一直的堅持。
書法怎么發展,怎么能夠出現有時代性、有個性的精品,書法界也在尋求繼承之路。但是對于繼承和創新的命題,思潮難免出現混亂,市場陷阱也比較多。就比如說怎么突破古人、突破傳統?你學顏真卿,超不過顏真卿,你學米芾,你不是米芾,你學黃山谷,你又不是黃山谷。清末書法家李瑞清醉心于寫《鄭文公》,前些時我看到書法雜志上刊登其作品,我覺得他學得不地道,不是真正的鄭文公,他是模仿鄭文公的樣子,因為他無法也不可能復制那種時代感。魏碑是從隸書向楷書之間過渡的一個生長時期,它的美就在于它非常自由的狀態中又包含規范,而且非常雄厚,你模仿他,寫得很像,寫得很漂亮,但是你還是一個模仿者(何況學不出那種斑駁的味道)。又比如沈尹默,不是寫得不精美,但是他不是有個性的書法家,因為他是要再現“二王”,而“二王”的唯美追求早在唐宋時期就被人突破、替代了,所以陳獨秀批評他“其俗在骨”,這個“俗”,是他走進了審美誤區。前些年又有人學沈尹默,等而下之,更加俗氣了。什么書法是好書法呢?我覺得是起碼要寫出自己。古代人從小寫字,基本技法過關不難,何以書法大師極少?前人說“書以人傳”,這個“人”是指名人(如今有所謂“名人書法”一說),但在歷史上,這個名人不是指當官的,不是知名演員,更不是電視臺主持人。古代流傳的書法家,是真正的文化人,有學問、有修養、有人品、有性格,書法就是這個人的映照。古人說“書如其人”即此意也。還要有鮮明的個人風格,蘇東坡、米芾初學顏真卿,他們的書法里有顏體,為什么蘇東坡和米芾都成為大師,都成為歷史上最有名的書法家?因為蘇東坡就是蘇東坡。即使有人批評他的用筆跳動性不夠,但是這就是他的個性,米芾就有米芾的個性。沒有個性、沒有文化內涵就是寫字匠。這些年有人曾經公然地倡導“丑書”,令人反感,按照“書如其人”的邏輯,我們要問提倡者是相貌丑,抑或是內心丑呢?
我幾十年前臨《鄭文公》,后來學孫過庭的《書譜》,學米芾,臨王鐸,我自知學得不好,資質不夠所致。但是也有很多收獲心得,我只是覺得在書寫當中會得到一種樂趣,一種精神的寄托,努力寫出我自己。我也不敢妄求成為為人稱道的書法家,始終保持一種平常心,這也是一種狀態,就是自娛自樂。好也罷,賴也罷,像不像也罷,都是自娛的,這或許是中國文人的一種狀態。
因為書法文化的內涵太深厚,古代的積累太豐富,超越古人實在太難。但我認為每個時代都可能出現杰出的書法家,只要人們把自己的個性體現出來。沒有個性,沒有文化,沒有較高的修養,人品傖俗,心胸狹窄,即使天天練斗大的字,這樣的書法家有什么意義呢?匠人而已。這個書法對今人、對后人來說有什么意義呢?沒有意義。
現在市場經濟這么熱鬧,我也很清醒,我就覺得這里頭有問題,我們應該不為它所動,因為藝術畢竟是藝術。政治歸政治,市場歸市場,藝術歸藝術,努力去做,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全力以赴,真誠對待。我自己所能做到的,就是幫助了一些畫家,盡了一個人微末之力。包括寫文章、發現人才、推薦畫家、熱心畫家們的公益事業等等。因為我經過很多人生低谷和困頓,幾十年的人生就是在艱苦奮斗。我深深知道一個處于困難中的人,如果有人此時伸手拉他一把,一定是功德無量的事。但是這卻常常不容易,如果能夠幫助別人的話,也等于把自己升華了。尤其是像黃秋園、陳子莊這樣的畫家,我都在他們身后為他們做了許多事,給他們寫文章,給他們做宣傳。到現在我還在宣傳陳子莊,陳子莊去世的時候,江青集團還沒有被打倒,我真的對他非常同情。把好的藝術、好的文化傳統繼承發揚下去,我覺得這是我們后來者的一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