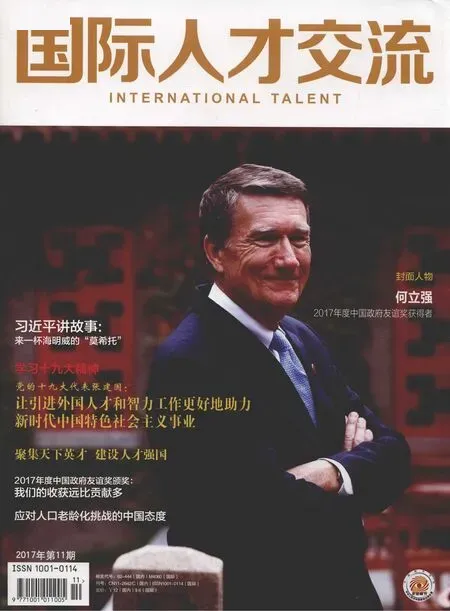為什么外國人習慣稱中國為“契丹”?
文/李強
為什么外國人習慣稱中國為“契丹”?
文/李強
編者按
從秦始皇、兩漢一直到盛唐時期都與中國交往密切的阿拉伯人自10世紀起開始將中國稱為“契丹”(Khita或Khata),甚至在遼朝和西遼均已滅亡后,阿拉伯兵書《馬術和軍械》(約在13世紀晚期成書)仍將火藥稱為“契丹花”,把管狀火器稱為“契丹火槍”“契丹火箭”等。
為什么外國人習慣于將中國、中原或者中國人叫“契丹”呢?我們知道,中華文明與西方交往甚久,秦朝、漢朝及隋朝、唐朝時期,中原的華夏(漢)族就與西方同時興盛的羅馬帝國、拜占庭、波斯、阿拉伯哈里發等帝國進行了密切的交往,但是他們為何不用廣泛使用“漢”“漢人”、“唐”“唐人”來稱謂中國和中原漢族呢?
這的確是個有趣的問題。
其實,答案很簡單:這是遼朝(916—1125年)與遼朝后裔西遼在兩個多世紀里遠播華夏文明的結果。
在中國內部而言,中原王朝往往稱北方游牧民族為“北虜”或“胡虜”,而遼朝的建立者——所謂的“胡虜”之一的契丹族,早在隋唐時期就已經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郡縣統治體系中的一分子,到遼中期圣宗、興宗以后早已完全漢化和儒化,并以中國正統自居,在對外交往時明確以“中國”(中原)自稱,自命為前朝法統的合法繼承者。
作為炎黃后裔的契丹民族,崛起于亂世:“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之后,中原政權陷入了不可逆轉的衰落。中央政府對周邊各族的影響和控制明顯削弱與放松,藩鎮之間永無寧日的權、利之爭使中華大地無比混亂;而北方草原的回鶻(舊稱回紇)汗國崩潰后,原本勢力比較強大的黠戛斯人卻沒能建立起強有力的政權,反而是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倫河)、土河(今老哈河)之濱的契丹人,抓住了這一歷史性的機遇:他們迅速擺脫了分散和各自為政的松散部落聯盟,緊緊依靠中原流離失所百姓中的先進分子,將自己從落后的奴隸制社會轉向農奴制和封建制相結合的社會,生產力得到長足進步,民族凝聚力空前提高,逐步建立其統一了中國北方的強大王朝——遼朝。
盡管在此前的中國歷史上,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曾經在兩晉南北朝時期都分別建立過封建制政權和皇權,但不是曇花一現,就是只能局促于比較狹小的區域;龐然大物般的少數民族如柔然(蠕蠕)、突厥、回鶻等,要么就如過客一般轉瞬即逝,要么就是建立松散的汗國,因此,之前除了北魏,很少有少數民族政權,能在統治范圍、文化社會發展、政權建設的規范與鞏固等方面與契丹相提并論。
重要的是,契丹民族在其天才領袖耶律阿保機及其家族帶領下建立的遼朝,橫亙在中國北方數百年,在地理和人文上替代自以為“中原正朔”的北宋、南宋與世界各國特別是亞歐大陸各民族、各國家進行交往,長時間的影響,使當時的外國人都把東方富裕、繁榮、強大的中國和中國人等同于契丹,于是在外族對中國的語言稱謂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跡。
遼亡后,秉持中國正統信念的遼皇族耶律大石僅率200人脫離金軍的追捕,卻能靠耶律氏遼朝的皇權正統,在短短數月糾集起十萬部眾追隨自己,并且以正統觀念為精神食糧,遠涉萬里,克服今人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在遙遠的中亞重建一個強大的遼帝國(史稱“西遼”,中亞史籍稱“喀喇契丹”。耶律大石為西遼首帝——德宗)。
正是因為西遼在中亞立國近百年,以及西遼被蒙古軍滅亡后后裔在今伊朗建立的后西遼政權,給當地帶來了先進的典章、政權體制、庶民文化、農業技術、生活習俗等中國文化,加深了各民族間的交流,使得這些以中國正統自居、帶有強烈中原(漢)文化特征的群體給當地和西方人以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因而西方人稱中國和中國人為“契丹”也就不足為奇了。
遼朝是繼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以后,中國少數民族建立的又一個具有重大歷史和現實影響的朝代,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與作用,它兼具草原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對促進中國北方各少數民族的經濟發展、文明進步居功至偉。
古往今來,許多國家把契丹作為對中國的稱呼,比如俄語和部分斯拉夫語中對中國的稱呼即來源于契丹,即“Kitan”(直譯為“契丹”“乞臺”),至今如此;中古時期的希臘語、阿拉伯語、波斯語、古代英語以及部分拉丁語言民眾,也都是采用“契丹”的叫法來稱呼中國。在現代英語中,也有用近似契丹的“Cathay”一詞來表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