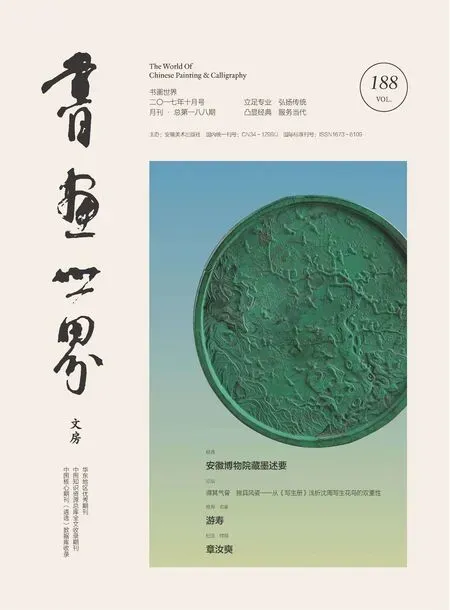從『書如其人』的疑問出發
文_楊二斌
從『書如其人』的疑問出發
文_楊二斌
清人劉熙載在《藝概·書概》云:“書者,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無疑,此說是西漢揚雄“書為心畫”之最佳注腳。而關于此論,贊成者有之,詆毀者亦有之。詆毀者往往以史上臭名昭著者(如蔡京秦檜之流)的書作為證據,而辯駁者亦是認為其人不足稱,其藝則等而下之。
的確,在書史之上,把人之道德準與藝術水準關聯在一起,稱為“人品即書品”。如果以“人品”為第一位,則“書品”是附著于“人品”等而下之的第二重意義。這是中國書法發展史上的主流意識,而強調以書法風格為第一位,把“人品”附著于書法風格之上,則是混淆了“書品”與“書法風格”二者的區別。
“書品”,我認為是“人品”意義在字里行間的道德疊加,而“書法風格”則是一個人書寫時的風格特征,“書品”強調的是人一生的達到高度,“書法風格”則強調一個人終其一生所形成的天生與眾不同的書寫面貌。如果必須找到關聯,歷史上書家的風格特征的確是和其性格相互表里。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性格氣質決定這個人的精神面貌,從而決定這個人自我書寫的外在特征。比如說王羲之風骨峭拔,其書遒勁而秀美;顏真卿嚴肅端莊,故其書雄渾而大氣。如果強迫讓一個性格很是拘謹的人書寫極為奔放的狂草,而或讓一個性格很是好動的人書寫極為安靜的魏晉小楷,那么這二者都是出力不討好的。
諸如蔡京之流,其道德水準極其卑劣,則其“書品”是極差的,而其書作本身僅僅是表現了蔡京之流的風格特色以至于性格氣質,這是藝術水準和道德水準不在同一水平線上的典型表現。若是一個道德高尚之人的書法藝術水準不夠,則不能以“人品”與“書品”不符相評論,而可稱其書法的技法水平不足,但字里行間表現其性格氣質的東西則不會大變。所以,書法的藝術水準與道德水準的關系是極為微妙而復雜的。當差別不彰時,最是以道德評價代替書法藝術水準,而當藝術與道德的差距過大時,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的觀念即是標準。
回想往事,練習書法二十年,而入門也僅僅十載。起先我的學習是盲目的,所以在不得筆的情形下歷了數年;后負笈求學于平陽,得遇柴建國、楊吉平、李晉林諸位恩師,初窺學術之門徑,以考據之學為根本,兼之書法技法的學習,集力于藝舟雙楫,尋根探源。具體來說,即在解讀書法史料中發現微觀問題,不放過每一個細節,包含技法與理論的雙重學習,從其發展原因、表現形態以及淵源流變,深入挖掘歷史文獻資料,精確找尋古人的蛛絲馬跡,對文本進行全面的分析和解讀,將書法史的宏觀層面以及書法技法的微觀層面結合起來,找到書法史中鮮為人知的而當時又被廣泛遵循的制度規范以及筆法演變發展規律。這樣讀書讀帖,不僅“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思路由點及面,由表及里,去偽存真,猶如新疆的坎兒井,自上而下,自前而后,深研擴展,理解書史的因果始末與勾連,這樣日久自然有所貫通。
丙申之秋,我又入長安求學,追隨鐘明善師、薛養賢師,向之甚篤,學之甚勤,以哲學之美學為方向,擴寬了學術視野。特別是以科學哲學之信息哲學為觀照,發現了書法文化信息化的密匙;以書法史中的東漢為中心,搞清楚了五體源流以及其與當時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從書法美的視角來理解漢末魏晉書法之所以成為藝術的史實,實在是因為草書是在漢代杜度、崔瑗、張芝這些文人的雅化中完成的,而其完成是書法時空變化的繼承、轉化并完善的。而我等的的確確能夠在這種書法研究中完善技法水平,這些理解成為我近來最大的收獲。

1.楊二斌 自作詩六首 34cm×68cm 2017

2.楊二斌 董逌廣川書跋一則 68cm×48cm 2015

3.楊二斌 論語節錄 68cm×68cm 2015

4.楊二斌 逍遙游節錄 68cm×68cm 2013

5. 楊二斌 文章高義聯138cm×34cm×2 2016

6.楊二斌 張九齡望月懷遠 120cm×26cm 2014

7.楊二斌 王羲之書論三篇 138cm×68cm 2015
當然,書法是一輩子的事,急不得也緩不得,只有找到正確的入門之途才能有所收獲,而隨遇而安卻也是獲得書法真經的大敵,只有勤學苦練加之方法正確才能有所小成。人一生若有小成也就不錯,但又不知足而讀書習文學畫,想要打通中國文化的“任督”二脈,或者再過數十年才夠達到古人之萬一。
誠然,每一位學人皆于春秋寒暑之間,無非是想求得一方碧水,以求不負自己的初心。然而駑馬十駕,功在不舍;跬步數積,方致千里,這樣或許可能浸潤于詩書之間,游藝于翰墨之內。所幸與諸位師友相知相琢,談心盡意,學問文章,充盈肺腑,時有舉杯邀月,把酒臨風,放書言志,頓感華年不負哉!
東坡居士曾說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于我觀之,累人之物,實在是用自己的執念去思索世間萬物,時有得到,時有未得,得到了高興,得不到痛苦,欲望其實是累人的根本。莊子把人的修性分為數層境界,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徹、見獨、無古今、不死不生,而自己連最初的外天下都很難達到,所以給自己刻了一方閑章“不外天下”。我想,生于天下之內,一定處之泰然,順乎自然之境,非可欲,則可以不爭于天下,或者可以達到莊子所謂的外天下,至于外物、外生諸境界,也就是冥想而已。今生能夠達到何等的境地,靠的是內心的干凈與平靜。而我只有通過書寫與天地溝通,與古人溝通,這也是“與天為徒”“與古為徒”的一種方式吧。
感嘆一下歲月又過了數時,想想,言之易而行之難,獨善易而眾達難,故而古代士人之理想是窮則獨善其,達則兼濟天下。而今日我等居小道或能達于可觀,居文海或能懷德于未來。冥心求索,或能感懷發于筆端,如人之書,或能傳播于未來!
約稿、責編:史春霖、徐琳祺

楊二斌 Yang Erbin
又名爾彬。西安交通大學博士研究生、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山西省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山西書法院特聘研究員。書學論文曾榮獲第四屆中國書法“蘭亭獎”理論獎三等獎、全國第八屆書學討論會一等獎、全國第十屆書學討論會優秀論文(最高獎)、首屆敦煌論壇優秀論文獎(最高獎)、全國第二屆草書展學術論壇(最高獎)等。出版有《山西書法史》(合著)一部,在《中國書法》《書法》《書法叢刊》等專業報刊上發表文章30萬余字。作品入選國家級、省級展覽數十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