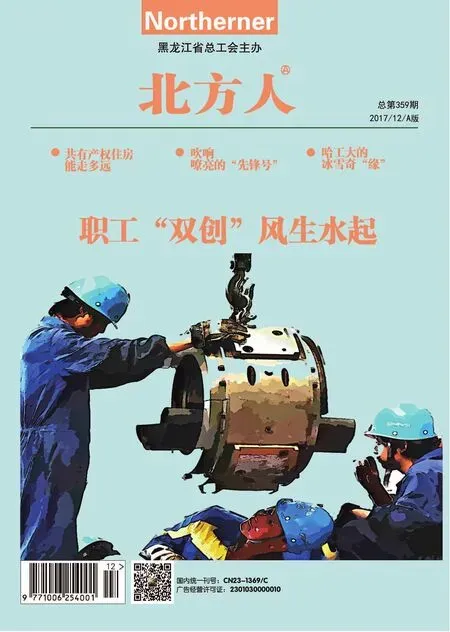父親的信
文/周脈明
父親的信
文/周脈明

中午剛剛走出單元門,投遞員小王就遞給我一封信,我低頭仔細一看信封地址,上面的字跡歪歪扭扭,是從山東農村老家寄來的。
這封信讓我大吃一驚,既沒有按照書信的格式寫,也沒有太多的文字,只是短短的兩行字,而且畫了好多〇,連標點符號都沒有:“兒好我是你爹爹媽〇好我們〇念你我不〇用電話電腦〇意聽別人念你寫給家中的信希〇你經常給家中寫信”。看到這里,我的內心一凜,鼻子發酸,兩行熱淚流了下來。這是父親的親筆信,這是我有生以來接到的父親的第一封親筆信。
父親是文盲,他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聽和父親居住在一起的弟弟說,自從我離開家鄉以后,盼我的信成了父親對我最習慣的思念方式。每逢郵遞員來到村口,父親就會迎上去,急切地問:“有我的信嗎?”當郵遞員把我的信遞給父親時,他會眉飛色舞,一邊興高采烈地回家,一邊自言自語:“我兒子來信啦!”
由于弟弟經常外出打工,常年不回家。每逢收到我的去信后,父親就會讓剛剛上小學的侄兒給他三遍五遍反復朗讀。侄兒有時候讀得不耐煩了,把信扔在桌子上就跑了。父親就會拿起我的信,睜大眼睛,仔細端詳半天……收信當天晚上,父親就會讓侄兒給我回信。他前言不搭后語地口述,侄兒在一旁毫無章法地記下來,信的內容,雖然語言不華麗,土得掉渣,但是字字敲擊著我的心弦,催我自新,同時也增添了一份勇氣和自豪。
父親在來信中常常出現的字眼兒有:
“咱當不了英雄,也別當狗熊。”“咱多吃點虧,沒壞處。”“穿過的舊衣服,別隨便扔了,也別賣破爛兒了,給那些討飯的也行,寄回老家來,給干農活的大爺、叔叔們也行。”“咱別當墻上的狗尾巴草,咱要像咱家地里的谷穗,粒越大越低頭”……
每當我收到父親的信,讀著只有我這做兒子的才能理解的內容時,有時候想笑,可是卻笑不出來,不爭氣的眼淚總會不由自主順著臉頰淌了下來。
后來,由于家中安裝了電話,我便和父母用電話保持聯系。據母親講,父親收不到我的信了,每逢收到我寄給父母生活費的匯款單時,父親就會兩眼盯著打印地址、姓名以及附言欄里的字跡端詳半天,舍不得去郵局取錢,有時候把匯款單在家存一段時間,不到最后期限,他就不讓拿著匯款單去取錢。又過了幾年,弟弟為了讓我省下寄生活費的郵資,在銀行開了個賬號,我把生活費直接匯到賬號上。父親整日盼我寫信給他,有時竟偷偷地盯著電腦出神……
手拿這封信,我的眼睛模糊了。“家書抵萬金”,我深深地理解了這句話的含義。通訊再發達,人與人的聯系方式再便捷,家書,也永遠是最沉甸甸的情感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