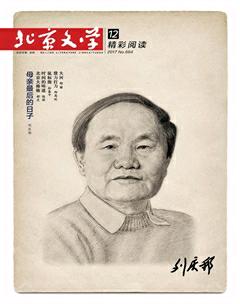誰不熱愛保羅·斯科爾斯(短篇小說)
段凡,四十三歲的“老男人”,是我們這一幫朋友里的球癡,他愛球,尤其癡迷保羅·斯科爾斯。我們在取笑他的同時,也在吹噓:誰不熱愛斯科爾斯,就如同誰不熱愛青春歲月。青春一去不復(fù),但熱血依舊。
不能不管了。
段凡拎著酒瓶從張勇的復(fù)式樓梯上往下跳,炸裂的玻璃碴兒差點把他戳瞎。他昏迷不醒,張勇?lián)渫ü虻兀皇职醋∷骂€動脈。后來他在急救車上醒了,頭一句就是,今晚曼城打曼聯(lián)。醫(yī)生說,看來問題不大。是的,問題不算大,最后確診輕微腦震蕩,歇四周歸隊。但跑不動,出球慢,轉(zhuǎn)身也慢,基本和從前那個保羅·斯科爾斯一樣驍勇的中場后腰說再見了。從前他多他媽能跑,900平方米的球場也容不下他。下場后我不敢看他眼睛,也不敢看他腦袋。估計后腦勺有手指寬的疤。他向兄弟們復(fù)述斷片前一秒——黑暗,針尖大的黑暗。
張勇咋了他喝酒?
“我告訴他,只要看上我公司任何一個姑娘,我立馬牽線。他不說好,不說不好,三拳打不出個屁。只認得喝、喝。喝多了就躥我樓梯上……”
我們收東西撤離海埂三號場。晚霞在低空燃燒,腳底優(yōu)質(zhì)的小葉草撲哧響,像浸水的毯子。我們在停車場道別。不能放任不管了。不能不管管我們的保羅·斯科爾斯了。他直著脖頸,朝我揮了揮手。
黑暗。針尖大的黑暗。我想象不出來。
段凡四十三了,沒結(jié)婚,沒女人。我猜這是他從樓梯上往下跳的原委。當(dāng)然啦,他不會承認。我了解他,比他自己更了解他。當(dāng)年我將一個家境不錯、大學(xué)本科的高中同學(xué)介紹給他,他見了面,一聲不吭。桂子把一個離婚出納帶到他面前,他整晚就說七個字,“請把那瓶酒給我。”小寶前后為他張羅三個,沒一個讓他開口。狗日的段凡,他手拎啤酒,縮進墻角,管你三七二十一。煩透了。我們煩透了。人過四十,要相親結(jié)婚就太難了,就像七老八十還想滿場飛奔。
我打他電話。
“睡了?”
“沒有。三點英超。”他說。
“你到底咋想?”
“想哪樣?”
“為哪樣跳樓?”
“我說了。”
“你沒說。”
“哪樣也不想。”
“真不找個伴?”
“沒意思。”
“就足球有意思?”
“行啦老李。”
“你還真以為你能踢一輩子?”
“行啦行啦。”
“保羅·斯科爾斯有老婆,而且有三個娃。”
他不吭聲。我能聽見他呼呼喘息。他好像又喝高了。也許滿地啤酒瓶。
“你聽著,”我一字一句地說,“2003年,斯科爾斯累積黃牌錯過歐冠決賽,最后曼聯(lián)奪冠,斯科爾斯從兩層高的看臺上跳下來——對,跳下來,死死抱住弗格森。”
他掛了電話。
狗日的。
他要傻到什么時候?
周五,大伙在彭翔樓下小酒館喝酒,酒館老板問何時結(jié)賬,小孫操著標準的東北普通話說,“你怕咱不給錢還是咋的?喝到明早上,咋的?”老板嚇壞了,“幾位大哥,要哪樣,只管說。”
凌晨一點,昆明的金色燈光洋洋灑灑,彭翔表妹及其閨蜜出場了。表妹的閨蜜一頭長發(fā),打著小卷卷,穿低胸夾克,緊身牛仔褲,身材火辣。大伙明白了,彭翔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段凡。但是對于其貌不揚、除了足球什么也不愛的段凡來說,這姑娘綽綽有余,用鮮花和牛糞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小孫劉磊桂子們立即大獻殷勤。段凡亮出標志性動作:縮進墻角,垂著腦袋,一杯接一杯喝酒。
姑娘說,“我叫束薪。束河的束,柴薪的薪。”
桂子說,“我這輩子頭一回碰上姓束的。他姓段,段凡。平凡的凡。”
“我三十五。”她說。
“他四十三。”桂子笑了。
兄弟們使勁講些廢話。之后,彭翔問她,“你喜歡足球?”
“喜歡。最愛英超。”
段凡看了看她。
“哪支隊?”彭翔說。
“曼聯(lián)。我是二十年曼聯(lián)鐵粉。最愛保羅·斯科爾斯。太偉大了。平凡的偉大。弗格森退位,斯科爾斯掛靴,曼聯(lián)找不著北太正常了。穆里尼奧有戲,曼聯(lián)會越來越好。小將拉什福德不可限量。”
“不喜歡小貝?”
“我說的是最。最愛斯科爾斯。”
段凡扛不住了,從墻角磨磨蹭蹭過來,小聲說,“保羅·斯科爾斯哪年的?”
“1974年生于索爾福德,92班主力,為曼聯(lián)出戰(zhàn)718場。”
段凡血往上涌,像被某種東西鉗住了。一個漂亮女人,一個懂球的漂亮女人。二十年來的偶像非斯科爾斯莫屬。他一直模仿斯科爾斯——不惜體力地奔跑,傳球簡潔、再簡潔。平凡的偉大,說得多好。斯科爾斯效力曼聯(lián)三十年,誰都可以蓋過他,誰也取代不了他。當(dāng)他不上場的時候,曼聯(lián)就不那么穩(wěn)當(dāng)了。段凡在我們球隊的地位差不多與斯科爾斯相當(dāng),他總愛引用齊達內(nèi)的話,“斯科爾斯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球員,沒有之一。”
彭翔讓他和束薪坐一起。兩人一直聊英超,很多八卦我們聞所未聞。后來彭翔讓他送她回家,他也很想送她回家,雖然嘴上不說。他們在街邊打車,段凡坐副座,束薪坐后座。車子沿長春路飛馳,他好幾次想悄悄回頭,但每次都被刺眼的路燈嚇退了。
“你從小踢球?”她說。
“……初中。”
“沒進校隊?”
“沒有。”
她忽然笑了。
“對不起。我不是——”她說。
他沒吭聲。
“你周末有空?”她說。
“周六,踢球。”
“我想去怒江。一起?”
“……開車?”
“對,自駕。輪流開?”
“……”
“明天之內(nèi),一定給我答復(fù)。”
凌晨三點,他打開電視,切爾西對阿森納,藍軍3比2險勝。他不如從前激動,也不再覺得非看不可。自從保羅·斯科爾斯退役,英超就沒那么牛逼了。就像馬拉多納之后的阿根廷,羅納爾多之后的巴西。他想起斯科爾斯對陣利物浦的35米遠射,想起他滿頭金發(fā)和靦腆笑容,想起他飛奔時有些寬大的曼聯(lián)球衫。接傳球太干凈了,像風(fēng)掠過冰面。他起來,打開一瓶啤酒,喝到一半,比賽結(jié)束。他關(guān)掉電視,躺下。第二天沒去單位——他那個工作去不去無所謂。下午,他給束薪發(fā)了一條短信:怒江。
這差不多就是段凡和束薪初識的過程。現(xiàn)在,我把它寫成小說冒著相當(dāng)大的風(fēng)險——寫出來的未必是真的,何況未經(jīng)兩位同意。是啊,我沒征求他們意見(需要征求嗎?)算了,何必擔(dān)心一個摔壞腦子的傻瓜——上上禮拜,大雨天,他居然跑到海埂3號場,打電話問我咋沒一個人?我說,小蔣沒通知你下雨改期?他沒說話,背景是噼里啪啦的雨聲,間或有電閃雷鳴。
“就我一個人,老李。就我一個。”
“行啦。等著,我過來。”
我趕到海埂,雨小了些。我停好車,撐傘往里走,遠遠望見段凡打一把黑傘立在3號場邊,粗大的桉樹站在他身后,像暗黃的巨人。雨點敲打草皮,發(fā)出清脆的吱吱聲。
“抽煙?”我問他。
他搖頭。
我取一支,點上。昆明遇雨成冬,真他媽冷。
我抽完一支,又取一支,點上。
放眼望去,1號、2號、3號、4號、5號、6號場不見一個人。連綴的草皮像一片綠海。
雨勢不減,風(fēng)越來越?jīng)觥?/p>
“走吧?”
他不吭聲,一手揣兜里。
“不走?”
等于白問。
雨點噼噼啪啪打在桉樹葉上。草地上的雨聲弱下去了。
“當(dāng)年,當(dāng)年下多大的雨也要整啊。”他說,“1997年、2003年……記得嗎,老李?”
我說,我記得,都記得。海埂爛得像秧田,大雨如注,我們上場玩命。球落在過腳面的積水里動彈不得,你必須使勁捅它、踹它,像犁地一樣把它弄到干一點的地方才能往前推進。早就不講技戰(zhàn)術(shù)了,全在爛泥里摸爬滾打。真過癮。真是過癮。雨水汗水海埂臭烘烘的爛泥糊住你的臉,讓你喘不上氣,讓你激動得像要渴死的馬。
“今晚英超?”我說。
“南安普敦打桑德蘭。”他說。
“回吧?找地方坐坐?”
“還是斯科爾斯牛逼。”他說。
“行啦。”我說。
“跑幾圈。”
我沒法反對。我為他撐傘,他脫了衣褲,換上行頭,轉(zhuǎn)身扎進雨里。噼里啪啦的跑動聲相當(dāng)空曠,像巨石錘擊大地。白色水花在他老邁的耐克鞋釘下飛濺。他掠過我,將海埂基地黑乎乎的惡臭甩我一臉。
段凡七天后回來的,那場野球束薪并未光臨,讓我們的期待落了空。他照樣跑不動,遲緩、疲憊,像垂死的狗。桂子說,他肯定在怒江途中把自己一次性掏空了。我們哈哈大笑,意淫各種場面,想象他們從昆明——怒江近千公里的漫長旅途中,租住一個又一個破爛小旅館,把劣質(zhì)小鐵床折磨得吱吱叫,讓隔壁的人拍墻大罵:狗日的,輕點嘛。
段凡扇他們嘴巴,桂子小蔣小孫兔子一樣逃竄。彭翔將他拽到場邊,問他進展如何,他一聲不吭。彭翔急了,有進展,還是沒進展啊?段凡說,狗屁進展,回家!
后來我才知道,段凡、束薪在怒江開過一間房,但是,他連她手都沒碰過。
這還是爺們兒干的?
兄弟們罵他“裝逼”“哄鬼”。只有我信他。是的,我信。我們認識太久了,他二十四、我二十二那年就組建了“紅番”足球隊,打遍昆明無敵手。我太了解他啦。他這輩子除了足球誰也不愛,除了斯科爾斯誰也不愛。多年來英超必看,無論多晚,他一定提前五分鐘起來。沒女人。一個也沒有。一個男人怎么能沒有女人呢?他不是gay,當(dāng)然不是。可到底是什么東西妨礙他找一個女人,哪怕和她睡上一次呢?
去怒江途中,他們第一夜住大理,各要了一間房。次日,束薪說兩間房太浪費了,不如就一間?段凡沒吱聲。別克昂科拉沿大理——保山高速穿山越嶺,公路正前方,黛青色高山氣勢雄渾,河流在峽谷里飛奔;太陽劃過山脊,余光閃閃發(fā)亮;當(dāng)寬闊的大河突然出現(xiàn),他的心怦怦跳。來到怒江——保山岔道口,他換束薪開車,以一百碼速度沖上怒江高速。山越來越陡,像巨人刀削斧砍的廢墟。束薪聽一張《綠洲》專輯,進入瀘水才換了張學(xué)友的老歌。束薪說,你一個踢球的不熱愛搖滾?他不知該怎么回答。一直聊足球,她竟然知道當(dāng)年皇馬來昆明時小貝的房間賣出了什么價錢;還能說出1982年、1986年世界杯決賽首發(fā)名單。絕大多數(shù)時候,他只能羞愧地擔(dān)當(dāng)聽眾。天擦黑時終于抵達六庫——怒江州府所在小鎮(zhèn),找到一家整潔的小旅館。她就開了一間房。
他后來講,這是他度過的最驚心動魄的夜晚,沒有之一。
進門后,束薪翻出一堆東西直奔衛(wèi)生間。他打開電視,衛(wèi)生間的流水聲高一陣低一陣。屋里一股霉味。也許一小時,也許更久,她終于托著毛巾包裹的長發(fā)出來了,身穿自帶的白色睡衣。
“你去吧。”她說。
他三下五除二,盡可能不發(fā)出多余響動。出來時穿得整整齊齊。她選了靠墻的床躺下,兩腿交叉,小腿裸著,亮得耀眼。他在空床上坐下來。她盯著電視。倦意和興奮同時壓迫著他。
“喝茶嗎?”她說。
他沒說行,也沒說不行。
她給他泡了自帶的普洱,茶味清淡。他側(cè)過身,忽然發(fā)現(xiàn)她距離自己如此之近,最多二十厘米吧。
“累嗎?”束薪說。
“還好。”
“你這人有意思。話不多,四十老幾了還單著。談過幾個?”
他不吭聲。
“你不會是彎的吧?”她笑了。
“不是。”他說,“高中的時候,高中的時候我喜歡過英語女老師哩。”這話說出來,他自己也嚇著了。
“真的假的?”
“真的。還寫過一封信。”
“哈哈,看不出來,你還有這膽子。”
“是,我也覺得……”
“回信了嗎?”
他拉過被子,墊在腦后,搖搖頭。
“哈哈,你有種。”她說,“后來呢?一直單著?”
他想不起來。似乎有過一個,又似乎算不上。是二十年前剛大學(xué)畢業(yè)分來的同事,地道的昆明姑娘。也就吃吃飯,看看電影。手都沒拉過。
“大哥,你四十三了。”
他又沒話了。
“我好過三個。”她說,“第二個差點結(jié)婚。要不是我發(fā)現(xiàn)他玩劈腿——媽的。”她停下來,像在等他說點什么。可他一言不發(fā)。她繼續(xù)說,“除了這點,他人很好。一直很好。”
他實在不知道該說什么。
“我怎么覺得地板在抖呢。就像還在車上,還在往前走。”她說。
“嗯。”
“抽煙嗎?”
“不抽。”
“介意我抽嗎?”
“你隨便。”
她下床,從箱子里翻出一包女士煙,很細,很白,像一截細小的骨頭。她點上,慢慢吸了兩口。煙味發(fā)甜,一點也不讓人討厭。
“你什么時候踢球的?”
“初中。”
“對對,你說過,沒進校隊。”
“殺手李是校隊主力。我們當(dāng)年一所中學(xué)。我比他高兩屆。”
“你那么愛足球,居然沒干過專業(yè)隊。連半專業(yè)也沒干過。”
“我喜歡的作家海明威說,想一想,不也挺好嗎?我想象自己……進曼聯(lián),不也挺好的?”
她哈哈大笑。
之后她將抽一半的煙按滅。
“那個差點跟我結(jié)婚的,第二個,劈腿那個,是紅塔的。你也許認識。”
段凡差點從床上蹦起來。他轉(zhuǎn)身看她,像打量一把鋼刀。心里忽然空空的,沮喪而辛酸,還有淡淡的苦澀。
“哪個?”
她說出名字。他當(dāng)然認識。紅塔*尚未解散之前的主力邊后衛(wèi)。
長長的沉默。
“他兒子都打醬油了。”她鉆入被窩,關(guān)掉電視。他沒動彈,還穿著外套長褲。
“你記得紅塔的最佳進球嗎?”她說。
他沒回答。
“就是他進的。主場打青島,過中場一腳怒射。世界波啊。”
他仍不說話。
她熄了燈。深沉的黑暗讓他想起《綠洲》的歌聲,還能聞見甜絲絲的女士煙的氣味,似乎有月光掩映過來。他不確定。當(dāng)他以為她已經(jīng)睡著時,忽然聽見她說,“他踢得真不比斯科爾斯差。”
“……位置,位置不一樣吧。”
沉默。
“我說真的。”她說。
“斯科爾斯老婆叫克萊爾,青梅竹馬。”她說。
“三個娃,老大阿隆、老二艾麗西亞、老三艾登。”她又說。
“是啊。”
“生活簡單之極。訓(xùn)練,比賽,回家,帶孩子,看電視,睡覺。”
“多好的男人。”他說。
“乏味又完美的男人。”她說。
他睜大眼睛,回想斯科爾斯的遠射和飛鏟。
“看出來了,你是真愛他。”她說。
“是。”
“一丁點緋聞也沒有。”
“從來沒有。”
“球場上幾乎沒有瑕疵。”
“是啊,是啊。”
他感到保羅·斯科爾斯的激流在房間里交匯涌動。他坐起來,靠著床架。他看見她也坐起來,發(fā)出窸窸窣窣的聲音。
“偉大的斯科爾斯,”她說,“偉大的保羅·斯科爾斯。”
他覺得身體在黑暗中微微發(fā)顫。
“嘿。”她說。
“嗯?”他說。
“我過來?”她說。
腦袋嗡嗡響。
“行嗎?”她說。
他沒說行,沒說不行。他看著她起身湊過來。他感到她在床邊坐下。他想起他在現(xiàn)場觀看過的她的前前男友,想起那粒遠射世界波——他可是當(dāng)年紅塔球迷協(xié)會的鐵桿啊。
“算了吧。”他說。
她一動不動。
“算了。”他說。
束薪緩緩起身,回到床上,躺下。再也沒說一句話。他背對著她。偉大的保羅·斯科爾斯消失了。黑暗比黑更黑。他心里涌上莫名的厭惡和悲哀。對自己、對一切、對這趟遠行。真黑啊,還能聞見女士煙的香氣。他比任何時候都厭惡和悲哀。他想立即入睡,卻遲遲睡不著。她要再來,咋辦?可他非常清楚,她不會過來了。不可能了。雖然他們之間也就短短幾十厘米。后來他做了一大堆亂七八糟的夢,次日天不亮就醒了,下樓給她買了早餐。她起床洗漱收拾。兩人又恢復(fù)到此前狀態(tài)。一種刻意的拘謹,勉勉強強的客套。當(dāng)然啦,他還能感覺到她冷冷的敵意。自找的啊。她肯定恨他,恨得要死。卻又不得不更加親密一些。他也痛恨自己。可誰規(guī)定了——上帝規(guī)定的?——他應(yīng)該而且必須那么干?
他們又分開了,各開各的房,各付各的房費。只在怒江待了兩天。也許太累了。是很累。除了奔騰的河流就是巍峨的大山,縮在峽谷里的小縣城越來越無聊;到處是奇裝異服的傈僳族、怒族,看多了也就那么回事吧。返程途中,兩人話越來越少。回到大理,她說她要留下待幾天,見幾個朋友。他識趣地去往長途車站,買了回昆明的車票。分手之前,她淡淡地說,“保重。”
“保重。”
這差不多就是怒江之行的全部了。他該遭到全隊唾棄,不過,考慮到他摔壞了腦子,偶爾出點狀況也是可以原諒的。我們猜想,他跳下來那一下子是否把老二也摔斷了?可憐的段凡,可憐的四十三歲老男人段凡。仍像過去一樣,他每場野球必定頭一個來,最后一個走;上場前必定繞場慢跑,必定聊到曼聯(lián),必定聊到保羅·斯科爾斯。
“你到底咋想?”我說。
“嗯?”他說。
“斯科爾斯大兒子都進職業(yè)隊了。”我說。
他坐著,一動不動。
“你說話。”我說。
他總算抬頭望我:“老李,他從看臺上跳下來,抱住弗格森。你猜他們說些什么?”
“我管他媽的說些什么。”
“弗格森問他,保羅,你還能踢幾年?他說,你讓我踢幾年,我就踢幾年。”
我一聲不吭。
“老李,你讓我踢幾年,我就踢幾年。”
“媽的。”我說。
海埂的落日余暉像燃燒的大海,點水雀在場邊溜達。
“他和他老婆是青梅竹馬。”他說。
我煩了,真煩了。這場球他還是跑不動,反應(yīng)慢,失誤多。我懷念過去那個跑不死、打不垮的段凡,那個昆明業(yè)余球壇的保羅·斯科爾斯。誰不熱愛保羅·斯科爾斯?下半場他有機會為我送出妙傳,但他忽然慢下來,拖著步子,低著腦袋。我沖他大吼,沒用,他像殘廢的斯科爾斯一樣不知咋辦。對方后衛(wèi)反搶得手,從他腳下輕松斷球,大腳開上去。
“我操你媽!”我大罵。
下了場,他說他被太陽直射腦袋,被熱汗糊住眼睛的0.09秒,就像從張勇樓上一頭栽下來。黑暗。針尖大的黑暗。
“老李,你要是不讓我踢了……”
“閉嘴。”
他慢騰騰脫下老掉牙的耐克鞋,脫下汗?jié)竦那蛞虑蛞m。
“該換雙新鞋了。”我說。
“還行。”他說。
“我陪你。踢一年是一年。”我說。
他汗?jié)竦哪橀W閃發(fā)亮,像銅鑄的斯科爾斯。是的,我早就發(fā)現(xiàn)他長得還真有點像保羅·斯科爾斯。
“英國《太陽報》上說……”他說。
“哪樣?”
“《太陽報》上說……”
“有屁快放。”
“斯科爾斯處男之身一直保持到新婚之夜。”
“哄鬼哩。”
段凡背起行頭往外走,我趕上他,死死按他的肩。他濕漉漉油膩膩的脖頸弄得我滿手是汗。
“你是段凡。記住,你他媽除了段凡哪個也不是。”
他一把將我搡開,走向那輛老邁的奇瑞。
小說寫到這里,我也有點蒙了。下面怎么寫?段凡的結(jié)局無非兩種:A,踢下去,直到顫顫巍巍年過半百不得不放棄。B,就此掛靴,找個女人,踏踏實實結(jié)婚生子。他會怎么選?換了你,怎么選?
我要是段凡呢?
他約束薪出來是四月的第一個周五,晚八點,翠湖邊城堡書吧。束薪早到了十分鐘。這是他的說法。如果再順著他的講述往下捋,你會發(fā)現(xiàn)后面每一個細節(jié)都順風(fēng)順水,與后來的意外扯不上半點關(guān)系。
好吧,我慢慢講。
他們都有點局促。尤其段凡。怒江之后,他頭一次約她見面。她呢,根本沒聯(lián)系過他,對他充滿莫名反感,似乎遭到了羞辱。當(dāng)他打來電話,她卻心軟了,答應(yīng)見一面。段凡后來承認,他挺喜歡她的——你上哪兒找這么一個骨灰級球迷?而且長相、身材沒得說。他,一個四十三歲老男人,錯過這個村可就沒這個店了。
“都好?”他說。
“都好。你呢?”
“老樣子。周六照例海埂,3號場。”
“抽空,我去看你踢球。”
他臉紅了,“我們業(yè)余隊,只是鍛煉身體。不過,說實話,我踢得不錯。”
她笑了。她笑起來很好看。
“最近看沒看英超?”她說。
“看,每場必看。”
“曼聯(lián)越來越好啦。”
“剛剛2比0拿下切爾西——”
“愛死穆里尼奧了。”
“我更喜歡當(dāng)年在切爾西拿歐冠的穆里尼奧。”
“哈,他手里就缺一個斯科爾斯。”
“誰比得了偉大的保羅·斯科爾斯。”
足球能一直聊下去。曼聯(lián)能一直聊下去。斯科爾斯能一直聊下去。
“還記得斯科爾斯怎么退役的?”她說。
他故意眨巴眼睛,賣賣關(guān)子,“啊……忘了。”
“2013年5月12日,曼聯(lián)2比1拿下斯旺西。斯科爾斯最后一戰(zhàn)。老特拉福德全體觀眾起身鼓掌。斯科爾斯什么表情?”
“很平靜,非常平靜。”
“你不是沒看嗎?”
“哈哈。”
他回憶斯科爾斯跑動、射門、傳球。兩臂像天使一樣張開。
后來他提議是不是喝點酒。啤酒或紅酒。他知道城堡書吧不賣白酒。束薪說,來點紅的吧。趁她上衛(wèi)生間的工夫,他發(fā)現(xiàn)書架上竟有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他翻到最后一頁,“羅伯特·喬丹匍匐在松針上,聽見大地回蕩著自己的心跳聲,撲通,撲通。”他激動起來,不知為什么。后來他們喝掉一瓶紅酒。再后來,他們都不說話。窗外很暗,看不清尿黃色的路燈。她提議出去走走。那就走走吧。
他起身結(jié)賬,太陽穴也許因為酒精的作用砰砰跳,就像那天夜里從樓梯上跳下來。他想起瀕死的羅伯特·喬丹。偉大的海明威啊!外面是文林街。周圍太吵,索性和她沿小吉坡下行,右轉(zhuǎn)來到翠湖。小吉坡幽暗陡峭,束薪似乎挽了他的胳膊,又似乎沒有。此時,路燈將長長的雪杉影子投下來,翠湖昏暗不明,空氣中有濃重水味。沒人說話。他們步調(diào)差不多一致。她的高跟鞋在水泥石板上敲打。遠處出現(xiàn)大片霓虹,像長長的透明的羽毛。他們停下來。她說,
“我們——”
他望著她,心臟怦怦跳。
故事進行到這里,基本塵埃落定了。我就這么想的,小說就此落筆不也挺好?不。這不是結(jié)局。我說過后來的事情出人意料——現(xiàn)實和虛構(gòu)總是天壤之別呀。那天我接到張勇電話是凌晨三點,他說他和段凡在翠湖派出所。是段凡給他打的電話。他覺得我必須來。我開車趕過去。出事地點在小吉坡,也就是城堡書吧與翠湖之間一條狹窄的小巷,光線昏暗,坡度很陡。他說他約了束薪,她來了,而且早到十分鐘;他們聊得很好,非常好;然后他們從小吉坡一路溜達到翠湖南門……“行啦,”張勇打斷他,“你編,繼續(xù)編!”真相是,當(dāng)晚他主動約了她,可她沒來。他從八點等到十二點。他一直望著門外,文林街喧鬧不已,刺眼的霓虹射在玻璃窗上。她沒來。就是沒來。他沒給她電話。她呢,連個短信也沒有。他從書架上抽出《喪鐘為誰而鳴》,讀了十來頁,又要了兩瓶紅酒,咕咚咕咚喝個干凈。之后結(jié)賬,出去,斜插小吉坡,在坡道中段抓住一個年輕姑娘,不容分說又摸又抱。姑娘掙脫后報警。他沒走幾步就出溜到墻角了。紅酒后勁太大,否則,以他踢球的腳力必定輕松逃脫。他就是這么交代的——醉了,不太記得干了哪樣,為哪樣這么干。
姑娘瘦而高挑,長頭發(fā),相貌毫不起眼。男朋友趕來要揍段凡,被警察喝止了。段凡酒勁全消,給張勇打了電話。還能咋辦?我們忙不迭賠禮道歉,向姑娘解釋段凡摔壞了腦子,人是傻的,做事沒譜,更別說還喝了那么多酒。后來張勇悄悄往姑娘坤包里塞了幾千現(xiàn)金,她總算消停了。派出所訓(xùn)斥我們一通,放人。
我們坐張勇的車送他回家,路上沒人說話。到他小區(qū)門口,我們忽然哈哈大笑,笑得眼淚都出來了。我打擊段凡,“這女的這么丑,你他媽瞎呀?”
他垂著腦袋,嘿嘿傻笑。
我又坐張勇的車回翠湖派出所取我的車。我們沒說一句話。
我取了車,與張勇道別。凌晨五點,天空像井一樣黑,再過半小時就該天亮了。我在車里點一支煙,狠狠吸。不想馬上就走。不想。我呆坐著,文林街頭涌來一批渾身荷爾蒙的小子,臉色發(fā)青,嗓門很大;城堡書吧的橘色門楣和咖啡色招牌相當(dāng)扎眼,讓你想起曼聯(lián),想起小貝,想起斯科爾斯。對過二十米就是小吉坡,入口深邃幽暗,簡直深不見底。我垂下腦袋。突然發(fā)現(xiàn)很想他,想念這個剛剛分開的兄弟。我撥過去,他說,剛洗了澡,睡下了。
“今晚有英超?”我說。
“明晚,斯托克城打熱刺。”他說。
“幾點?”
“三點。”
“要看?”
“看。”
“明天海埂,莫忘了。”
“忘不了。”
周六,我堅持送他一雙嶄新的“刺客”,段凡死活不要。事情鬧僵了,好在無人嘮嘮叨叨,就連段凡照樣跑不動、跑不快也沒人說了。我忽然發(fā)現(xiàn)一個事實——他媽的,我們這票年過四十的老家伙,都跑不動了。
“你不要,老子翻臉。”我說。
“再逼我,老子翻臉。”段凡說。
最終聽張勇的——段凡花八百買下“刺客”,我用這筆錢請大伙吃飯喝酒。
下一場,下一場比賽,段凡將蹬上“刺客”。我想象這個摔壞腦子的老男孩猶如腳踩風(fēng)火輪,就像從未缺席的保羅·斯科爾斯,我們的同齡人,跑不死的鐵血中場。也許束薪會來看他踢球的。這種事情,哪個也說不準。
(*:云南紅塔隊曾經(jīng)是云南唯一的中超球隊。后因資金原因,于2005年突然宣布解散。)
作 者簡介
陳鵬,男,1975年生于昆明。國家二級足球運動員。小說家。現(xiàn)任大益文學(xué)院院長。曾獲《十月》文學(xué)獎等多種獎勵。
(標題書法:周潤天)
責(zé)任編輯 張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