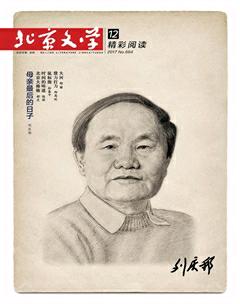鄉愁片羽
李成琳
題記:古鎮、古寺、古城、古石刻、古城墻,故居、書院、舊畫展……每一處遺存都可以牽出一段溫情的記憶,折射著我們內心的憶念、向往與鄉愁。
一
離開巫溪的那天清晨,去了大寧河畔的寧廠古鎮。
曾經在朋友的書里,通過很細致的文圖“踏訪”過這里,印象深刻。但身臨其境,當青綠的河岸上若電影的搖鏡頭般呈現那綿延數里的蒼老的房屋時,還是有一種柔軟的情緒如水般漫上心田。滄桑,也可以讓人凝住腳步,屏住呼吸。
古老的寧廠,不單單是中國最早的鹽業生產地,不單單是中國西南最早的集鎮,也不單單是吊腳樓建筑模式最早的起源地,它還是《山海經》的故鄉,是先秦時期巴文化和楚文化重要的發祥地之一……
流淌了五千年的鹽泉,依然年輕,充滿活力與靈動。掬一捧來喝,清朗的咸、清澈的純,讓人回味。而與之對應的,是河對岸觸目驚心的衰老。
跨過搖搖晃晃的吊橋,實地踏訪曾經繁盛至極,如今蕭條至極的古街老巷。隨處都是廢園,荒草萋萋。那一座座行將垮塌的吊腳樓里,曾有怎樣的笑語?那一扇扇緊閉或開啟的木窗木門邊,曾有怎樣的歡聲?一只白色的貓棲在墻頭,一朵寂寞的花開在山前。有一種沉默卻延展的憂傷,也有一種內斂而質樸的定力,峰回路轉,扣動心弦。
二
佛光寺。它是五臺山之行最大的驚喜。
一個偶然的提議,因為梁思成和林徽因曾經的造訪,也因為我記憶里的似曾相識,我們決定多繞幾十公里的山路,去五臺山外圍的佛光寺看看。
七十七年前,梁思成曾有這樣的記敘:我們騎馱騾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著走,沿倚著崖邊,崎嶇危險。下面可以俯瞰田壟……近山婉婉在眼前,遠處則山巒環護。旅途十分僻靜,風景很幽麗……瞻仰大殿,咨嗟驚喜,我們一向所抱著的國內殿宇還必有唐構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個證實了……
我們乘車入山,山路已不似當年的陡峻崎嶇,但依然僻靜而幽麗。寺前下車,便見一松幾乎橫臥于地,枝丫卻伸出崖外,繁盛蔥蘢。進得寺內,幾無游人,牡丹卻艷紅得正盛,古樸的大殿掩映于林木森森的高臺之上,那樣的恢宏和靜謐,仰視之間,全無他念,連咨嗟驚喜都顯輕慢一般。終于進得殿去,有大唐風韻的泥塑雖然因民國初年的重新著色稍顯唐突,但仍能從脫落的地方看到當初淳古的色澤。更有原汁原味的唐代壁畫,充滿了滄桑的圓潤和流暢,吸引你靜聽千年時光的聲音,有讓你落淚的力量,欲罷不能。
是因為地處“臺外”,才葆有了千年古剎的風貌?是因為身處“邊緣”,才成就了中國現存最古老木構建筑的美譽?
回家后,翻看《林徽因傳》,終于找到對佛光寺似曾相識的理由:239頁到243頁,全部記錄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考察測量佛光寺的過程。重溫文字的過程,恍若重游佛光寺的過程。
三
有的地方是值得反復重溫的,即便匆匆。
榮昌城外的安富古鎮。“金竹山,瓦子灘,十里河床陶片片,窯火燒亮半邊天,窯公吆喝悍聲遠。”流傳了幾百年的民謠,是古時安富陶器盛況的真實寫照。我們抵達時已是下午,古鎮不古,盛況不再,迎接我們的是它的空曠、閑散和熾熱的陽光。
安陶博物館,以它流傳有序的陶器物和陶片片牽引著我們的目光。在模擬的窯火前,把自己遙想成一方漢陶,以粗獷、樸素的線條和姿態,于反復的淬煉中,讓自己結實、堅韌而明亮。
那個下午,便在陶器間流連。制作的神奇,雕飾的靈感,觸目而生的心動,一手在握的質感,還有那熟稔到兒時記憶的親切,當然,也有悵惘和遺憾。
告別安陶,已近黃昏。
在近晚的余暉里,重溫路孔古鎮。即便匆匆的領略,仍有一些溫良的氣息,如蒸籠里揀出的艾粑粑,糯糯的,甜到心底。
陶,是泥與火的結晶。古鎮,是記憶與時光的交響。
四
昨日雙桂堂,今日老君洞。前為西南佛教禪宗祖庭,后為川東道教第一叢林。步履重溫之間,仿佛在時光隧道里往返穿行。
梁平雙桂堂于清順治十年(1653)創建,迄今剛好三百六十年。盛夏時去過,天大熱,汗淋漓。因為數百年的殿宇婉轉幽深,因為“第一禪林”的聲名端正悠遠,因為那些長亭短榭回廊曲巷的安靜和平,便有一縷涼意從熱汗里滲出。昨日于寒風細雨間停留,于竹禪墓塔前,燃香,鞠躬,似有憶故人溫熱又淡遠的述說娓娓而來。同樣的地方,有了不一樣的心得。暑寒二度雙桂堂,均因竹禪而往,因古琴而往。“松風入處白云深,時有僧徒學撫琴。流水聲圓山曲折,閑中一聽一清心。”錄竹禪知音雪堂《聽琴》詩以記。
南山老君洞始建于三國時期,正式創建于隋末唐初,明成化十六年(1480)重建,僅此已有五百三十三年的歷史。吸引我們雨中訪道的明代摩巖石刻也完成于明成化年間,五百多年的風雨也難掩漁樵耕讀的形神兼備和伯牙子期的栩栩如生。此地多次登臨,保存如此完好的撫琴圖卻首次得見。今日因此圖而往,收獲的卻不僅于此。“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錄東門對聯以記。
五
銅梁,古安居城。又一個浮出水面的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九宮十八廟,明代古城墻,朱門花窗鉛華洗盡,尋常巷陌縱橫交錯,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養在深閨人未識。
抵達城下,見工地正在進行時,多少有些掃興。進城去,卻見青石板鋪成的老街,串起黛瓦白墻,亭臺樓榭,古舊殘壁,這是一座無意張揚的小城,即便有燈籠酒旗,雕梁畫棟,但整體的氣息是安靜的,有一種傾聽的姿態,就像那些觸目可見的木雕磚雕石雕,靜靜地闡述著瞬間和永恒的關系,怎樣的驚嘆都不會驚擾它們的安詳與淡定。
“禮樂長承燕翼,詩書永荷龍光。”在瓊涪兩江清流圍繞的城隍廟高臺上,風乍起,吹得我的長裙若長發飄飄,是江風、山風,還是古風?風里傳遞的,依然是歲月安居的清爽和安然。
六
endprint重溫大足寶頂石刻。午后的陽光,于濃蔭下依然熾熱。熱汗淋漓,心卻清涼,一尊尊生動的造像,一張張安詳的面目,一個個寧和的手勢,一道道飄逸的裙裾,凝視,仰望,感覺,體味。近千年歲月侵蝕的滄桑之美,近千年歲月淘洗的藝術之美,大氣而細膩,寬廣而溫厚,堅定而樸素,若安然自適的夢土,讓人安頓。
所謂經典,就是值得反復閱讀的作品。寶頂山,多次造訪,反復閱讀,有時讀到修行,有時讀到降住心魔,有時讀到一切由心造。每次閱讀都是未完式,如寶頂山下最后那些未完成的造像,給人更多寄予和聯想。
子夜歸,雨傾盆,恍若將白天的熱汗傾回。涼與熱,雨和汗,都是通透,都是良辰。
七
鳳凰古城,十年前來過。
記得是春天,來重慶最東南的秀山講課,因為近靠邊城,所以自然講到沈從文,講到沈先生的“希臘小廟”。課后的某天,去了邊城,也來了鳳凰古城。因為沈從文故居的安靜,我原諒了古城當時的大興土木,原諒了熙熙攘攘的人流和日益興盛的商業氛圍。
今天的鳳凰,因為七月的洪水,觸目皆腳手架,橋、塔、樓、院,都在修復中,卻依然人多物盛。幸好河水是清澈的,倒影下的綠樹是蔥蘢的,白墻灰瓦下的小街巷是安詳的,沈從文故居的藍花花窗戶依然滄桑又親切。同行的文友在故居書屋一人買了一本沈先生的書,又找到一家正宗米酒店, “鄉下人”的“甜米酒”讓我們微醺,出得店門,已是華燈初上。
“塔靜梧高凌空引鳳,河清岸曲流水藏蛟。”徜徉河岸,燈火掩去了白日的傷感。歌舞升平里,有沈先生的話語穿越那些歌聲而來:美麗、清潔、智慧,以及對全人類幸福的幻影,皆永遠覺得是一種德性……生活或許使我平凡與墮落,我的感情還可以向高處跑去;生活或許使我孤單獨立,我的作品將同許多人發生愛情同友誼……
八
黑石山。始建于公元1868年的聚奎書院。
多年前來過,記得是個雨瀟瀟的春日,山色空漾,山葉滴翠,美樹香樟成林,翩飛白鶴成群,寫滿青苔的巨山石,以及山石上不時得見的優美題刻,步步驚艷!
今天在陽光下重溫,一屋一院,一石一樹,一字一句,一花一草。都有無限的和平與感慨。白鶴在香樟林間飛躍,撲扇出一幕幕的畫面:陳獨秀在這里做生命中最后一次演講,馮玉祥在這里緬懷白屋詩人吳芳吉,于右任用不同的書體題寫“奮乎百世,頂天立地,繼往開來”,還有梁漱溟、文幼章、歐陽漸、臺靜農、佘雪曼等文化名人在這里登臺講學。桃李芬芳,教澤長流,“是英雄鑄造之地,為山川靈秀所鐘”,書院里的對聯作了最精要的點睛。
“萬事盡如秋在水,幾人能識靜中香。”山前驢溪河水緩緩流淌,園中九曲池上落葉密布,春天的水以自己的面目靜靜地芬芳。
九
秋陽下的通遠門。久違了的老城墻。
這里是老重慶九開八閉的十七座古城門碩果僅存的兩門之一,也是我曾經每天“穿越”多次的地方。
媽媽的家在城門外的數百米處,我執教的學校在城門內的數百米處,曾經兼職的報社就在古城墻的邊上。通遠門是我的通近門。每天清晨、中午、黃昏或夜晚,都要從這布滿藤蔓的城門洞穿行。記憶中的它常年都濡濕而暗沉,年輕的我總是朝著洞口的亮光快速地穿過……
如今,老屋已非,老校已遷,陽光依然,老墻依舊,老樹盤根,歲月留痕。通遠門前青枝蔥蘢,城門洞內清爽陰涼,車流過,人跑過,風掠過,雨洗過,不改神色。
十
四川,廣安,鄧小平故里,第一次來。春陽的拂照下,綠樹濃蔭,花香滿徑。故里的感覺在淡化,就是一個春天的園子,講述著春天的故事。月季、山茶、迎春,還有若干不知名的野花,自在散漫地盛放。樹樹新枝,高高低低的欣喜,散發著新綠的香。一灣靜湖,天光云影共徘徊,轉過去,蓮葉何田田,鋪陳出別樣的風景。
故居前后,竹樹環繞。藍天白云下的嘉木凡樹,掩映著樸素的老屋。廳堂里“忠孝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的對聯,讓我想起另一副對聯,朋友說在鄧氏祖墓上看到的:“陰地不如心地,后人須學好人。”彼此呼應的,是樸素里的雋永恒常。
天黑了,風起了,涼意透徹,洗滌生命的塵埃,燈影里的樹葉像花兒一樣透明而輕盈。
沒有星星,沒有月亮,在暗夜里漫步,風清氣朗。
十一
午后漫步,又到博物館。本來因另一個展覽而往,看到“我的三峽記憶——伍必端寫生畫展”,為這樸實的展名所吸引。畫家伍必端并不熟悉,但他畫筆下的三峽及山城卻有一種熟悉的親切。展廳被隔成狹長的空間,兩百余幅大大小小的寫生作品仿佛順流而下,一路看過去,真有“輕舟已過萬重山”之感。
這些作品畫于上世紀70年代三峽蓄水之前,那些逝去了的不復存在的景象,讓人懷念又感慨。奉節古城、萬縣老街、大昌古鎮,都已全部沉入水底。孤帆遠影、兩岸猿聲、江石纖夫,也是很難再生的風景。喜歡那些用青灰色的調子,在淡淡的水墨里氤氳出來的充滿憶念的畫面,三十多年前的霧重慶,靜靜流淌的大寧河,靈動變幻的巫山云雨,青蒼茫茫的群山重疊。更喜歡那些有情有意的清新小景、山谷幽泉、橫石晨霧、大山樹影、山城小巷、黑瓦白墻、舊園、小溪、村莊、小橋流水、青翠田園、斑駁的山石、純藍的山色、陽光下的小樹叢,世外桃源般的安詳,純樸而寧靜。
這位中央美院八十八歲的老畫家,用這樣一個展覽回眸他在最好的年華里所記錄的最好年華的三峽。我相信他此后一定畫過三峽,但沒有一幅展出其中,畫上所留下的時間全部定格于1973和1979……
腦海里閃過: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
十二
平遙古城,十幾年前攜帶保存完好的古城墻、古街道、古店鋪、古寺廟、古民居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給出的評價是: “平遙古城是中國漢民族城市在明清時期的杰出范例”,并用“非同尋常”表達了驚喜和敬意。
可以說的太多,還是說說印象深刻的對聯吧。
戲中有文,文中有戲,識文者觀文,不識文者看戲。音內藏調,調內藏音,知調者審調,不知調者聽音。這是戲樓上的對聯,看似寫“實”,卻有讓人回味之“虛”。另一戲樓的對聯有異曲同工之妙:曲者曲也,雅曲內寫盡人情,愈曲愈直。戲豈戲矣,游戲中傳出物理,越戲越真。
作為晉商票號的集散地,看到“輕重權衡千金日利,中西匯兌一紙風行”這樣的對聯不稀奇,稀奇的是錢莊門前這樣的對聯:一榻琴書南北史,兩樓風月東西路。寄懷楚水云山外,得意唐詩晉帖間。琴書風月,山水詩帖,何其蘭芳桂馥!
再看看民居對聯:修身如執玉,種德勝遺金。樂天為事業,養志是生涯。花影云拖地,書聲月在天。再來聯長的:延晚景于桑榆,不外栽培心上地。 壽長令乎姜桂,只緣涵養性中天。心上地,性中天,怎樣的栽培和涵養,才能如平遙古城般地厚天闊、風清氣朗?
責任編輯 張 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