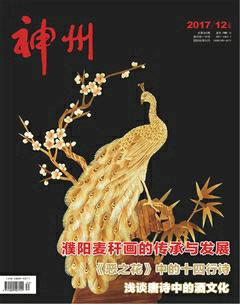從歷史多維角度分析決策者的政治邏輯
張若靜
摘要: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最高統治者的政治決策往往有著鮮明的主觀情感色彩,這種偏于個體主觀傾向的政治邏輯不僅影響了我國的歷史發展進程,而且也決定了政治的發展形態。從歷史發展角度來看,個體認知差異和外部的政治、文化環境因素是影響統治者進行政治決策的根本因素,居于最高統治地位的個體的政治邏輯影響著民族的變遷和歷史發展。鑒于此,本文就從歷史多維角度就決策者的政治邏輯展開詳細的分析,并提出具體性研究策略,以供廣大讀者借鑒。
關鍵詞:歷史;多維角度;決策者;政治邏輯
一、“焚書坑儒”背后的政治決策
從我國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歷史的環境因素、統治個體的主觀意識、國家的政治形態是影響統治者進行政治決策者的根本原因。面臨不同的政治局勢和外部環境變化,封建統治者是很少憑借個人臆斷進行決策的,往往是在綜合考量多種因素后,在自身政治能力范圍之內進行決策,以此來保障政策的適用行和決策的價值性。以秦始皇皇焚書坑儒為例而言,很多人稱他為暴君,但作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大秦帝國締造者,他的政治手段不得不令人佩服。滅六國,一統天下是秦始皇的輝煌業績,但不等于其政治統治就當如磐石,六國老世族無時無刻不想著復辟,各種力量扭曲涌動,統一初定的秦國暗流洶涌,如何維護政治統治,保持社會穩定是嬴政最擔憂的問題。
在胡亥亂政、陳勝吳廣大澤鄉起義后,國士儒生淳于越提出:“廢郡縣,立行王道,恢復分封”的政治主張。此時儒家老生老調重彈,并大以為非,其政治狂妄程度有悖常理。在這種表現的背后,顯然有強大的六國復辟力量在推動。面對如此形勢,丞相李斯痛加駁斥了以古非今的論調,揭露了儒家依附分封而存的立場,并倡導焚毀除實用之書、史學之書外的一切“王道之書和春秋古籍”。李斯的這種倡議恰恰驗證了他作為荀況得意門生的法家理論。對于嬴政而言,焚書只是政治威懾力大于破壞力的一種威懾手段。焚書的發起人是李斯,而其政治目的是遏制以古非今、阻礙變革,所以焚書坑儒不應該是秦始皇應該背的鍋,而其內在含義只是禁止私學,以達到思想控制和統治的目的。
嬴政燒書是為了統一思想,加強思想統治。但他并沒有焚毀實用之書,他網羅六國客卿并不專注于“秦法思想傳播”,反倒是博采眾長。至于坑儒,秦始皇主要坑的是術士。他只是坑殺術士,并沒有大范圍針對某一個學派進行迫害。客觀歷史說明,秦始皇得罪的是儒家的文化學者,于是乎遺臭萬年,事實上作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開創者,嬴政的功績遠遠大于過失,且漢承秦制才有了我國封建歷史上國家鼎盛的局面,所以說歷史多元形態下的政治決策往往具有一定的環境限制和時間因素影響,歷史事件不一定是真實的歷史事件,是經過后人修改、具有學派政治色彩的政治歷史。
二、儒家思想對統治者政治決策的影響
從我國歷史發展角度來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是基于儒家思想而形成的統治歷史和專制歷史,儒家文化的思想在歷史的事實闡述中占據了主導。從西漢初年,遵從“黃老之言”修養生息,恢復國力,到文景之治和漢武帝“罷戳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學說儼然成為了中國封建思想的正統。在這種尊崇儒家學說為核心的封建文化體制中,“武死戰、文死諫”被看做是文臣武將的最高使命和責任,過于封建和固化的意識形態,不僅在千年的帝制長河中抹殺了學者、文人的創造性,更是固化了民眾的人文理性和自然精神。“三綱五常”被看做是社會文化核心,倫理道德被看做最高的行為約束,在這種缺少理性精神的文化環境中文人學者從未有過任何關于實用之學、百家之術的創新,順從圣賢之言,遵從圣賢之訓被看做是最高的行為標準,統治者受到儒家封建思想主義的束縛,政治決策往往“以偏概全”,文化效果、政治目的和遵從“孔孟圣人訓”是決策的出發點,有悖于儒家倫理的決策往往被士子看作是荒誕不經的,統治者的政治邏輯深深局限在了儒家的倫理框架中,政治主體和個人意志是難以凸顯的。
三、儒家禮教對統治者的主觀行為的影響
偏重于封建禮教和儒家學說的政治體制和朝政環境注定了最高統治者只能在儒家文化價值體系下進行決策,而這種不帶有任何民主色彩和理性因子的政策行為既要上合“儒學天倫”、也要下合士子之心。封建王朝時代沿襲的政治體制是維護封建儒家和中央專權的核心所在,統治者必須在這種介乎人倫綱常和政治禮儀教化的環境中有所做,而不能是有所為。岳飛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在他的觀念中保家衛國,維護民族獨立是畢生的使命。就這樣的英雄而言,在宋朝的官僚體制中也許注定了被殺的命運。“重文輕武,抑制武將專權”一直是宋朝政治管理的重點和核心。岳飛作為岳家軍的軍事領袖和朝廷的主戰派在經過幾次重大的軍事勝利之后,其軍事實力、民間威望、政治權力已經高速膨脹,且不說岳飛是否有專權之心,單單他的權力和威望已經嚴重威脅了趙構的皇權統治地位,功高震主顯然是趙構不能接受的,秦檜之言只是給了趙構借口而已,實則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消除威脅才是趙構的政治目的。至于神化的岳飛和西湖一跪八百年的秦檜銅像只是統治者打造民族理想,轉移矛盾的政治手段而已。
綜上所述;儒家的文化價值體系從根本上影響了歷史王朝的政治形態,決策者的政治意愿實現是借助了儒家的文化和思想而已,無論功過是非,或是史實評論在儒家這里儼然成為了美化外在,轉移目標的手段。兩千年的封建專制儒家思想從本質上決定了決策者的政治邏輯。就社會現實角度而言,社會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理念直接決定著決策者的政治邏輯,正如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所說明的那樣:“歷史的發展終究是偶然和必然的聯系,文化基因直接決定著統治階級的決策意志”。如果想避免重蹈歷史覆轍,必須在發展中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馬列思想為指導進行改革,始終維護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
參考文獻:
[1]略論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的歷史地理因素[J].邱江. 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10(02)
[2]近代以來“焚書坑儒”研究綜述[J].堵斌,高群. 烏魯木齊職業大學學報.2009(0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