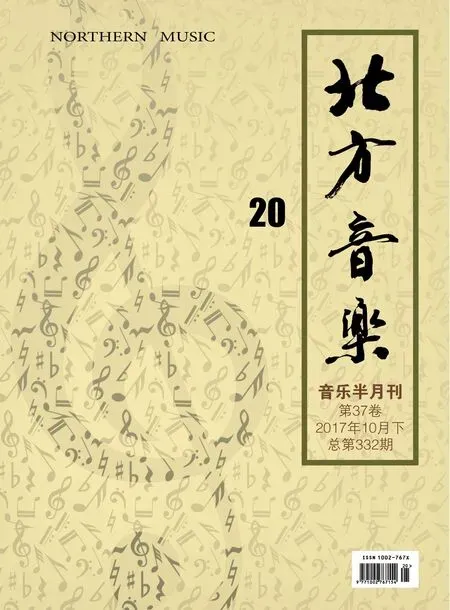埃德溫·戈登音樂聽想理論解析
王 藝
(西安音樂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1)
埃德溫·戈登音樂聽想理論解析
王 藝
(西安音樂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1)
對于大多數中國音樂教育工作者來說,埃德溫·戈登是一個很陌生的名字,但他卻是具有國際影響的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音樂教育家,也是西方音樂教育史上最早從事音樂教學理論研究的教育學者之一,他所創立的“音樂學習理論”在西方被視為與柯達伊、達爾克羅茲、奧爾夫和鈴木等齊名的音樂教學理論之一,本文主要通過文獻研究法對埃德溫·戈登音樂學習理論中的音樂聽想理論進行簡要的梳理和概況。
埃德溫·戈登;音樂聽想理論
埃德溫·戈登(Edwin E. Gordon, 1927-)是當代美國音樂界非常活躍的音樂教育家,是集樂手、心理學家、音樂教育學者和教師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人。先后在艾奧瓦大學、天普大學、南卡羅來納大學等多所高校任教,在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基于心理學及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結合大量的實證研究,在音樂性向、音樂聽想的階段和類型、音樂學習理論、音樂能力性向及測量等方面進行深入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包括著述44部、論文79篇、研究報告16篇、測試工具和手冊9套,對美國等西方國家音樂教育領域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一、音樂聽想的概念與來源
戈登曾在《嬰幼兒音樂學習原理》一書提到:“音樂聽想是為了已脫離音樂喃喃發聲期的兒童開始接受正式的音樂教學而發展的,而預備音樂聽想的對象年齡范圍向前推移,是對還沒有脫離音樂牙牙學語、喃喃發聲的萌芽初期。”這里面提到兩個詞語,一個是音樂聽想,一個是音樂預備聽想。音樂聽想與預備音樂聽想是戈登音樂學習理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字面上就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后者是為前者做準備之用,這兩者有相同也有不同之處,最明顯的區別就在于教學對象理想年齡的劃分差異。“音樂聽想”(Audiation)一詞是由戈登于1975年提出,戈登將其定義為,當音樂已經沒有或并沒有發出真正的聲音時,我們依舊能靜默地聽到并且能理解音樂,其主要的目標是通過理解去發展學生思考音樂的能力,學生們能夠通過聽想,從他們所聽到的、演奏的、即興表演的、創作的音樂中獲取更大的意義。
那么聽想這一概念是怎么來的呢。關于聽想研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羅馬時代,在歷史上,人們就曾經對通過大腦的活動去看的能力,或者說是利用“心眼”(mind’s eye)的能力冠以“心智表象”(mental imagery)的說法。到了后來,人們開始使用聽覺表象(auditory imagery)一詞來形容在實際的聲音不存在的情況下,大腦內部的聽覺能力。19世紀80年代之后,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研究開始了,對“心智表象”現象感興趣的高爾頓開始嘗試對“心智表象”進行數量化的測量和評價,而這種研究后來引起了西肖爾的注意,他的《音樂才能心理學》的第14章和《音樂心理學》的第11章,就均對音樂表象和音樂想象作了專門的論述。他認為聽覺表象是音樂才能的必要成分,對于測驗一個人的音樂才能如何至關重要,但遺憾的是,他本人并沒有找到對聽覺表象進行測驗的工具。與西肖爾相似,著名音樂教育家達爾克羅茲采用的是“內心聽覺”( inner hearing)來描述類似的現象,二者的表述雖然不同,但所蘊涵的意思是相似的。同樣,柯達伊的音樂教學理論所采用的“內在聽覺”的概念,與戈登的聽想也具有相似性。最初戈登也是借用前人的研究,采用“音調表象和“節奏表象”來表示類似的概念,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期,戈登對使用表象來概括音樂活動中的聽覺過程表示失望,對音樂表象和聽覺表象,以及他自己所采用的“音調表象”和“節奏表象”也感到不滿意。直到1975年,戈登的朋友、編輯克萊爾·艾夫斯(Claire Ives)向他推薦了“Audiation”這個詞。這個詞是“audition”和“ideate”兩個詞的組合,前者是名詞,表示聽覺的行為或機能;后者是動詞,表示形成觀念或進行思考。戈登認為這個新詞能夠確切地表達他的意思,于是便接受了,1999年,新版的英文字典里就已加入“聽想”一詞的解釋。
二、音樂聽想的類型和階段
1984年,戈登在《音樂學習的序列》一書中,提出音樂聽想可以分成七個類型和五個階段。在該書的1997年的修訂版中,他提出聽想的發展方式是多元且復雜的,原則上可細分成八種無一定次序性的類型和六個有次序的聽想階段。前后兩個版本的區別在于:第七種,即閱讀不熟悉的音樂是在1997年加入的,這種分類和分段后來一直沒有發生變化。

表1-1 音樂聽想的八種類型①
第一種,聆聽熟悉或不熟悉的音樂。這是最為常見的聽想類型,是在聆聽熟悉或不熟悉的音樂時產生的。我們對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音調型和節奏型進行聽想,然后按次序對它們加以聯系,給予音樂以句法的意義。可以將聆聽比喻做說話,先是注意各個詞匯,然后將它們組成句子和段落,再賦予句法和語法的意義。
第二種,閱讀熟悉或不熟悉的音樂。這也可看作是樂譜聽想,即對樂譜進行的聽想,它是在我們閱讀熟悉和不熟悉的音調型和節奏型的樂譜時發生的。我們可以靜默地閱讀,可以對所閱讀的樂譜通過演唱或演奏的方式表現,也可以在他人表現音樂時進行閱讀。
第三種,對熟悉或不熟悉的音樂記譜與聽寫,這也是樂譜聽想的形式。當對熟悉或不熟悉的音樂記譜與聽寫時,我們對聽覺感知了的東西進行聽想,然后用樂譜的符號對聽想了的東西加以表現,我們只是聽想音調型和節奏型中重要的音高和音長。此類聽想突出了這樣的一個事實,即當我們對所聽的音樂進行聽覺感知時,首先聽想的是基本音高和音長,也就是背景,然后補充非基本的音高和音長,來完成所聽的樂句或樂型。
第四種,從記憶中回想起熟悉的音樂。此種情況通常是不靠樂譜回想或演奏音樂,所以音樂的音調或節奏可能是熟悉或不熟悉的,以不出聲演唱或演奏等方式來呈現音樂聽想中所有熟悉的音樂。熟悉的音樂都被用來當指引,用回想來組織音樂中的其余形態,最后經由音樂聽想的回想過程持續到整首曲子結束。我們回憶熟悉的音樂片段不是記憶的結果,而是借助對音調和節奏語句進行組織。
第五種,從記憶中回想起熟悉的音樂,這也是一種讀譜聽想。我們在回想中所組織和聽想的熟悉音樂中的每個熟悉語句,幫助我們在對余下的熟悉音樂中的熟悉的語句進行組織和序列地回想,這個過程貫穿于熟悉音樂片段全部過程之中。如同在第四種類型中一樣,書寫的音樂不是作為記憶結果的回想,雖然我們只是對回想和作曲的音調型和節奏型的基本音高和音長進行聽想,但在回想和作曲時,我們下意識地將音調型和節奏型的中非基本的音高和音長置于完整的樂句之中。
第六種,創作或即興不熟悉的音樂。是在我們使用熟悉的或不熟悉的語句,靜默地在實際表現過程中,創作或即興不熟悉的音樂時產生的。我們在聽想中創作或即興的每個音樂語句幫助我們對后續的音樂語句進行序列地組織。
第七種,閱讀和創作或即興音樂。這種類型同樣也包含樂譜聽想。它是在人們閱讀熟悉和不熟悉的語句、同時在靜默狀態下或實際表現中創作或即興新的、不熟悉的音樂時發生的。雖然在沒有樂譜的情況下創作音樂或即興的心理過程是相同的,但這種類型的聽想涉及樂譜聽想。
第八種,當我們寫作熟悉或不熟悉的音樂,同時創作或即興不熟悉的音樂時,就出現了這種聽想,它也包含樂譜聽想。但是,假如我們在寫作之前對已經創作或即興的音樂進行一段時間的回想的話,這種類型的聽想就會變成第五種聽想。第七種聽想和第八種聽想的過程是相同的,區別在于前者的結果是讀,后者的結果是對我們已經創作或即興了的音樂進行寫作。
音樂聽想也可分為六個階段,由于類型不同,聽想的階段呈現出層級性、累積性和循環性的特點。前一階段的聽想是后續也就是更高階段音樂聽想的基礎和前提,當達到更高階段時,其他階段仍然重復地進行。實際上,我們可以將戈登的音樂聽想階段看作是一種音樂認知模式,即一種與概念形成有關的、對音樂進行信息加工和處理的模式。

表 1-2 音樂聽想的六個階段②
第一階段:瞬間的短暫記憶與保留。在對所聽的音樂中一系列音高和音長進行聽想之前,我們是無意識地對剛剛聽過的音樂中短的音高和音長系列進行聽想,因為是無意識參與,所以在聽音樂的那一刻并沒有進行聽想。我們是對聽覺感知到的音高和音長系列進行聽想,這是當即的印象,并沒有賦予音高和音長系列任何音樂上的意義。
第二階段:對調式語句和節奏語句進行模仿及聽想,并辨認出主音和主拍。當我們聽音樂并無意識地對一系列音高和音長進行聽想時,我們在有意識并靜默地模仿這系列中所有的音高和音長。然后我們通過聽想,有意識地把該音高和音長系列組成一個或數個基本音高的音調模式,以及一個或數個基本音長的節奏模式。根據有意識地確認或辨別出音樂中的音高點和主拍的位置,我們對基本音高和音長的音調及節奏模式加以組織。這是一個在有意識地確認或辨別出音樂中音高點和主拍的位置,以及對基本音高和音長的音調及節奏模式加以組織的互動過程。
第三階段:建立主觀或客觀的音樂調式與拍號。隨著對音高點和主拍位置的認識和確認,以及不斷地組織起音樂中的基本音高和音長的音調模式和節奏模式,我們就有意識地建立起了音樂的音調和拍號。
頭三個階段的聽想是同步進行的,此過程是基本音高和音長的音調和節奏模式的組織與音樂的音調和節拍的建立之間的持續互動,互動過程的結果是幫助我們對在聽想中已經組織了的和保持了的基本音高和音長的音調型和節奏型進行評價并可能進行重組。我們也可以對正在聽想的音調和節拍、將要組織的基本音高和音長的音調和節奏模式、以及音樂中已經出現或即將出現的音調和節拍變化,進行澄清和更好的判斷。
第四階段:在聽想中有意識的記憶已經組織了的調式語句和節奏語句。在此階段,我們能在聽想中有意識地保持己經在音樂中組織了的基本音高和音長的音調和節奏模式。四個階段的聽想是同步進行的,呈現循環的過程,因為各個階段是相互作用的。判斷。正是在此階段中,我們達到了對序列、重復、形式、風格、音色、動力,以及其他使得我們賦予音樂以音樂意義的相關因素的完全辯識和區分。
第五階段,對其他音樂片段中己經組織和聽想了的調式語句與節奏語句進行回想。在本階段我們有意識地對在其他音樂片段已經組織過和聽想過的基本音高和音長模式進行回想。我們可以發現,與當前所聽想音樂的相同點和不同點,我們所聽的音樂越多,所建立的代表各種音調和拍號的基本音高和音長模式詞匯數量越大,在此階段的表現就越好。如同語言,我們掌握的詞匯越多,我們交際的水平就越高。在音樂中,我們所掌握的基本音高和音長模式越豐富,我們的聽想能力就越高。
第六階段,預知并預測將會出現的調式語句與節奏語句。在經歷了前五個階段的聽想時,我們有意識地對將要聽想的音樂的基本音高和音長模式進行預測。戈登在描述本階段時用了兩個詞,一是預知(anticipation),包含兩層含義,一是預先知道在熟悉的音樂中將會聽到什么;二是預測(predication),指的是在不熟悉的音樂中可能聽到什么。后者是建立在對不熟悉的音樂的了解基礎之上的。除了第五階段的聽想外,在第六階段,所聽想的基本音高和音長模式比其他階段都多,對音樂的預知和預測越是準確,對所聆聽的音樂的理解就越深刻。
三、總結
如果沒有聽想,音樂理解就變得非常有限。戈登認為假如一個人能夠對音樂進行聽想,那么他就可以學會創作和即興演奏,并為自己和其他音樂家伴奏。戈登反復強調了聽想在音樂學習過程中的重要性,他認為聽想是一切學習音樂的前提要素,換而言之,想要學會演奏樂器之前就必須要學會聽想。在一個孩子真正理解基本的音高音型片段,以及節奏型片段之前,他也會很自然地處在初級階段的音樂思想過程之中,這己經是能夠讓他產生聽想過程的階段。然而聽想的能力并非能夠立刻或迅速學會的,學生們必須通過教師對其的音樂引導,經過每一個類型及階段的發展,對音樂產生內在理解進而感受和創作音樂。
注釋:
①Gordon,E. E.(2003).Learning Sequences in Music Chicago:GIA Publications,p.4.
②許冰.埃德溫·戈登音樂教學理論與實踐[M].人民音樂出版社,2014.
[1]許冰.埃德溫·戈登音樂教學理論與實踐[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4.
[2]埃德溫·戈登,余原.嬰幼兒音樂學習的秘密[M].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3.
[3]李爍.埃德溫·戈登的幼兒“音樂聽想”理論研究[J].北方音樂,2013.
[4]吳珍.埃德溫·戈登音樂學習理論研究[J].中國音樂,2009.
[5]Gordon,E. E.(2003).Learning Sequences in Music Chicago:GIA Publications.
J60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