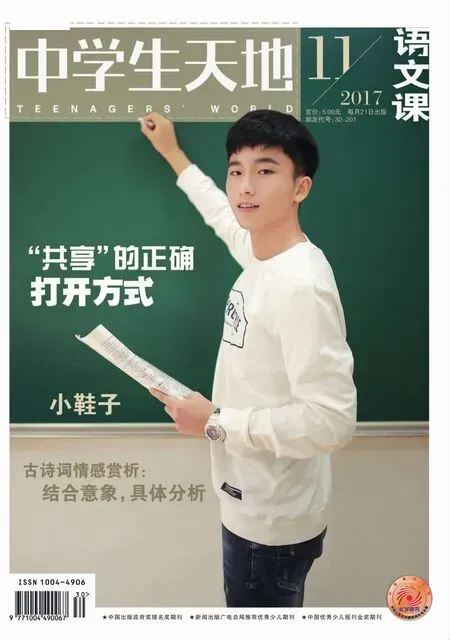《雨巷》:古典詩境現代詩
■瑞安中學 黃華偉 (特級教師)
《雨巷》:古典詩境現代詩
■瑞安中學 黃華偉 (特級教師)
《雨巷》的古典
談及白話詩,我們常常會提到它的“第一首”,即胡適先生的《兩只蝴蝶》:
兩只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么,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只,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相比胡詩,戴望舒的《雨巷》(蘇教版語文教材必修一)無疑要優美得多,原因很明顯:胡詩就是大白話,戴詩有“古典詩境”。
從意象看,“古典詩境”體現得最突出的,莫過于“丁香”這一古詩中較常見的意象。
李商隱《代贈》云:“樓上黃昏欲望休,玉梯橫絕月如鉤。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李璟《浣溪沙》有“青鳥不傳云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李清照《浣溪沙》有“梅蕊重重何俗甚,丁香千結苦粗生”;韋莊《悼亡姬》有“竹葉豈能消積恨,丁香空解結同心”……這些,不就是活脫脫的一個個“丁香一樣地結著愁怨的姑娘”嗎?
還有“江南雨”“雨巷”“籬墻”,還有“夢”,還有“油紙傘”。白居易《憶江南·江南憶九首之二》的意象、意境,簡直可視作《雨巷》的“前身”:
江南雨,古巷韻綢繆,油紙傘中凝怨黛,丁香花下濕清眸,幽夢一簾收。
在表達上,《雨巷》最大的特點是重章疊唱。
比如《雨巷》的第1節和第7節:
撐著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著 /一個丁香一樣地/結著愁怨的姑娘。
……
撐著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飄過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著愁怨的姑娘。
除了“逢著”和“飄過”不同,其余一模一樣。這種重章疊唱的方式,從《詩經》開始就是古典詩歌,尤其是樂府詩、民歌中的常用手法。
比如《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又比如南朝樂府詩:“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至于整首詩中“悠長、悠長”“丁香一樣的顏色,丁香一樣的芬芳,丁香一樣的憂愁”“像我一樣,像我一樣地……”“默默地走近 /走近……”“像夢一般地,像夢一般地凄婉迷茫”等反復之處,或者也可以理解成小規模的重章疊唱。
其他方面,“彷徨”“寂寥”“愁怨”“哀怨”“凄清”“惆悵”“太息”“凄婉迷茫”,對古典詩詞稍有涉獵者,就會覺得這樣的情感耳熟、眼熟、心熟得很了。
最后從整體看,《雨巷》也逃不離古代文人常有的那種纖弱柔美氣質、唯美朦朧風格,于是也就有了《兩只蝴蝶》所沒有的美感。
《雨巷》的現代
在白話詩還沒有真正擁有屬于它們的審美對象時,它們暫時借助傳統的古典的內容,也是可以理解的。這也是我們認為胡適《兩只蝴蝶》嘗試的重要意義。而《雨巷》的成就正在于這個“新瓶裝舊酒”——用白話詩表達古典詩境。
也就是說,胡適雖用白話,卻仍還有明顯的古詩形式的束縛,比如全詩八句、每句五字,還沒有很好地發揮白話詩的語言優勢。戴望舒在這方面就大大地前進了一步,最明顯的貢獻,我認為在于“又”“的”“了”的頻繁使用。

“又”使語意更顯悠長,表達更為盡興。
“又”在古詩中并非沒有,如“道阻且長”,就是“道路險阻又漫長”。但《雨巷》是這么寫的:“悠長、悠長/又寂寥的雨巷”“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冷漠,凄清,又惆悵”“走近 /走近,又投出”。
在古詩中,我們很少能看見三個并列的詞出現,這是受古詩的句式特點、語句容量所限。白話詩則不同,它可以有不止三個并列詞,甚至可以有不限量的“后補”詞并列呈現,只要詩人覺得不夠“盡意”。所以,“又”使白話詩具有了“賦”一般鋪陳排比的功能,使語意更顯悠長,表達也更為盡興。
“的”緩解詞語間連接的局促、生硬。
“的”是白話文區別于文言文的重要語言標志,它很大程度地緩解了詞語間連接的局促、生硬,表達功能甚至比楚辭中的“兮”更為強大。
比如《雨巷》的第 2、6節,詩人集中使用“的”:“……的顏色”“……的芬芳”“……的憂愁”“雨的哀曲”“她的顏色”“她的芬芳”“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悵”。我們現在看來平常得很,但如果沒有了“的”,就難能呈現白話詩特有的舒緩柔軟的節奏。
來看后起詩人艾青的詩,更能體察“的”的重要意義,有人甚至開玩笑地說:“艾青的詩句就是一個定語再加一個定語。”比如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的幾句:“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莊的名字”“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長大了的 /大堰河的兒子”“你的被雪壓著的草蓋的墳墓 /你的關閉了的故居檐頭的枯死的瓦菲/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園地 /你的門前的長了青苔的石椅”。你試著去掉“的”讀一讀,什么感覺?

“了”有音節上的延長感、時間上的延續感。
“了”也是很了不起的白話虛詞,它既有音節上的延長感,往往也有時間上的延續感。
比如《雨巷》的第 5、6節都連用三個“了”:“她靜默地遠了,遠了,/到了頹圮的籬墻”“消了她的顏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沒有“了”固然不成話,而有了“了”就更有惆悵的韻味、凄婉的美感。
對比《兩只蝴蝶》,沒有“的”“了”“又”等有重要表現意義的白話虛詞,在表達上就顯得寒磣、拘謹得多了。
此外,還有詩歌的大容量,全詩共7節,用我們現在已經非常熟悉的散文似的筆法,盡情盡意卻又能較有節制地敘述、描寫這種想象之景、理想之境。
另外,就是句式長短不拘,既能展現詩歌和諧的節奏,又能充分體現出其靈活多變的一面。這是古典詩,即使是古風的歌行體也難能做到的,也是胡適《兩只蝴蝶》沒有做到的。
總之,《雨巷》既有古典詩歌的優美內涵,又有白話詩歌的自由形式,可謂“兼美”矣,這使它在白話詩發展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圖:馬 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