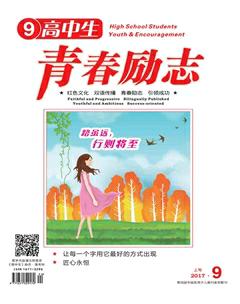缺少交通工具的古人如何出遠門
王月
如今,因為有各種交通工具,想要出個門是再方便不過了。但是,出門這件事,放在以前可不容易,像徐霞客走完大半個中國,就用了30多年。當然,古人也是有交通工具的,只不過從現在看起來很奇葩。
馬車、牛車各有故事
今天可能很難想象,很長時間以來,牛車是古代中國的主流交通工具。在歷史中,馬車和牛車差不多是同時期的產物,起源于商代。相比牛車,馬車的地位顯然要更高,畢竟跑得快,打仗用得上。但是,馬匹的消耗就很大了。仗打到了西漢初年,馬匹奇缺,連皇帝出行都難找到幾匹毛色相同的馬拉車,一些官員就只能乘牛車出行了。
牛車相比馬車來說走得慢,另外,牛還要耕田,不體面,所以經濟一好轉,大家還是換上了馬車。東漢時,一個叫謝夷吾的太守,因為坐牛車出巡,丟了朝廷的體面,被刺史劾奏,直接貶為縣令。
但是,到了魏晉時期,牛車又成了好東西。這是因為那時的名士崇尚清談,享用著佳肴美酒,每日也不趕時間,牛車速度慢的缺陷在這時也就無所謂了。更何況,當時道路條件差,速度慢的牛車坐起來也比較舒適。因為速度慢,所以不用學習專門的駕駛技術。“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就經常一個人駕牛車出行,走到沒有路了,就放聲慟哭。
木牛流馬能運糧
看過《三國演義》的人,恐怕對諸葛亮發明的“木牛流馬”很好奇。在小說中,這是運糧利器,能順利穿越險峻的蜀道,把軍糧運到前方。
在現實中,木牛流馬究竟是什么,雖然有些爭議,但是推測它是獨輪車,應該是不錯的。獨輪車俗稱“雞公車”,漢代就有了,當時叫“轆車”。漢代井上汲水多用轆轤,是一種輪軸類的引重傳動器,而這種手推車就是由一個向前滾動的獨輪帶動前行,輪子形似“轆轤”,所以稱其為“轆車”。
諸葛亮的木牛流馬,應該就是從轆車改制而成的。“木牛”說的是這車像一頭不吃草的牛,“流馬”說的是獨輪轉動靈便,運行輕快,如同能流轉疾奔的馬。
在道路不發達的古代,獨輪車是南方丘陵地區理想的交通工具,它比肩挑手提省力多了,哪怕走山路也平穩、輕巧。車夫還會把一根布條系在兩個車把上。推車的時候就把布條掛在肩上,這樣能保持平衡,也能利用肩膀來分擔一些重量,省些力氣。
備轎有規矩
宋代之后,轎子開始流行。當然,如果是武職官員,他們要帶兵打仗,坐轎子就說不過去了。在轎子極盛的明清,都有明文規定,武職官員不準坐轎,哪怕是王爺。順治年間,有官員就平西王吳三桂等各路王爵乘轎一事請示。朝廷上諭回復:各王在鎮守的地方可以乘轎,到京師則須騎馬。乾隆年間,甚至還有滿洲籍文職大臣禁止坐轎的規矩,只有年事已高、身體確實不好者才能例外。
但是,大將軍福康安就例外得有點過分了。他不僅平時坐轎,連打仗也是坐轎子。他手下常備有36名轎夫。這么多人,并非都是一起來抬轎子,而是輪流抬,所以福康安的轎子速度快,跟騎馬也差不了多少。那些替補的轎夫呢,每人也要備幾匹好馬,騎著馬跟著轎子行進。
但是,史上最夸張的轎子,還是張居正的32人大轎。那時的張居正是內閣首輔,他奉旨回湖北江陵老家,為父親辦喪事。那時皇帝年幼,張居正權傾朝野,所以他的轎子“超標”得厲害:32個轎夫一起抬,內分臥室和客室,還有兩名小童在內伺候。算重量,這個轎子超過一噸,算體積,驛道都可能不夠寬。所以,張居正這一路,途經的州縣都是大興土木,修橋鋪路。
羊皮筏子也叫船么
關于羊皮筏子,有個很有趣的舊聞:幾年前,甘肅羊皮筏子開始按船舶來管理。此前,羊皮筏子屬于“浮動設施”,不算是船。羊皮筏子看起來也不像船,但在古代,像羊皮筏子這樣的“革船”,還真的就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革船,也就是皮革做的船。史載匈奴以馬革制船,此外還有牛皮船、羊皮船、魚皮船。早期的革船,就是用皮料裹住草或者動物的毛發,縫起來當漂浮物。宋代以后有了“渾脫”———將山羊皮浸水、曝曬、去皮、扎口,灌入食鹽和油,就是一個不漏氣的氣囊。為了安全和增大載重量,若干個“渾脫”相拼,就有了羊皮筏子。
制作羊皮筏子需要人用嘴吹氣,使其脹滿,所以蘭州人見到有人夸海口,說大話,往往以“請你到黃河邊上去”來嘲諷,意思是讓其去吹羊皮囊或牛皮囊。據說,“吹牛皮”的說法就來源于此。
但是,羊皮筏子再神奇,也不如木船靠譜。在中國古代,無論載人載貨,木船才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明清兩代的京杭運河之所以成為國家的經濟命脈,是因為運河上的漕船運送著幾百萬石的糧食,附帶大量白銀和各種商品,還有往來的官吏、客商。北京的官去四川上任,看直線距離肯定是走陜西最近。但是,走京杭運河,到揚州換江船,沿長江逆流而上,才是最佳選擇,又快又舒服。
在水網密布的江南,除了在城里或山上用轎子以外,普通代步是用烏篷船,再走遠一點就用白篷的夜航船,夕發朝至。睡一覺就到了,想來就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