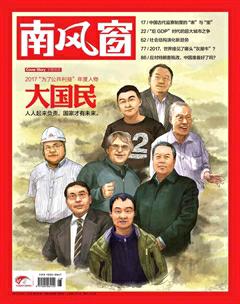社會結構演化新趨勢
石勇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庫利曾將人類生命的歷史比喻成一條河流。它其實也可以用來比喻2017年中國的社會結構。
2017年,中國社會這條河非常平穩,緩緩而行,沒有泛起太多的波瀾。盡管有霧氣籠罩,且從上游所挾帶的泥沙、廢棄物也讓河流顯得有些渾濁,其間還醞釀著一些變化,但我們大致還是知道它的情況,它的走向。

有哲學家說,過去是用來懷念的,不是用來回去的。說得很對。事實上,在這一年里,我發現很多人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心理模式:不要說“過去”,即使是“現在”,發生了之后在心理上就變成了“過去”,只想快速遺忘。我們已經培養了一種把“現在”看成短暫易逝或易碎,并望著“前方”或“未來”的能力,只是,這樣做時,在期待中又疑慮重重。
但從來就沒有一個預先形成,在那兒等待我們的“前方”或“未來”。它們是現在的人,利用現有的資源和機會創造出來的。關鍵只在于,誰有這樣的資源和機會。
本文想梳理一下2017年中國社會結構的演化,并展望或說預測2018年的大致面貌。我注意到了一些過去沒有出現的東西。
從土地到房子
按照社會學家米爾斯的理論,我們要了解社會,需要一點“社會學的想象力”。但這一年來其實并沒有提供足夠的想象空間。或者說,很多東西很直觀,不需要想象。
社會結構的演化,大致可以在人口、階層、社會心理、社會結構與政治、經濟結構的關系等維度上去考察。
據國家統計局2017年2月28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6年年末全國大陸總人口138271萬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79298萬人,農村戶籍人口58973萬人。這是中國城市化的一個新階段。
盡管一年來,我們還沒有獲得關于城鎮和農村人口的最新統計,但根據中國城市化率的逐年上升完全可以判斷,城市人口肯定是在大大增加,農村人口肯定在大量減少。2016年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增加了2182萬人,鄉村常住人口則減少了1373萬人,城市化率為57.35%。我們據此判斷, 2017年,中國新增的城鎮人口和減少的鄉村人口離這兩個數字也不會太遠。
而新增的人口,呈現出一種向大城市及周圍城市集中的明顯趨勢。一線城市及周邊、省會城市對經濟、人口的吸附能力非常明顯。
于是我們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從2016年上半年開始的那一波房價的暴漲,先是從一線城市發端,繼而,蔓延到二線城市。在一、二線城市通過限購、限售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冰封”了樓市后,資本、恐慌外溢到三、四線城市這些所謂的“價值洼地”,推動其房價暴漲,實現了“漲價去庫存”的不可思議的奇跡。站在2017年的終點,我回頭看了一下,在一些一、二、三線城市,這一兩年來,房價已經翻倍了。
我發現了這樣的一個規律:一線城市上漲到一定幅度,限購、限售,冰封→資金往二線城市、不限購的城市→二線城市、不限購的城市房價上漲→上漲到一定幅度,限購、限售,冰封→資金往三線城市、不限購城市……最終的到達地,似乎是“價值最洼地”六線縣城。
這是填平房價不平衡的客觀后果。不過它當然也有影響人口分布和用房子來劃分階層的意思。我注意到,在這種現象中,人們的心理已經發生變化,從對高房價的怨氣變成對買不起房上不起車的恐慌,以及在無能為力中,通過想象房價會暴跌,對于現狀的壓抑性接受。但最直接的一點就是房子在一定程度上識別出了一個人的階層地位。
于是在這些背景下,困惑中國幾千年的一個問題,即土地問題,已經具有了新的涵義,變成了土地之上的房子問題,或者說,是房子所對應的福利、資源、財富、機會等問題。這個轉變不是突然之間形成,但它的影響是極為重大的。
那么在現有的高房價下,在它本身就是一個風險而又不能捅破泡沫的情況下,如何應對這個“挑戰”?
辦法是有的。我們看到了租售同權的出現,看到了2017年租房市場的一些打造。這些都能把房價問題轉換成“租房”這個完全是次一級的問題。雖然,房租或許會在2018年以后成為一個新問題。
這是2017年社會結構變化中,一個最值得關注的點—它一定是2018年及以后一些社會現象的出發點。
新的變化
前面說過,2017年中國社會結構并沒有什么波瀾。我指的當然是浮出社會表層的重要事件,不是指社會結構內部所發生的一些變化。
社會演化有自身的規律,也受到政治結構、經濟結構的影響。從社會結構的變化上看,其原子化程度在加深,而且,每個社會原子之間的心理距離在2017年加大了—甚至出現一些過度的心理防御,以及暴力鏈條的傳遞。這意味著道德底線的下降和突破。
我們從這一年所發生的一些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這一點。比如像災難事件在社會交媒體上并沒有成為一個關注的話題;比如“教科書式老賴”和其女兒的表現;比如幼兒園虐童事件。社會結構的腐蝕是在繼續的。
還可以看到,這一腐蝕已經蔓延到中產階層這個結構層面。它導致了精致的利己主義實際上已經變得粗鄙;歲月靜好的生活也建筑在一種自我想象之中。中產的分化在加劇,群體內部的心理競爭也越激烈。中產的中下層群體已經能夠體驗到足夠的社會痛點。
就是說,在“農民工”之類詞匯所代表的階層群體在社交媒體上越來越沒有議題設置能力后,中產社會圈層已然成為社會結構各種問題的承受地。這是風險的標志,但其實也是“社會承受能力”因為抬高了階層,在各種矛盾沖擊中并沒有降低的標志。
中產階層更多地關注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在心理上和利益上都沒有辦法和這兩個場域隔離。所以,我們發現,2017年,社會結構受政治結構的影響越來越大。
我們知道中國社會的風險模式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政治結構。這一模式至今未變。可以看到,風險其實來自于經濟結構而不是社會結構,只是,它若出現很大的問題,會對社會結構有沖擊,從而帶來雙重的破壞力而已。
那么,從影響社會結構演變的因素上來說,思路并不復雜。
從政治結構上說,它可以在強化權威,自我把控和整合社會結構后,對經濟結構進行影響和控制。這是消除風險和實現偉大目標的路徑。這是從過去幾年一直到現在發生的事情,只是在2017年非常明顯。經濟結構是必須具有可控制性的。這是一個一直發生的現實。所謂的讓市場自我調控,從來只是一個理論上的神話。
而這也意味著,資本要服務于整個社會和經濟目標的需要。這一點,是一些一直成為大眾熱點話題的民營企業家某些行為選擇和語言表達的背景。過去一直講的“國進民退”、“國退民進”話題,在今天已經有了一個新版本。我們能夠看到國家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發揮更強影響力和話語權這樣的趨勢。這一趨勢目前實際上已經顯示出來了,在2018年,我們將看得更清楚。
社會心理
我注意到,在2016年大行其道的直播,已經沒有那么引人矚目,各路網紅也因為“時尚之后就是low”這個規律而開始減弱自帶的250瓦光環。我曾經說過它是沉悶社會背景下人們心理上的出口,現在,這個出口已經不是人山人海,意味著社會心理背景已經有了新的指向。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變化。我想說,沉悶的社會背景中,已經開始顯出一些煩悶心理的跡象了。
一個社會要開始產生煩悶心理,要滿足以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人口多數已經解決溫飽,但尚達不到“有房有車”的水準。換句話說,大致介于貧窮的農業社會和高度工業化的富裕社會之間。
為一日三餐發愁的人是沒有多少心理能量用在別的事情上的,只要生存的根基還可以維持,他們在心理上就會死死地抓住現實。對于現狀,他們已經成功地采取了“認命”的心理策略。而已經成為“人生贏家”的人,也不可能產生煩悶。他們可能有不安全感,但內心有秩序感,似乎能控制現實。他們的自我,在對比中好像是成功的。
產生煩悶的,是那些已經解決溫飽,但在追求更好生活中受挫,沒有一個價值感的出口的心靈。
第二個條件是社會高度原子化,人們孤獨,而又感受到彼此的心理競爭。
第三個條件就是在現實中感受到自我的受挫,而且,娛樂、裝X都仍然掩飾不了這樣的體驗,現有的一切仍不足以成為心理的出口。
這個條件目前只是初步出現模糊的輪廓。我們存在足夠的消除煩悶心理的制度和價值觀的資源。
第四個條件就是社會經濟變化使人們想快速遺忘現實。在沉悶中找娛樂等出口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想遺忘現實,在心理上往并沒有明確預期的未來上趕過去,正是有一點煩悶的折射。
無論是沉悶還是煩悶,社會結構本身并沒有方向感,其心理能量消耗在個人的情緒和一堆社會原子的互動中,跟存在憧憬,甚至焦急的社會心理背景的社會結構都有所不同。它的方向感需要政治結構的賦予和強化。所以,宏偉目標的提出,以及把心理能量引導到實現社會整體福利的制度設計與政策導向,尤為重要。
我們可以預期,2018年,各種社會心理會繼續存在,期待,憧憬,激動,焦慮,沉悶,煩悶,將復雜地共存,但有些心理會強化其比例,在社會表層中表現出來,而有些則會減弱成為不起眼的背景。但無論怎樣,它都是社會結構演化到了哪一種狀態的重要特征,我們對一個社會的結構和其狀態的判斷正是從中可以看出一二。
中國社會結構具有一種良性的演化機制,即秩序強有力的存在,以及價值觀對它的粘合。而各種問題,則會影響到它的表現。但很多時候,社會是在解決問題中進步的。讓我們對2018年抱持更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