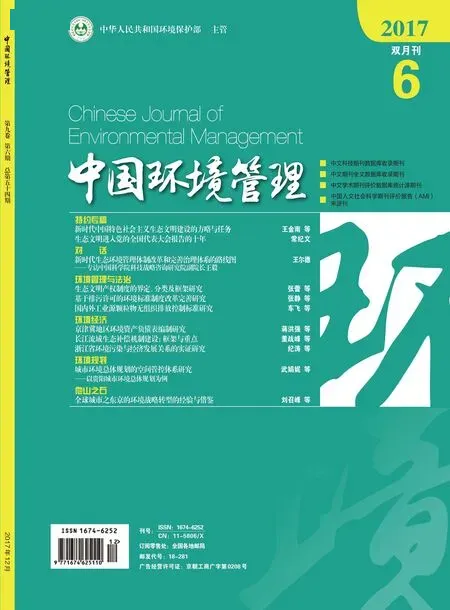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的空間管控體系研究
——以貴陽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為例
武娟妮*,孫寧,姚夢茵,盧靜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北京 100012)
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的空間管控體系研究
——以貴陽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為例
武娟妮*,孫寧,姚夢茵,盧靜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北京 100012)
環境空間管控和環境空間規劃是我國城市空間規劃體系中的短板,我國亟需建立起一套城市環境空間管控體系,來參與城市空間規劃體系的建立,進而徹底扭轉城市環境污染被動治理的尷尬局面。構建覆蓋城市各領域的環境空間管控體系是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的主要任務。本文梳理了我國環境空間管控發展現狀和問題,從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的角度,在城市層面構建了由環境功能區劃、以生態保護紅線為核心的嚴格管控區以及環境承載調控等手段組成的環境空間管控體系,并以貴陽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為案例,進行了環境空間管控體系的構建。最后提出了實施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空間管控的政策建議,保障空間管控體系能夠落地和發揮作用。
環境總體規劃;環境空間管控;環境功能區劃;生態保護紅線;資源環境承載;貴陽
引言
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越來越多的資源和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的規模不斷擴大。人口和經濟要素的空間分布決定了污染物的空間分布,也決定了城市環境問題突出的空間特征,主要表現為城鎮連片開發蠶食生態空間、部分區域污染物排放超出環境承載力等區域性、格局性環境問題。然而長久以來,我國環境規劃滯后于城市化發展,缺乏對城市空間的管控手段,環境保護規劃與措施在空間上不落地,環境對城市發展的約束和引導不足[1]。自十八大提出生態文明建設以來,國家對環境空間管控,尤其是生態空間管控的重視程度逐漸提高,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建立空間規劃體系,劃定生產、生活、生態空間開發管制界限,落實用途管制”,并提出了劃定生態保護紅線。2015年印發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提出“構建以空間規劃為基礎、以用途管制為主要手段的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著力解決因無序開發、過度開發、分散開發導致的優質耕地和生態空間占用過多、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等問題”以及“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其后印發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要》《全國生態保護“十三五”規劃綱要》等均進一步強調了空間規劃體系、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空間治理體系和生態保護紅線。環境空間管控和環境空間規劃仍然是城市空間規劃體系中的短板,我國亟需建立起一套城市環境空間管控體系,來參與城市空間規劃體系的建立,進而徹底扭轉城市環境污染被動治理的尷尬局面。
1 我國環境空間管控發展現狀
1.1 現行空間規劃中的環境空間管控
我國現行的空間規劃體系以主體功能區劃、城鄉總體規劃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為主。主體功能區劃目前主要在全國和省級層面開展,根據不同區域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劃定“四區”(優化開發區域、重點開發區域、限制開發區域和禁止開發區),確定不同區域的主體功能,從宏觀上引導分區的開發方向和強度,完善開發政策,形成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相協調的國土空間開發格局,自然保護區、世界文化自然遺產、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地質公園等重點生態功能區劃入禁止開發區。城市總體規劃從城市建設的角度出發,規劃范圍主要為中心城區,通過劃定“四區七線”(“禁止建設區、限制建設區、適宜建設區、已經建設區”和紅、綠、藍、紫、黑、橙、黃7種控制線),明確中心城區禁止、限制和適宜建設的地域范圍,具有重要生態和環境價值的空間劃入禁止建設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從節約和合理利用國土資源的角度出發,規劃范圍為整個市域,劃定“三界四區”(城鄉建設用地規模邊界、城鄉建設用地擴展邊界、禁止建設用地邊界和允許建設區、限制建設區、管制建設區、禁止建設區),同樣把具有重要生態和環境價值的空間劃入禁止建設區。以上規劃的出發點主要為區域開發建設和土地利用,非生態環境保護的視角,雖然對環境保護也有所考慮,但是份量較輕,保護的范圍不全面。此外,由于事權限制和規劃調整對象的局限,城市總體規劃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對非建設用地的空間管制作用非常有限,相關管控政策缺乏操作性[2]。主體功能區劃主要起引導作用,管控力度不強,列入禁止建設區的生態功能區類型較少。此外,大部分城市尚未開展主體功能區劃,省級甚至國家級的主體功能區劃在城市層面的作用有限。
1.2 環境空間管控的發展現狀
目前專門的環境空間管控仍以單要素專項環境功能區劃為主,如水環境功能區劃、大氣環境功能區劃、生態功能區劃等,僅在該要素的范圍內進行分區管控,對環境保護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對生態環境、社會經濟和人類健康等因素的綜合考慮,環境保護的統籌指導作用有限[3]。在這種背景下,開始了綜合性環境功能區劃的工作,基于區域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分區制定生態環境保護目標和污染物總量控制、工業布局與產業結構調整等環境管理要求。國家層面首先編制了《全國環境功能區劃綱要》,將全國分為自然生態保留區、生態功能保育區、食物環境安全保障區、聚居環境維護區和資源開發環境引導區五大類,明確了分區環境功能目標和分區生態保護、環境準入、污染控制、環境監管等環境管控要求[3]。環保部在2012年和2013年共選擇了13個省(區)①省級環境功能區劃試點:2012年為吉林、浙江和新疆;2013年為河北、黑龍江、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四川、青海、寧夏、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開展省級層面的環境功能區劃試點工作,積累提煉出了大量基礎性做法和實踐經驗[4]。在城市層面,貴陽、福州、廣州等城市通過城市環境總體規劃試點②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的通知》(國發〔2011〕42號)提出探索編制城市環境總體規劃。2012年環保部開展城市環境總體規劃試點,第一批試點城市為大連、鞍山、伊春、南京、泰州、嘉興、福州、宜昌、廣州、北海、成都、烏魯木齊;第二批試點城市為長治、本溪、鐵嶺、銅陵、煙臺、威海、海口、三沙、貴陽、石河子、沈陽經濟技術開發區、平潭綜合試驗區;第三批試點城市為青島、賀州、貴安新區和廈門。工作開展環境功能分區研究,新余、鄂州、梁子湖等城市通過編制生態文明建設規劃來開展,包頭、鄭州等城市開展了專門的城市綜合環境功能區劃研究[3]。環境功能區劃是對主體功能區劃的深化,對提升環境管理水平、實施精細化管理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另一項大力推動的環境空間管控手段是生態保護紅線,其最早在2005年廣東省頒布的《珠江三角洲環境保護規劃綱要(2004—2020年)》中被提出并得到應用[5],2011年,《國務院關于加強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的意見》中首次正式提出“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并實行永久保護”[6]。2012年,環保部通過城市環境總體規劃試點工作推動生態保護紅線的研究和劃定,使生態保護紅線技術和管理體系逐漸成形[7]。同時,江蘇、天津等省市也先后完成了生態保護紅線劃定[8]。生態保護紅線已成為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的一項戰略性制度安排[9],《全國生態保護“十三五”規劃綱要》已明確要求各省份完成生態保護紅線劃定,并勘界定標。
總體來說,目前主要的環境空間管控手段較為分散,且仍在試點或總結當中,各地結合地方實際開展了環境空間管理策略的探討研究,并取得一定的實踐經驗,但目前構建環境空間管控體系方面尚未形成統一的理論體系和操作模式[2]。其次,對城市而言,目前環境空間管控更注重城市生態環境底線資源的保護,如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和落地,對其他手段重視度不夠。生態保護紅線為城市范圍內劃定的一部分嚴格保護的區域[10],是城市范圍內的一小部分,最嚴格的管控結果也僅為不開發不建設的“無人區”,而對該區域以外的區域的生態環境保護不能產生作用。即只能守住城市生態安全的底線,不能從源頭形成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的態勢,所以應多種管控手段并重,綜合利用和優勢互補。
2 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的空間管控體系構建
城市環境總體規劃是城市人民政府以當地自然環境、資源條件為基礎,以保障行政區域環境安全、維護生態系統健康為根本,通過統籌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合理開發利用土地資源,優化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空間布局,確保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所做出的戰略部署[7]。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的最大特征是空間規劃和統領性的總體規劃,構建覆蓋城市各領域的環境空間管控體系是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的主要任務。總體思路上,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的空間管控體系應覆蓋生態、水、大氣、土壤等環境要素,宏觀上起到對經濟社會的引導作用,微觀上具備管控的有力抓手,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綜合目前環境空間管控的進展,城市環境空間管控體系應由三種手段組成:城市環境功能區劃、嚴格管控區和環境承載動態調控,對城市空間進行全方位的定位、約束和引導,如圖1所示。

圖1 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的空間管控體系
一是頂層的城市環境功能區劃,管控范圍為整個市域。城市的面積較廣,不同區域的生態環境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差異性,生態環境問題的空間異質性決定了要構建差異化的環境管理機制,所以應首先在大尺度上,依據不同地區在環境結構、環境狀態和環境服務功能的分異規律,劃分自然生態保留區、生態功能調節區、食品安全保障區、聚集發展維護區、資源開發引導區等類型區,分析確定不同區域的主體環境功能,并據此確定差異化的保護和修復的主導方向,執行相應的環境管理要求,從戰略層面指導城市分區發展。
二是嚴格管控區,管控范圍不僅包括生態保護紅線,還應覆蓋水、大氣和土壤等環境要素。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和水、大氣和土壤等環境質量紅線區,將城市生態、水、大氣和土壤中的極重要區、極敏感區和極脆弱區進行嚴格保護。需勘界定標,出臺明確的管控措施。該區域的約束力最強,是環境空間管控最有力的抓手。此外,考慮到這種底線控制法將環境問題壓于一線,一旦突破底線將難以恢復和補救,應有一定的過渡地帶[11],所以應在紅線區外劃定一定的黃線區,并制定相應的管控措施。
三是環境承載動態調控,管控范圍為超出環境容量承載能力的城市水體流域和大氣環境區域。該手段實現的基礎是對各環境單元的環境容量的識別,由于環境容量隨著自然條件的改變而改變,環境承載還隨著污染物排放量的增減而變化,所以該管控手段是動態的。根據水和大氣環境容量和承載狀態,實施動態調節性措施,嚴格限制環境容量超載區增加污染排放,引導工業企業向環境容量較大的區域轉移。該區域的約束力要弱于嚴格管控區,但是管控范圍可以涉及非嚴格管控區內的區域,手段更靈活,是城市環境空間管控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3 貴陽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的空間管控體系
3.1 貴陽市環境空間管控現狀
在第二批城市環境總體規劃試點城市中,貴陽市是西部生態脆弱城市的典型代表,喀斯特地貌極度發育,生態環境極其脆弱敏感。近年來貴陽市城市化進程較快,城市迅速擴展蠶食生態空間的現象突出,造成部分地區生態系統功能退化明顯。污染物排放的空間不均衡性突出,部分水體的水環境容量和部分區域的大氣環境容量超載嚴重。在編制環境總體規劃之前,貴陽市僅開展了生態環境功能區劃、水環境功能區劃和大氣環境功能區劃等專項環境功能區劃,覆蓋范圍不全面,且管控措施約束力較弱,對資源環境的空間布局缺乏有效綜合協調。隨著貴陽市開發的提速,對完善和系統化的城市環境空間管控的需求越來越迫切。下面以貴陽市為案例,結合貴陽城市環境總體規劃,分別從城市環境空間管控體系的三個方面進行構建。
3.2 貴陽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的空間管控體系的構建
3.2.1 環境功能區劃
貴陽市的環境功能區劃以自然生態環境、產業結構和布局為基礎,銜接了城鄉總體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主體功能區規劃等相關規劃,以行政單元,劃分生態保育區、環境風險防范區和環境質量維護區。北部的開陽縣和息烽縣為生態屏障保育與環境風險防范區,環境功能為保障區域生態安全、維護水源涵養、調節區域氣候、維持生物多樣性等,盡量減少社會經濟發展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大規模擾動和破壞,盡量維護和提升生態功能價值。該區域的環境管理政策為生態保護優先,強化生態紅線管控和生態修復,保障長江支流烏江的流域生態安全,重點開展增強生態涵養和生態保護功能的建設項目。西部的清鎮市和修文縣為環境安全保障區,環境功能為維護區域水源涵養、水土保持、防風固沙、生物多樣性保護等,防治沙漠化、土壤侵蝕、石漠化、土壤鹽漬化等生態風險,平衡經濟建設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該區域的環境管理政策為保護與發展并重,強化生態修復和水體保護,引導農業、工業和旅游業合理布局和生態化、綠色化發展。南部的六區為城市環境維護區,環境功能是為社會發展、經濟建設、科研教育、旅游度假和文化精神生活等提供承載、容納、欣賞、休閑的環境空間,提供水源供給和廢棄物處理,調節局部氣候,維持生物多樣性。該區域的環境管理政策為優化發展,強化資源節約和環境質量改善,控制人口總量,嚴格管控工業污染和機動車污染,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各區域分別制定了與政策相適應的環境目標和指標。
3.2.2 生態保護紅線和環境質量紅線區
貴陽市生態保護紅線劃定以《生態保護紅線劃定技術指南》為依據,包括貴陽市法定生態環境保護區(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飲用水水源一、二級保護區,濕地保護區,林業生態紅線等),生態評價得出的生態環境極重要區、極敏感區和極脆弱區等區域。在生態保護紅線內,根據紅線類型實施分類管控措施,嚴禁實施對主導功能產生破壞和重要影響的建設行為,嚴格控制對次要生態功能產生影響和破壞的建設行為。貴陽城市環境總體規劃中劃定了生態保護黃線,作為生態保護紅線的緩沖,同時提出了相應的管控措施。
貴陽市的環境質量紅線區主要為水環境質量紅線區和大氣環境質量紅線區。水環境質量紅線區根據管控的嚴格程度不同分為兩級:一級紅線區主要包括飲用水源一級保護區和源頭水水體及上游最小水文控制區,二級紅線區包括飲用水源二級保護區、環境功能類別為Ⅱ類的水體和濕地保護區。水環境質量紅線內實施分級管控措施,一級紅線區內嚴禁開展與供水設施和保護水源無關的建設活動,二級紅線區內可以存在一定程度的開發建設活動,但嚴禁向水體排放污染物。大氣環境質量紅線區的出發點是保障公眾健康,基于貴陽市的人口分布以及氣象流場特征,納入城市人口聚集區和環境空氣質量一類功能區、城市主導上風向地區和大氣環流通道以及大氣污染物自凈擴散能力差的地區。大氣環境質量紅線區嚴禁使用高污染燃料,嚴禁新(改、擴)建高污染項目,并加強對現有污染源的總量管控和達標排放監管。水和大氣環境質量管控區也都劃定了黃線區作為緩沖。
3.2.3 環境承載動態調控
大氣污染物承載方面,通過對10區(市)縣的污染物(SO2、NOx、PM10)承載率進行評估,發現部分區域尤其是主城區已嚴重超載。對此,貴陽城市環境總體規劃提出了控制新建廢氣排放項目、對現有大氣排放項目應實行更加嚴格的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加大污染防治水平低下企業的清理整頓和關停淘汰力度等措施,引導大氣污染項目退出大氣環境容量超載區,向富余區轉移。在水污染物承載方面,通過對貴陽市29個水環境控制單元的污染物(COD和NH3-N)承載率進行評估,發現部分控制單元容量嚴重超載,部分為一般超載。貴陽城市環境總體規劃對嚴重超載區提出了調整產業結構和布局,關停規模小、產值小、排污大的企業,嚴禁新建、改建、擴建增加水污染物排放的項目等措施,對一般超載區提出了優化產業結構,限制新建水污染物排放項目等措施,引導水污染項目退出水環境容量超載區,向富余區轉移。
4 落實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空間管控的保障措施
上述城市環境空間管控體系構建目前仍以理論構想為主,需配套相應的保障措施,才能使管控措施真正落實,起到相應的約束和引導作用。
4.1 推進環境空間管控體系與相關規劃的“多規融合”
相比于城市總體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空間管控,環境總體規劃的空間管控起步較晚,缺乏法律依據的支撐。為了增強環境空間管控的約束力,應推進環境總體規劃與相關規劃在空間管控體系上的融合。環境總體規劃的生態保護紅線與城規的“四區七線”、土規“三界四區”、城市基本生態控制線等銜接,城市總體規劃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在規劃城市空間布局時充分考慮環境質量管控區的管控要求。此外,環境功能分區應與城市分區功能、土地利用功能分區進行銜接[1]。
4.2 環境功能區劃的保障措施
為了推進環境功能區的差異化發展,應建立基于環境功能區劃的差異化的領導干部環境保護績效考核,《“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明確提出以市縣級行政區為單元,實施差異化績效考核[12]。以貴陽市為例,北部生態屏障保育與環境風險防范區應將森林覆蓋面積、生態建設成效、土壤環境質量改善、水環境質量改善和環評制度執行情況納入環境保護績效考核重點內容;西部環境安全保障區應將水體保護、生態建設成效、工業污染、農業面源污染以及城鎮生活污染治理納入環境保護績效考核重點內容;南部城市環境維護區應將水環境改善、大氣環境質量改善納入環境保護績效考核重點內容。
4.3 生態保護紅線和環境質量紅線的保障措施
制定生態保護紅線和環境質量紅線區的保護目標與管理要求、生態補償辦法、環境準入準則、監督考核辦法、違法處理辦法以及相應的責任機構,建立紅線范圍內關閉搬遷改造清單和工作計劃。成立由市長負責、相關部門為成員的生態保護紅線綜合聯席管理機構,將生態保護紅線和環境質量紅線納入城市主要規劃以及各部門的監督管理范圍之內。制定實施考核管理辦法,對區縣人民政府保護生態保護紅線和環境質量紅線的成效開展績效考核。重點考核生態保護紅線區和環境質量管控紅線區的面積變化、生態保護紅線區內生態系統結構變化、水、大氣、土壤紅線區內的環境質量變化,以及管理政策落實情況等。
4.4 環境承載調控的保障措施
建立環境承載能力的監測、評估、調度、預警等全過程制度。開展生態環境承載力預測預警評估,以流域區域生態環境質量狀況及其變化、損害健康的重點污染源和污染物排放情況為基礎構建監測預警機制,對環境容量超載區域及時“亮紅燈”和“亮黃燈”,及時調整產業準入政策和審批政策等。以環境容量及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倒逼產業轉型升級,引導城市建設和重大產業布局向環境容量較大的區域發展。
[1]萬軍 ,吳舜澤 ,于雷.用環境空間規劃制度促進新型城鎮化健康發展 [J].環境保護 ,2014 ,42(7): 24-26.
[2]呂紅亮 ,周霞 ,劉貴利.城市規劃與環境規劃空間管制協同策略研究 [J].環境保護科學 ,2016 ,42(1): 7-11.
[3]許開鵬 ,遲妍妍 ,陸軍 ,等 .環境功能區劃進展與展望 [J].環境保護 ,2017 ,45(1): 53-57.
[4]熊善高 ,萬軍 ,于雷 ,等 .我國環境空間規劃制度的研究進展 [J].環境保護科學 ,2016 ,42(3): 1-7.
[5]陳雯 ,孫偉 ,李平星.“多規合一”中生態管制作用與任務 [J].環境保護 ,2015 ,43(3): 20-22.
[6]高吉喜 ,王燕 ,徐夢佳 ,等 .生態保護紅線與主體功能區規劃實施關系探討 [J].環境保護 ,2016 ,44(21): 9-11.
[7]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理論方法探索與實踐 [M].北京 : 中國環境出版社 ,2014: 26.
[8]俞龍生 ,于雷 ,李志琴.城市環境空間規劃管控體系的構建——以廣州市為例 [J].環境保護科學 ,2016 ,42(3): 19-23.
[9]李干杰.“生態保護紅線”——確保國家生態安全的生命線 [J].求是 ,2014(2): 44-46.
[10]高吉喜 ,鞠昌華 ,鄒長新.構建嚴格的生態保護紅線管控制度體系 [J].中國環境管理 ,2017 ,9(1): 14-17.
[11]劉貴利 ,郭建 ,崔勇 .城市環境總體規劃推進實施建議 [J].環境保護 ,2015 ,43(22): 18-20.
[12]吳舜澤 ,萬軍.科學精準理解《“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的關鍵詞和新提法 [J].中國環境管理 ,2017 ,9(1): 9-13.
Research of Urban Environmental Spatial Management System of Urban Environmental Master Plan—Taking Guiyang Urban Environmental Master Plan as an Example
WU Juanni*, SUN Ning, YAO Mengyin, LU Jing
(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Beijing 100012 )
Environmental spatial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al spatial plan are weak points of the urban spatial plan system in China. The environmental spatial management system should be built up to complete the urban spatial plan system, and to convert the situation tha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plays a passive role. Building environmental spatial management system covering all areas of the city is the main task of urban environmental master plan. Progress of urban environmental spatial management is review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problems a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current progress, an environmental spatial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city is built up in the view of environmental master plan, which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function zoning, urban environmental restrict zone centered by ecological red line, and environmental bearing regulation, and Guiyang city is taken as a case study. In the last,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spatial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city.
urban environmental master plan; environmental spatial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function zoning; ecological red lin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 Guiyang
X321
1674-6252(2017)06-0084-05
A
10.16868/j.cnki.1674-6252.2017.06.084
貴陽市政府支持的“貴陽城市環境總體規劃”。
*責任作者: 武娟妮(1984—),女,碩士,工程師,主要從事環境規劃與管理研究,E-mail:wujn@caep.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