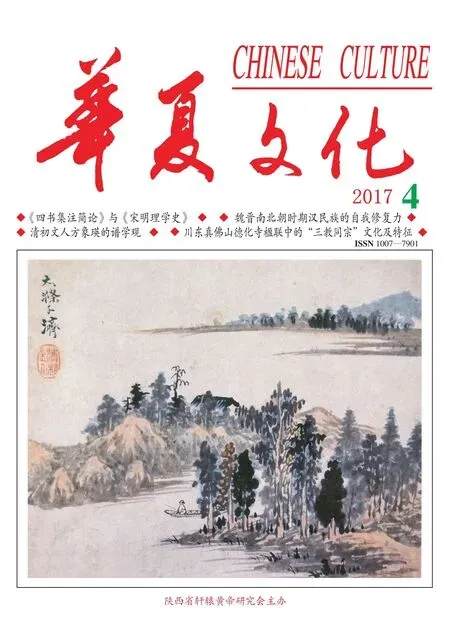試論《觀書有感》之理學(xué)思想與境界
□孫春陽(yáng)
試論《觀書有感》之理學(xué)思想與境界
□孫春陽(yá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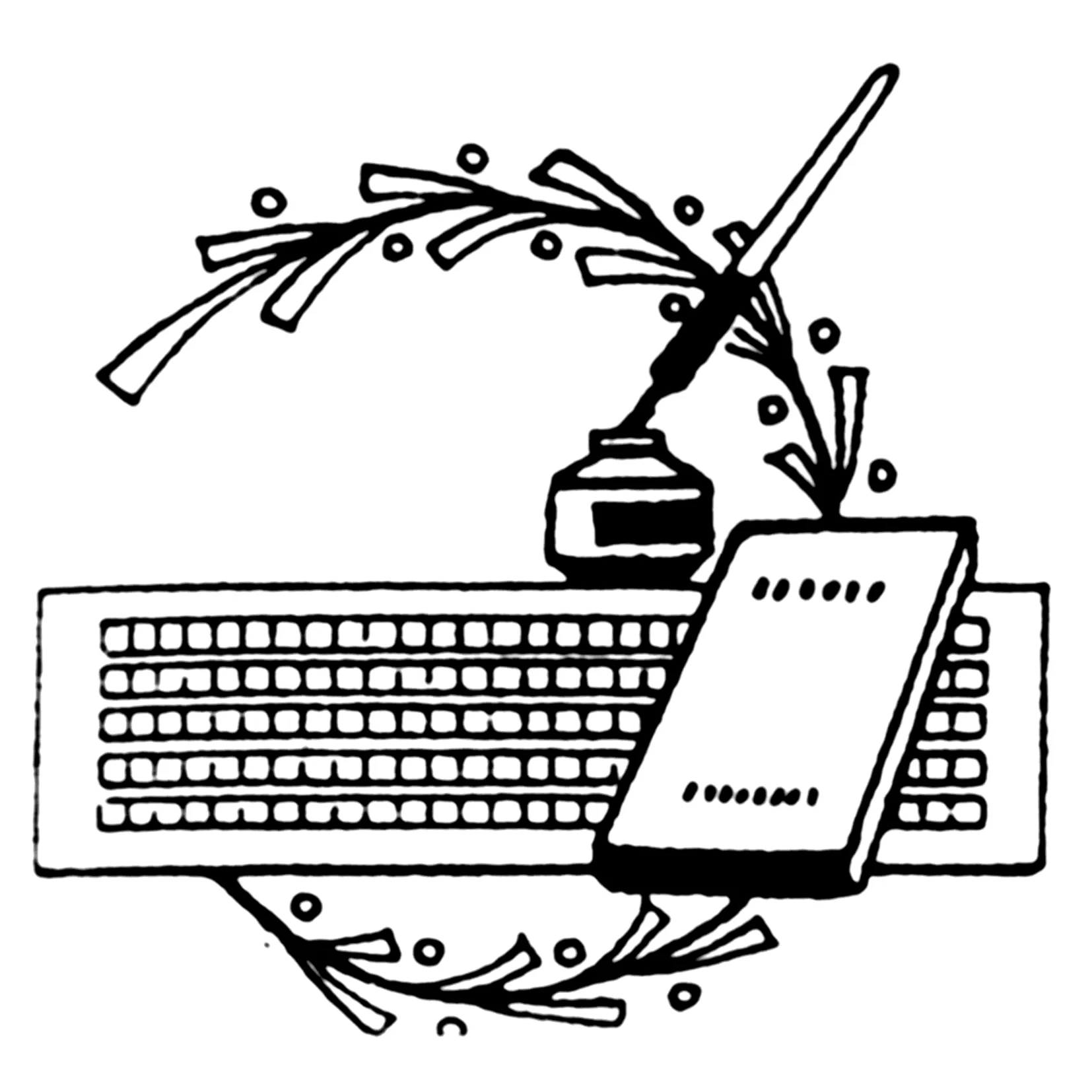
本文以概念隱喻理論為依托,找出《觀書有感》中方塘的不同喻底,結(jié)合該詩(shī)詩(shī)義,闡發(fā)朱熹相關(guān)的心性思想以及詩(shī)的不同境界,朱熹作為理學(xué)大師,不僅在理學(xué)上有著極高的成就,而且在文學(xué)上也有很高的建樹(shù)。朱熹詩(shī)文雖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觀書有感》。
觀書有感二首
其一
半畝方塘一鑒開(kāi),天光云影共徘徊。
問(wèn)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lái)。
其二
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
向來(lái)枉費(fèi)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下面將通過(guò)概念隱喻理論對(duì)這兩首詩(shī)進(jìn)行語(yǔ)篇分析。
概念隱喻理論
概念隱喻理論是認(rèn)知語(yǔ)言學(xué)的重要理論之一,它探討人如何認(rèn)識(shí)事物和如何思維等方面的問(wèn)題。隱喻不只是語(yǔ)言上的修辭方式,從隱喻與相似性關(guān)系角度可將隱喻大致分為:基于相似性的隱喻和可創(chuàng)造相似性的隱喻(見(jiàn)李福印編著《認(rèn)知語(yǔ)言學(xué)概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第131頁(yè))。基于相似性的隱喻喻底是很明顯的,在詩(shī)文中一般直接給出。但是創(chuàng)造相似性的隱喻的喻底是認(rèn)知主體在主觀上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在認(rèn)知主體的主觀想象力不斷的豐富和加深的情況下,本體和喻體之間的相似性也不斷的發(fā)現(xiàn)或者被創(chuàng)造出來(lái),從而認(rèn)識(shí)主體對(duì)一個(gè)事物的認(rèn)識(shí)的角度逐漸更新,認(rèn)識(shí)也越深越抽象。文章將以觀書詩(shī)其一為主,其二為輔進(jìn)行義理和境界的闡釋。
基于相似性的隱喻:
來(lái)源域 目的域
半畝方塘 書
一鑒開(kāi) 打開(kāi)書
天光云影 知識(shí)映射到心上
徘徊 不斷的學(xué)習(xí)
渠(池水)智慧
清 明亮
源頭 書中知識(shí)或真理
來(lái) 觀書所得
從詩(shī)的內(nèi)容上來(lái)欣賞該詩(shī)所描繪的意境,清澈平靜的水塘像一面鏡子那么光滑明亮,自然的光和白云的影子都在水塘里徘徊。該詩(shī)描繪了一幅渾然一體、自然和諧的景觀。王國(guó)維《人間詞話》中提到有我之境和無(wú)我之境。其中說(shuō)到:“無(wú)我之境,人惟靜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動(dòng)之靜時(shí)得之。故一優(yōu)美,一宏壯也。”從該詩(shī)主觀情感沖淡和平靜自然的角度看,此詩(shī)的意境應(yīng)該是無(wú)我之境。此無(wú)我之境恬靜優(yōu)美,意味深遠(yuǎn),頗耐人尋味。從詩(shī)詞藝術(shù)鑒賞的層次來(lái)看,該詩(shī)確實(shí)是在描寫靜中之境。由于此境是源于靜,于靜中所得(心定有得)。
在這一種隱喻體系中所得到的是觀書有所得,即詩(shī)人在靜中有所得,主要指書上知識(shí)。重在講觀書而后所得到的知識(shí)和智慧。“活水來(lái)”與“春水生”是“清如許”與“自在行”的直接原因。前兩句闡述了觀書的效驗(yàn),后兩句表達(dá)了產(chǎn)生效驗(yàn)的原因。
基于可創(chuàng)造相似性的隱喻:
來(lái)源域 目的域
方塘 心(人心又合道心)
一鑒開(kāi) 格物窮理(或仁的境界)
天光云影 性和情(或天理與人欲)
共徘徊 性情交感(或理欲相革)
渠 心中之理(性)
清 性體澄明
源頭活水 天理
來(lái) 天理呈現(xiàn)
隱喻的目的域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層次的。此詩(shī)不僅描繪了觀書后的境界,更表達(dá)了該詩(shī)境界所產(chǎn)生的原因,突出了此詩(shī)的理趣。嘉慶丙子家塾版《注釋千家詩(shī)》這本書的注釋說(shuō):“半畝方塘皆方寸心地也,一鑒開(kāi)則理欲凈矣,天光寂然不動(dòng)之性也,云影徘徊通之情也,方寸之中虛靈不昧,而寂感相與性來(lái)如天光云影。后二句一問(wèn)一答,言其所以如此,由其深造自得而資深有逢源之妙也。”這里就是從心與性(理)關(guān)系以及“深造自得”的功夫論的角度解釋的。
此詩(shī)是朱熹“丙戌之悟”所作,這時(shí)的朱熹認(rèn)識(shí)到心任何時(shí)候都是處于已發(fā)狀態(tài),而性未發(fā)。重在講心如活水,動(dòng)之不息,未嘗間斷。“蓋通天下只是一個(gè)天機(jī)活物,流行發(fā)用,無(wú)間容息。據(jù)其已發(fā)者而指其未發(fā)者,則已發(fā)者人心,而凡未發(fā)者皆其性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答張敬夫》)。認(rèn)為已發(fā)之心是“通天下”的唯一的“天機(jī)活物”,并且超越時(shí)空而完全的自為自行。此時(shí)的活物重在指人心的能覺(jué),而非指理之流行的道心。觀書詩(shī)有其內(nèi)在邏輯,第一首詩(shī)是,一鑒開(kāi)而得以活水來(lái),活水來(lái)而得以一鑒開(kāi)。第二首詩(shī)是,春水生而巨艦輕,進(jìn)而自在行。所以觀書詩(shī)其一是功夫與境界合一,其二重在講功夫之后的境界。
從一鑒開(kāi)而得以活水來(lái),把一鑒開(kāi)當(dāng)做動(dòng)詞表達(dá)人心作為一個(gè)天機(jī)活物,處在不停的運(yùn)動(dòng)中,而這個(gè)運(yùn)動(dòng)是格物窮理的運(yùn)動(dòng),在窮理之心不斷的運(yùn)動(dòng)下,水塘逐漸清澈即天理發(fā)明而性顯,此寂然不動(dòng)之性之所以顯現(xiàn),是由于清澈的水塘所映云影的到來(lái)。性情的關(guān)系在某種程度上和理氣關(guān)系相一致,理以氣顯而不離不雜,性與情亦如此。心中之理即是性。“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huì)之地。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fā)用底”(《朱子語(yǔ)類》卷五)。性是理在人身上的體現(xiàn),性是理在人生活中的道德依據(jù),而心對(duì)性的發(fā)動(dòng)具有主宰作用。“所知覺(jué)者是理,理不離知覺(jué),知覺(jué)不離理”(《朱子語(yǔ)類》卷五)。又說(shuō)“所覺(jué)者心之理也,能覺(jué)者氣之靈也”(《朱子語(yǔ)類》卷五)。首先理不離心,而心又能覺(jué)此心內(nèi)之理,體現(xiàn)了心的能動(dòng)性,最下功夫處也在這里。此時(shí)主要表達(dá)的是人心的主動(dòng)性以及其主宰和認(rèn)知的功能。“一家自有一個(gè)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jué)處”(《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答張敬夫》),此安宅就是人心,也是理所安存處。能覺(jué)作為主動(dòng)性是氣所具有的本來(lái)功能,也就是人心。所覺(jué)作為道心,能夠被人心覺(jué)察,所以格致窮理的最大目的就是使理不斷匯聚于心而最后達(dá)到湛然虛明。
從活水來(lái)而得以一鑒開(kāi),即是把一鑒開(kāi)當(dāng)做名詞看,既有朱熹所說(shuō)的漸進(jìn)之后的豁然貫通,這樣一鑒開(kāi)就是理之貫通全體之后的境界,“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朱子語(yǔ)類》卷五)。水之靜,即性顯。“心譬如水,水體本澄湛”(《朱子語(yǔ)類》卷十五)。只有達(dá)到“水體澄湛”,才算是盡性,道心才算得其全。此外該境界要在時(shí)刻的涵養(yǎng)下才能保證“活水”(理)的不息不斷,因?yàn)橹祆滟澩链ǖ摹办o中有物”。“‘靜中有物’如何?曰:‘有聞見(jiàn)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問(wèn):‘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lái)喚做敬’。”(《朱子語(yǔ)類》卷九六)所以該境界是在敬的作用下而產(chǎn)生和保持,敬產(chǎn)生的靜和動(dòng)相對(duì)的靜是不一樣的,所以兩者所得之境界也是不同的。
由上可見(jiàn),水塘喻為人心,人心是自家安宅,也是道心所具之處。一鑒開(kāi)和活水來(lái)的關(guān)系就是人心與道心的關(guān)系,一鑒開(kāi)是人心功夫,活水來(lái)是理之呈現(xiàn)。全詩(shī)的邏輯結(jié)構(gòu)即是:“一鑒開(kāi)”→“活水來(lái)”→“一鑒開(kāi)”。“一鑒開(kāi)”到“活水來(lái)”人心之靈的格致窮理功夫,則理之呈現(xiàn)得以盡性。“活水來(lái)”到“一鑒開(kāi)”是性盡之后,物來(lái)則寂感之性得以顯,即是天光云影之謂,而道心則得其全。第一階段先功夫后涵養(yǎng),第二階段先涵養(yǎng)后功夫,且敬貫始終,此即是“涵養(yǎng)須用敬,進(jìn)學(xué)則在致知”(《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總的來(lái)說(shuō)就是螺旋式的上升和波浪式的前進(jìn)。
活水來(lái)和水塘明澈時(shí)間上是同時(shí)的,只有邏輯上有先后。第一階段是窮理功夫,不能算為心定有得。格物致知是識(shí)的仁體湛然虛明之前,心定有得應(yīng)該是識(shí)的仁體湛然虛明之后,而有得之后的狀態(tài)就是“天光云影共徘徊”。第二階段才是心定有得。是居敬窮理所得的一種境界,是涵養(yǎng)得仁體湛然虛明的境界。
來(lái)源域 目的域
方塘 天地之心
一鑒開(kāi) 天地有心(仁的境界)
天光云影 天地之心與吾之心(本體上)
共徘徊 天心與人心合
渠 生物之心
清 仁體之理
源頭活水 天地?zé)o心(仁體、生)
來(lái) 天地合有心無(wú)心(道體流行)
從道心和天地之心的角度,也就是從心與理合的境界闡發(fā)此詩(shī),也許不符合朱熹思想,但是也不違背詩(shī)意。“半畝方塘,……此詩(shī)文公因觀書而見(jiàn)義理之高明,猶水之澄清而同照萬(wàn)物。問(wèn)渠何其澄澈光明如此,則謂有源頭活水周流。水周流而不竭,如人之義理有萬(wàn)事之殊,其本源歸于一,不外圣賢道統(tǒng)之真脈而已”(《千家詩(shī)注解》,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頁(yè))。這里對(duì)朱熹觀書的解釋是從活水周流不息的角度而見(jiàn)得本源歸一圣賢道統(tǒng)之真脈。立足點(diǎn)是一個(gè)“活”字,從活處、流動(dòng)不息處觀道體之流行。這一層是繼上

層人心的討論而加以擴(kuò)展。當(dāng)“一鑒開(kāi)”作為窮理功夫時(shí),“活水來(lái)”就是天理呈現(xiàn);當(dāng)作為境界時(shí),“活水來(lái)”就是道體流行,如“春水生”,生生不息之機(jī)。而此時(shí)的“一鑒開(kāi)”和“自在行”就是人心與道心合,人心與天地之心合的境界。
“古人觀理,每于活處看。故詩(shī)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羅大經(jīng)撰,王瑞來(lái)點(diǎn)校:《鶴林玉露》,中華書局,1983年,第163頁(yè))古人從活處觀得生生之理。不論川之流,還是窗前草之生皆是此理,從客觀處觀得此理,水塘(人心、天地之心)是一個(gè)生生不息的有機(jī)整體。從活處,道體流行,萬(wàn)物化育之處見(jiàn)得天地之心。“若果無(wú)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shù)上發(fā)李花,他又卻自定……曰:這是說(shuō)天地?zé)o心處。且如四時(shí)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jiàn)得他無(wú)心處,只恁定說(shuō)不得”(《朱子語(yǔ)類》卷一)。從生上看天地似無(wú)心,只是生,從生成上看天地似有心,因?yàn)椤八謪s自定”,所以不能從單方面講天地有心無(wú)心。塘之源頭活水來(lái)只是生,生之心,即天地?zé)o心處,方塘一鑒開(kāi)生成之貌,又見(jiàn)得他自定有心處。
“這個(gè)道理,吾身也在里面,萬(wàn)物亦在里面,天地亦在里面。通同只是一個(gè)物事,無(wú)障蔽,無(wú)遮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圣人即川之流,便見(jiàn)得也是此理,無(wú)往而非極致……”(《朱子語(yǔ)類》卷三六)朱熹認(rèn)為人之心和天地之心為一個(gè)事物,前提基礎(chǔ)是“發(fā)明這個(gè)道理”,這個(gè)道理即是心理合一。天地和人都只是一個(gè)理,說(shuō)的是在理的角度上人心和天地之心是合一的。圣人則從川流不息處觀得此理。
不論從人性的角度上達(dá)天理,還是從天理下傳人性都是為了達(dá)到天人合一,心與理合的境界。“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仁的境界、誠(chéng)的境界、樂(lè)的境界。以仁為根本,合為一個(gè)整體理的境界”(蒙培元:《理學(xué)范疇系統(tǒng)》,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2頁(yè))。由此該詩(shī)有靜之境、敬之境、道之境。一是由與動(dòng)相對(duì)之靜產(chǎn)生,二在敬(理性)的夾持下產(chǎn)生,三是由理之境而表現(xiàn)的立極之靜產(chǎn)生,而前兩種仍是歸為靜之境,與理之靜有很大差別。靜之境是主觀感受,理之境是主觀與客觀的渾然合一。沒(méi)有本然的理之境就沒(méi)有主觀的靜之境。在通過(guò)敬的功夫之后而得到仁、誠(chéng)、樂(lè)三者合一的理的境界,才能夠真正認(rèn)識(shí)到主觀靜之境的本然。所有主觀之境都是理之境的顯現(xiàn)。
結(jié)語(yǔ)
觀書詩(shī)是朱熹對(duì)心性已發(fā)未發(fā)有所悟之后而作,通過(guò)對(duì)心的認(rèn)識(shí),朱熹的理學(xué)思想也逐漸成熟,在此基礎(chǔ)上確定了其后來(lái)格物致知,即物窮理的為學(xué)方法。窮理的道路也是修養(yǎng)的道路,義理的不斷發(fā)明,德性修養(yǎng)的境界也不斷提高。宋代理學(xué)思想中認(rèn)識(shí)論和修養(yǎng)論是合一不可分的,發(fā)明義理和道德修養(yǎng)是一體的。
其次,當(dāng)主體的修養(yǎng)達(dá)到仁的境界之后也就進(jìn)入“從心所欲”的境界。朱熹在《四書集注》中引文云“胡氏曰:‘……萬(wàn)理明盡之后,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55頁(yè))總的來(lái)說(shuō)一切功夫都?xì)w于理,而一切功夫都從理流出。觀書詩(shī)是朱熹理學(xué)詩(shī)的代表作,也是朱熹理學(xué)思想的集中體現(xiàn)。
(作者:陜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學(xué)中國(guó)思想文化研究所碩士研究生,郵編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