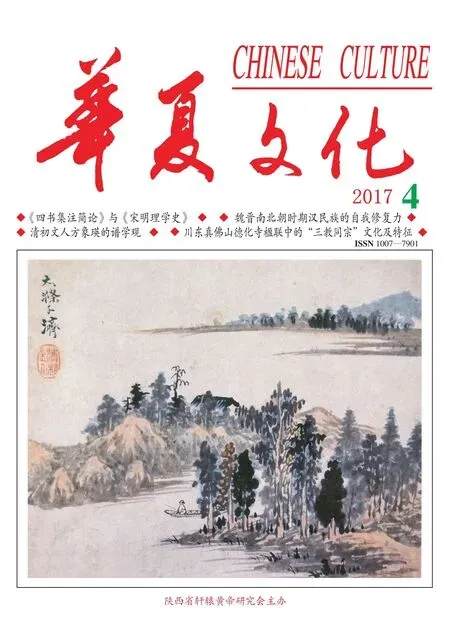戰國時期“分”思想的興起及意義
□陳 偉 王 敏
戰國時期“分”思想的興起及意義
□陳 偉 王 敏

一、問題的提出
戰國時期天子失權,王綱解紐,諸侯漫無統紀,起而互相兼并,以至戰爭頻仍、民不聊生。《史記·周本紀》概括當時的情形說:“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可以說,政治動蕩、社會失序、正義蕩然正是那場“整體性危機”的真實寫照。世事的混亂激發了思想家們的思考,置身亂局的他們“渴望秩序與和諧,由此而形成了一種秩序情結的文化心理現象”。斯塔夫里阿諾斯對于這一點看得清楚,說得明白:“混亂和改革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的思想家,迫使他們重新評估自己民族的傳統思想,或將其拋棄,或使之適應過渡時期的需要。”(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那么,彼時的思想家們提出了怎樣的思想方案來匡復社會秩序,匡扶社會正義呢?德治、禮治、法治,不一而足,各種各樣的思想主張碰撞爭鳴,可謂盛況空前。其實歸根到底就是一個“分”(fèn,意為“職分”)字,都是以“分”(fèn)的確立和實現為旨歸的,都期望明確厘清社會成員的職分和持守,并要求所有人都一體遵行,從而實現社會的有序和諧,也就是“分(fēn)而有分(fèn),共致和諧”。關于這一點,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評價荀子思想時曾經說:“荀子所說的分有時候稱為辨,不僅限于分工,已經是由分工而分職而定分。”這確實是十分精到的評價。戰國時期的思想家普遍主張通過禮法規范明確厘定社會成員的職分和持守,并希望通過喚起人內在的自覺心和借由外在的制度保障使人人都能恪守自己的社會規定性,既不逾越,也不缺位,這樣就可以做到各歸其位,各盡其責,各守其分,各勤其事,各得其宜。如此,社會也就可以實現有序和諧了。
二、戰國早期至戰國中期“分”思想的發展
早在春秋時期,“分”思想就已經顯露端倪,但是當時“分”這個概念并未被普遍地討論,“分”的思想也尚處于隱而不彰的狀態。到了戰國早期至中期,隨著社會亂局不斷趨于嚴重,“分”這個概念及其所包含的思想內容終于被思想家們系統地闡發出來了。
墨子認為上至王公大人和士君子,下至庶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分”,各盡其分是社會和諧運轉的關鍵。《墨子·非樂上》指出:王公大人的“分”就是聽獄治政,治理國家,士君子的“分”則是盡心竭力,協助君王進行社會管理,農夫的“分”乃是早出晚歸,專力于農耕生產,婦人的“分”則是早起晚睡,專心于紡紗織布。墨子認為所有的人都完成了自己的分事,各種社會事務就沒有遺缺了,社會就能夠良性運轉起來,國家就能安定。需要注意的是,墨子主張的是“均分”,他所期望的社會是有“區分”但卻無“區別”的社會,認為“分”是個人對國家社會應盡的職責。
《黃帝四經》則認為每個人各歸其位、各守其分乃是杜絕紛爭,實現國家大治的關鍵:“臣君當立(位)胃(謂)之靜,賢不宵(肖)當立(位)胃(謂)之正,……靜則安,正(則)治。”(《黃帝四經·四度》)也就是說,君王和臣吏各安其位,國家就會政治穩定,賢能的人和平庸的人分別得到恰當的任用,國家的治理就會順暢。總體來說,《黃帝四經》明確強調通過“正名修刑”來厘定社會成員的職分,其思想理路可以概括為“道→法→分”。
商鞅探求“使民之道”,認為“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商君書·修權》)。亦即頒行明確的法律來倡明社會成員的職分,而不要用君王的恣意來隨意破壞法律的實施,這樣國家才能治理良好。而且,他認為職分明確還有助于激發民眾的積極性,即“功分明,則民盡力”(《商君書·錯法》),強調的都是定分的重要性。商鞅“分”思想的特色在于強調“以法定分”,而且《商君書》還專設《定分》篇,強調通過各級官吏來倡明“分”的內容:“圣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商君書·定分》)
《尸子》對于“分”同樣很關注。《尸子·分》有曰:“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為成人。”也就是說,人的言行舉止都符合“分”的要求,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從國家政治層面來說,尸子認為“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疏,皆得其分,曰治”(《尸子·分》),也就是說,社會成員“皆得分”才能實現社會生活的有序和國家的良好治理。而且,尸子認為“分”的厘清會有助于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社會效率:“夫使眾者,詔作則遲,分地則速,是何也?無所逃其罪也。”(《尸子·發蒙》)
《慎子·威德》有曰:“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這里的“工不兼事,士不兼官”也就是各司其職,各守其分,每個人都盡職盡責地完成本職工作,互不侵越。“工不兼事”則“易勝”,“士不兼官”則“易守”,也就是說職分清楚明確,才能夠高質量地完成本職工作。《慎子·知忠》篇也指出,君王治理國家最重要的是“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也就是清晰地厘定各級官吏的職分,使其各司其職,忠于職守,這樣就可以使國家事務和順,達到最理想的治理。
孟子繼承孔子學思,其“分”思想也隱而不發,比較含蓄。《孟子·盡心上》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這是孟子唯一一次明確在“職分”意義上使用“分”。不過《孟子·滕文公上》中的一句話表明他已經接受了當時甚為流行的“分”思想:“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在這里,孟子類比說明了一個道理,即厘定人己界限,明確職分,社會自然可以治理良好,所以他主張人盡其分,即“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孟子·告子下》)
總起來說,在戰國早期至戰國中期這一時段,先秦諸子在“職分”意義上使用“分”已經比較普遍,此時“分”思想已經初步成型。
三、戰國末期“分”思想的勃興
到了戰國末期,“分”思想得到了最宏富的闡發。
荀子對“分”思想進行了前所未有的體系性闡發,這在先秦時期是獨樹一幟的。他一方面提出“明分使群”(《荀子·富國》),認為社會和諧有賴于社會成員角色的合理劃分和職分的良好持守,另一方面又提出“明分達治”(《荀子·君道》),認為明定職分是實現國家良好治理的必由之路,所以“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荀子·富國》)荀子認為要實現國家大治,就必須使臣吏百姓“敬分安制”,各謹其事,將“明分”提升為攸關社稷興衰的根本治世方略。實際上荀子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把“分”提煉、發揮成為一個型構其思想體系的關鍵概念,并進一步體系性地闡發了“分”的思想。《荀子·王霸》篇中的一段話最好地闡釋了他的理想:“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荀子所期望的是建立一個人人自覺守分的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于仁、義、禮、法的申言都是以“分”為鵠的的,“分”這個范疇是荀子政治法律哲學思想最后的落腳點。
受荀子“分”思想的影響,其后的《韓非子》在“職分”意義上使用“分”十次,專設《制分》篇闡述“分”的思想。韓非從人性惡的預設和預期出發,主張“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韓非子·揚權》),即制定法律來明定人的職分。他還從國家治理的角度論述了“分”的意義,認為“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且為‘下走’‘睡臥’,與夫‘揜弊’‘微服’”(《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也就是說,君王不通過明確各級臣吏的職分來督促其盡心竭力地工作,反而親自處理具體事務,是無法實現國家良好治理的。
《呂氏春秋》在“職分”意義上使用“分”十八次,且專設《審分》《分職》等篇,其“分”思想也是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立論的:“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呂氏春秋·審分覽》)這里的“名”實際上就是法度,制定法度,勘定職分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否則國家治理就會誤入歧途。所以,“凡人主必審分,然后治可以至”,而“不分其職,……亂莫大焉”(《呂氏春秋·審分覽》),所以正名審分是君王治理國家的根本方略。《呂氏春秋·季春紀·圜道》還以“五音調均”類比闡述了“分”的思想:“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審也。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患無由至矣。”亦即五音調均,各處其處,才能演奏出美妙的音樂,賢能的君王也應該效仿這一點來“立官”,使各類人才各安其位,各顯其能,則“國無不利矣”。
在戰國時期,“分”已經不再是一個普通語詞,它已經成為思想家們立論言說的一個重要概念,被賦予了清晰、明確、穩定的特定思想內涵,成為彼時各派思想主張的共同落腳點。
四、余論
2011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肯地指出我國當下“一些領域道德失范、誠信缺失,一些社會成員人生觀、價值觀扭曲”,明確強調要“引導人民增強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在全社會形成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其實,“人生觀、價值觀扭曲”反映的正是一些社會成員主觀上對于自己“分”的失覺;“道德失范、誠信缺失”所反映的則是恪守本分在現實行為上的失守;《決定》同時提出要引導人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也就是要求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要建立起對于自己“分”的強烈自覺,積極擔當,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盡到自己的本分,從而實現社會和諧。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一中全會上講話時都一致提出要“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這可以說是對以“分而有分,共致和諧”為思想旨歸的中國古代“分”思想的當代闡釋。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在于,她永遠像一盞明燈,照亮著我們前進的道路,為我們解決新問題提供值得借鑒的思想方案。在當下塑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法治國家的時代背景下,以“各盡其分,共致和諧”為旨歸的中國古代“分”思想理應有著更為鮮明的時代意義。
說明: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15FFX002)、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15CWHJ01)、山東省高等學校人文社科研究項目(2015JG04)和德州學院橫向項目(311455)的階段研究成果。
(作者:山東省德州市德州學院政法學院副教授,郵編253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