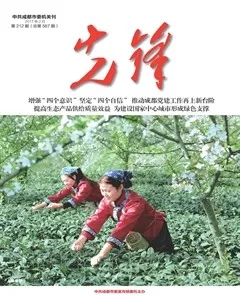成博鎮館的石犀有點萌
石犀身份考證
古人相信犀牛有一種分水能力。因為犀牛的主角長在鼻子上,下水游泳時,如果速度夠快,水波會向兩邊明顯分開,好像劈波分浪一樣。“巨海有大犀,其出入有光,水為之開。”《太平御覽》有記載:“溫嶠還武昌,至牛渚磯。云其水多怪物,遂燬犀角而照之,見奇形異狀,或朱衣,乘車馬。嶠夢人曰:‘與君幽明道別,何苦相照?’”古人認為,把犀牛角點燃,可以照見水中的牛鬼蛇神,如果讓犀牛站在岸邊,任何水精當然就不敢興妖作怪了。因此,石犀立在河邊鎮水,就是非常自然的事。
有一些文獻記載李冰擔任蜀郡太守期間,曾建造五頭石犀以鎮壓水精。如《華陽國志》中“(李冰)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后轉置犀牛二頭:一在府市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是也;一在淵中。”又如,《水經注》:“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吳漢入蜀,自廣都令輕騎先徃焚之,橋下謂之石犀淵,李冰昔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渠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后轉犀牛二頭,一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一頭沈之于淵也。”《藝文類聚》也曾記載:“《蜀王本紀》曰:江水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下,二在水中,以厭水精,因曰石犀里。”
雖然目前還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成都博物館的這頭石犀就是李冰所建造的五頭石犀之一,但可以肯定的是,這頭石犀與李冰治水是一個體系的,兼具水則(古代衡量水位的水尺)和鎮水神獸的功能。
千年后石犀重現人間
2012年8月,四川大劇院考古工地正式開工。為配合四川大劇院的修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對原天府廣場電信大樓所在地開始了正式的考古發掘工作。
2012年12月16日,經過考古隊發掘,石獸露出真容,它形似犀牛,埋藏在距地表3米以下地層,為整塊紅砂巖雕刻而成,作站立狀,側身掩埋于坑內,頭東尾西,耳朵、眼睛、下頜及鼻部雕刻簡練,風格粗獷。莫名讓人覺得可愛的外表讓市民們親切地稱它為“萌牛牛”。
根據層位關系和坑內共存遺物的時代特征,專家初步判斷石獸的埋藏時間約在蜀漢末至西晉,制作和使用年代當在秦漢時期,這是迄今發現的我國同時期最大的圓雕石刻。
這只“萌牛牛”石犀可是幾經波折,才能重現人間的。上世紀70年代,鐘樓破土動工,石獸初現。但由于條件限制,被原地回填,繼續塵封近40年。直到2010年,代表一代人記憶的鐘樓拆除,“天府廣場鐘樓基腳埋著石獸”再次引起各界人士的關注。2013年1月,隨著考古發掘的推進,石獸才逐漸露出真容。
“美容”后石犀與市民見面
石犀剛出土時,全身是“病”,令人揪心。表面被鋼筋混凝土覆蓋,其余部位有風化粉化、片狀剝落、缺失等多種病害,情況之復雜,保護難度之大,實屬罕見。文保專家專門為它量身定制了一套保護方案:第一步,用人工機械清理混凝土:機械清除表面覆蓋的大部分混凝土后,改用人工砂磨面積較小、覆蓋層較薄的部位。第二步,搭建保護棚:防止太陽直射、酸雨、冰雪對文物的損害。第三步,石獸“翻身”:啟用了大型吊車,為重達8.5噸的石獸“翻身”。在裝吊過程中,為保護文物不受損傷,文保人員用厚棉被對文物本體進行了包裹。“翻身”文保人員對石獸右側使用毛刷、竹刀等工具對石獸右側表面進行了細致清理。第四步,“面膜”脫鹽:用濕紙漿或者濕宣紙,吸附在石獸表面,等石獸體內的鹽分富集出來,凝固在“面膜”的表層。每天需要不停地更換紙張,大量的可溶鹽分就會被遷移出來。脫鹽成功后,針對文物的風化、粉化病害對其進行加固。后期還對固化后的石獸進行有依據的局部修補,力求呈現最真實的文物原貌。
現在,在成都博物館“九天開出一成都”展廳中,市民可以見到這個 “萌萌噠”的石犀,它長3.3米,寬1.2米,高1.7米,重達8.5噸,局部裝飾卷云圖案,四肢短粗,身體渾圓。以石犀為原型開發的茶寵、扇子、冰箱貼、徽章等文創產品,也深受大家的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