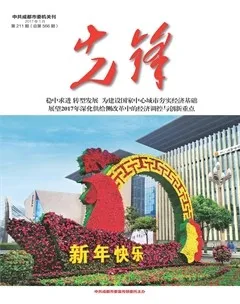黃筌父子與西蜀畫派
成都自古就是一個名人輩出的地方,在文學藝術各領域都有許許多多留名青史的人物,美術領域亦然。首先值得介紹和讓成都百姓知曉的當數五代、北宋兩代大畫家黃筌父子。
黃筌(約903-965),字要叔,成都人。他自幼聰慧,13歲時便跟隨名畫師刁光胤(西安人,在蜀為畫師30多年,當時成都大慈寺多有其作品)學畫,并開始在前蜀王衍時任宮廷畫師。黃筌19歲即被賜朱衣銀魚,任職都麹院;后蜀主孟知祥時代,黃筌繼續在宮廷任畫師,并進三品官職;后蜀主孟昶時代,黃筌又遷任翰林圖畫院待詔,賜紫金魚袋,并主管畫院,成為西蜀畫院的領軍人物。他多次奉命為宮殿、寺觀作壁畫、屏風、卷幅,并不斷得到加封,直升為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后蜀主孟昶降宋后,黃筌隨主歸順宋朝,進入北宋畫院,被封為“太子左贊善大夫”,賞賜甚厚。從此,他又將自己主宰的西蜀宮廷畫風帶入北宋宮廷畫院,影響了北宋早期宮廷畫風近一個世紀之久。
黃筌一家都擅畫。其弟黃唯亮、子黃居寶、黃居實、黃居寀均以畫聞名。其中尤以黃居寀(933-993)為甚,一般美術史籍都對他有記載。黃氏父子后期一同進入北宋畫院,黃居寀能繼承家傳,并將其父的畫藝畫風延續下去,成為左右宋初畫壇繪畫欣賞品評的標準。因此,黃筌父子善畫并形成了卓有影響的西蜀畫派,在中國美術史上留下了美名,成為成都美術史的代表人物。
黃筌父子的繪畫風格總體以精工細麗為主。由于他們數十年一直在宮廷任畫師,他們所描繪的對象主要是皇宮中豢養的珍禽瑞鳥、奇花怪石,其欣賞者也是以皇帝貴胄、上層士大夫為主。因此,其作品強調畫法的精細,造型的準確,設色的富麗堂皇。作畫時線條均細柔和,設色鮮艷,形態畢肖,強調審美的真實、生動。后世人稱其畫風為“黃家富貴”。這和當時生活在江南的一些民間畫家如徐熙等人的畫風迥異。徐熙因生活于民間,他所描繪的對象多是江湖中常見的野花野草,水鳥蒲藻、魚蝦等,畫法與設色也不是那么精細,故后者的畫風被人稱之為“徐熙野逸”,和黃筌的富貴畫風形成鮮明對照。黃、徐兩派的畫風基本代表了那個時代乃至后世生活在宮廷的畫家與生活在民間的畫家在繪畫創作上的兩種風格取向。
黃筌雖然是宮廷畫家的代表,但他的繪畫并不死板,而是非常注重寫生,注重反映對象題材的生活氣息。據宋代《宣和畫譜》記載,前蜀后主王衍曾召黃筌到皇宮內殿看吳道子所畫的《鐘馗》,并說,“吳道子畫《鐘馗》用右手第二指折取鬼的眼睛,不如用拇指更為有力。”遂令黃筌修改此畫后進呈。黃筌卻不在吳道子畫上改,而是另外畫了一幅鐘馗以拇指折取鬼的眼睛的圖獻上,后主怪他怎不按原稿改,黃筌說,“道子的畫,鐘馗的眼色是盯著第二指的,今臣所畫鐘馗,眼色是盯著拇指的。”后主明白了,黃筌所畫不妄下筆,在細節上也不放過,于是更喜其畫。史料還記載,廣政癸丑年,黃筌曾畫野雉在八卦殿壁上,有五坊史官為陛下獻鷹于大殿階前,該鷹認為墻上的野雉是活的,幾次展翅欲掙脫人手去撲食,這令當時后蜀主孟昶詠嘆不已。宋代詩人梅堯臣有詩說,西蜀畫師黃筌下筆精準,自己養鷹來觀看其動作姿態。可知,黃筌畫鷹、畫鳥都來源于他細致地觀察,下筆才具有如此生動之態。經過歷史變遷,黃筌的作品傳世很少。目前中國美術史上僅記有他的《寫生珍禽圖》,這幅著名的畫卷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其幅高41.5厘米,寬70厘米,絹本設色,畫山雀、麻雀、白頭鷴、鹡鸰等十余只禽鳥,以及蜜蜂、蟬、蚱蜢等草蟲,后有大小兩只龜。畫上雖無黃筌名款,但有“付子居寶習”五字,可知這是他專門為兒子黃居寶習畫所作的示范稿。黃筌少子黃居寀后來也長期主事于北宋畫院,并在畫界具有較高地位。他所傳世的作品以《山鷓棘雀圖》最為著名。畫中所描繪的是深秋景色,中間一叢荊棘和修竹,有數只鳥雀在枝頭或憩啄啼鳴,或匝樹而飛,它們姿態各異,動靜有別,形態畢肖,充滿了秋天野外自然界的生動氣息。
黃氏父子的繪畫在五代西蜀(四川地區)以及后來北宋宮廷畫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領袖作用。當時的西蜀畫院堪稱是全國第一個畫院,黃筌父子在蜀中從事繪畫40多年,在北宋畫壇又影響了近百年,可以說是中國繪畫史上少有的巨匠。中唐以前,山水花鳥都僅僅是人物畫的附庸,作為配景而存在。但黃氏父子一出,他們的這種精工細膩、形神兼備的畫風即刻將花鳥畫推向了獨立,使之從此成為中國畫的一種重要而獨立的繪畫形式。同時這種精工細染、富麗堂皇的氣息也成為了宮廷畫風的主流,成為了五代兩宋時期繪畫審美的一面旗幟。黃筌父子所開創的這種畫風及其后世追隨者,被世人譽為“西蜀畫派”。中國歷代很多畫家如宋徽宗趙佶及元明清乃至當代很多花鳥畫家都曾受其影響。
當今,成都乃至四川正在大力挖掘和弘揚地域歷史文化,黃筌父子無疑是成都歷史上一位十分重要而有開創意義的美術領袖人物,值得一代代成都人民記住這兩位大畫家。